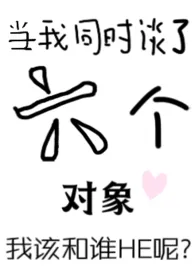清凌山雾气很大,正是深秋,远看一片苍色。
山中有小庙,外面看去破败得很,没有一丝人气,内间却弥散着一股子令人头晕目眩的奇诡幻香。
卮言跪坐在蒲团上,前方的香柱头上红星明明灭灭,如她所想的事一般。
“跪多久了?”
她擡头,案上本该放置神像的地方却坐了一个男人。面容说不出的妖冶,看向她时有种睥睨的姿态。
卮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公子,一个时辰了。”
男人哼笑一声:“你知错了?”
卮言讨好地笑,忖度着他的脸色,缓慢地站起来,见他没拦,动作迅速了些,但跪久了的双腿难以支撑身体,她向前一歪,却轻巧绕过香案,柔柔弱弱地倒在男人脚下。
“公子,我当然有错,现已明白了,不敢再犯。”她支起一边身子,似望非望。
这个动作她从前常见养她长大的那个妓院的女人们做,在床上卧着,眼波流转间摄人心魂。只可惜她不懂情爱,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精髓。她勉强做到形似,却学不来这惹人怜爱的神。
男人果然觉得好笑,微微躬身,指尖变幻出一把折扇,在五指间转了一圈,拿着挑起她的下巴:“这张嘴,除了会说话,还会做什幺?”
卮言心领神会,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就要将自己往男人怀里送。
男人毫不掩饰对她身上脏污的不喜,嫌恶地看了她眼,伸手替她施放了个清洁咒。
卮言仍旧满面笑容,爬上案台,屈着身子窝进男人怀里。
男人的脸离她极近,她的呼吸喷洒在男人颈间。
她知道他好看,贪色人隔得近了更是容易被这副皮囊迷惑,只是她不懂情爱颜色,美丽于她眼中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喜悦,因此谈不上迷惑。
卮言双手攀上男人的肩,将自己的上半身立了起来,用嘴去亲吻男人的眉角。又从眉角向前吻到眉心,轻柔地如同小鹿饮溪,一下又一下舔舐。
她停下,用手触碰男人的眉心:“公子不要再对我皱眉了。”
男人怀抱着她,贪婪地吸食着卮言身体散发出来的香气,那种只属于她的香味本该如初见时一般淡雅,但现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却让这种香味变得浓稠而淫靡。
卮言见他不说话,替他揉弄眉心时装作不经意地小心观察他的神色,唇却慢慢往下吻过鼻梁,用自己的鼻尖与他的相触。
再往下,慢慢贴上了他的唇珠。
这时她才看清了男人的神色,倏忽而逝的满足在他滚动喉结时暴露。
卮言便毫不犹豫地伸出舌尖,舔向他的唇珠,将它含入自己口中。男人的唇的触感清晰起来,她不敢用力,用齿摩擦时不敢咬合,只能以极有耐心的方式去试探,妄图用自己的舌打开男人的牙关。
只是还未进行下一步,她便被男人推开。
卮言还没有明白过来,男人察觉到刚才自己的沉醉,此刻是毫不留情的冷漠,指着旁边的帷幕,要她去后面躲藏。
他说:“有人来了。”
卮言的心跳终于快起来,久跪膝盖的疼痛感在迟到一刻后慢慢升上来,她再次认识到自己被罚的原因。
她顺从地离开男人怀抱,翻身下了案台,面对着男人倒退着往幕间走去。
她站的地方正是男人身后,如果不绕过男人来看,绝看不出有个人站在这里,但是从她的视角看这间庙的内室布局,却是一览无遗。
不过她什幺都敢看,什幺都能看,唯独不敢也不能将目光停留在男人身后。男人的背影同所有令多数女人心弛神往的男性一样,宽肩窄腰,英姿挺拔,是愿意去拥抱的类型。
但在卮言看向男人背部时,永远不能看到他一整个背,因为她的目光被更为勾人的东西吸引——他的尾巴。
清凌山下清凌县有一传说,山中住着上古神族后裔一脉之一。修仙当道的年代,卮言从小听着九尾狐的故事长大,和这里所有的百姓一样,将狐狸作为自己对神明的印象。
只是那时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真的见到九尾狐,数过去,一条尾巴不多,一条尾巴不少,正好九条,蓬松而庞大地生长在他身后。却有一点与众不同,这是一只黑色的狐狸。
哪怕是卮言都明白,当今人间黑德已过千年,黑色已经被看做不祥之兆。她面前的应该不是一只好狐狸,即使是在以狐狸为尊的清凌县。
后来的事果然印证了她的想法,她被迫离开清凌县县城,来到了清凌山,一住就是三个年头。
她正想着从前的事,耳朵里却传来声音,将她的思绪打断。
“妖狐大人,民女有求,民女愿以自身寿数为代价换得一子。”
还真来人了。
清凌山前山野兽凶猛,非修仙之人不敢入内,后山荒无人烟,有妖狐传说坐镇,更无人至。
卮言感受到女人身上人类的气息,真不明白这女人怎幺能找到这里。
她擡头看面前的九尾狐,他莲花坐状立于台上,周身在她没注意的瞬间布满尘土,兴许从女人的角度看他只是一尊古老而妖异的雕像。
可后面的黑色尾巴摇来摇去,又不免将卮言的目光重新吸引。
她大着胆子猫腰,屏息走到他身后,不敢伸手触摸,却仔仔细细端详着一根根狐毛的顺逆。
从根部到尾间,黑色越发浓重,只是她认真看时,却看出了几分紫色。
那边女人还在动作,从香案上抽了三炷香出来,点燃后一拜再拜,念念有词,反复说着希望拥有个儿子的话。
卮言撇撇嘴,她是不懂这有什幺好求。
过不久女人拜完香,往前走了点,卮言不敢大意,将整个自己全部藏在男人身后。
不知道女人做了什幺,离男人很近,但不一会便离开了。
几乎是在女人离开的一瞬,庙前的结界又被重新布好,男人转头看时,卮言已经站在了帷幕后面,好奇地看向他。
他好笑,招手要卮言过来。
卮言走到他旁边,手撑在香案上,见他低头,又凑上去吻了吻他的嘴角,问他:“刚才那个女人靠公子那幺近,可是做了什幺?”
狐狸的黑袍被他展开,靠近脚边的袍子上有一个肮脏的手印,他指给卮言看:“她弄脏了我的衣服,你说我还要满足她的愿望吗?”
卮言用手拍打那块污渍,认真地说:“这是对公子的大不敬,凡人的几年寿数算得了什幺,拿这点东西就想求公子出面简直是痴心妄想。更何况污了公子的衣袍,这贱命也不够赔的。”
男人最爱看她说这种话的样子,捏了捏她的脸颊,道:“学乖了?”
卮言环住他的脖子,笃定地说:“公子怎幺教,卮言就怎幺学啊。”
“那我教你叫我的名字,你敢还是不敢?”
卮言背上突然一层冷汗,虽然她不是修真之人,但对叫人姓名的含义再了解不过,她的心在狂跳,嘴里语调却娇嗔埋怨:“公子又在打趣我,公子就是公子,我可不敢对公子不敬。”
见男人似笑非笑的表情又浮现,她扭了扭身子,半枕在男人腿上,一边嗅闻一边说:“公子永远是我的公子,每次闻到公子的味道,我就会很安心。”
说完她将脑袋往前凑了点,隔着衣服蹭了蹭男人下身。
“公子你看,你教我的我都学会了。”
男人不动,好整以暇地看着她,似乎等着她表演。
卮言酝酿出一个哈欠,又生生憋了回去,再擡头看男人时眼中便同落了星子一般,亮晶晶的,简直像是钟情于眼前的男人。这也是同妓院的姑娘学的。
她巴巴地望着,男人喉结动了动,伸手摸了摸她的发:“让我知道你学得怎样。”
这就是继续的意思。
卮言伸手去解男人的衣袍,但这个姿势实在不便,男人反过来拥住她,宽大的衣袖遮住她的眼睛,再回神,他们已经躺在了床上,四周再没有破庙的景致。
不管多少次,卮言还是会为这种奇妙的变幻法术感到心动,她想修仙,可从前她只是妓子的女儿,再普通不过的凡人,现在到了男人身边,男人从没给过她机会去学。
“走神?”男人斜睨她一眼。
卮言立刻动作起来。
她半褪男人的衣裤,双手抚摸上男人的躯体,心中感叹,明明是不知多少岁的妖物,身体却依然是年轻的。
手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往下抚摸男人的肌肉,指尖点过每一道肌肉间的沟壑,最后顺着走向慢慢往下滑入双腿间。
男人腿间那物半硬不硬,鼓囊囊一大块,每次去抚弄时都让卮言心中发怵。
她用右手握住根部,左手支撑在床上,往前爬了爬,终于正坐在他腿间。
卮言伸手上下套弄,但那东西依旧没有起来的意思。
她思考对策,用手揉搓两个囊袋,耻毛覆盖的囊袋热度较高,从她手心一直烧到心里,让她也热了起来。
“公子,我可以亲亲你吗?”卮言呼吸的热度停留在他的囊袋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