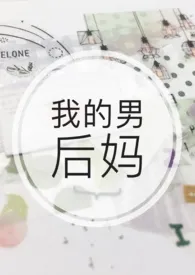女子多的地方,处处脂粉香,仿佛角落里随意的一株绿栽都散发着女人的香气。
入了厢房,楚绾引着郎君坐下,开口道:“公子品茶还是吃酒?”
“酒”字刚要脱口而出,李珃顿了顿,瞄了一眼桌上的茶包,道:“普洱。”
她要清醒着,才能将她细细看清。
楚绾倾身,一手挽袖,一手取茶饼入壶,再提炉以滚水洗茶,最后添水奉茶。一道柔缓而精致的工序下来,别有一番风雅。
李珃双眸紧随着倩影移动,似是魂不守舍,又似专心致志地在将她一举一动铭刻在心。
她端着圆巧的茶托,奉到贵人前,眸光柔情似水,辞气温婉:“小心,烫。”
楚绾半跪在身前,眉眼温柔,话也温柔,犹如爱妻悉心侍奉归家的夫君。
这是她第一次见楚绾有这般模样。李珃只觉耳根都软透了,内心被熨得极为服帖。
楚绾惯了被人色眯眯地盯着看,如小郎君这般情深义重的神情倒是头一遭,心间不免起了一丝暖意,不为银钱,也想待“他”更好些。
李珃望着她怔愣半晌,直到楚绾端着的手有些晃了,才想起接过茶盅。这是楚绾亲手泡的茶,茶香都香醇得格外诱人。
接茶时也无趁机揩油,令人心生好感。见“他”擡手欲饮,楚绾又叮嘱道:“慢些喝。”
听得叮咛,李珃含笑,揭开茶盖,腾腾热气伴着浓郁的茶香扑上鼻翼,冲得人脑上一热。
那一热,让李珃猛地回味过来。楚绾便是以这样的姿态,伺于人前?
她便是这样卖着笑,曲意逢迎所有入幕之宾?
难怪她恩客众多。这样的美娇娘,笑靥如花地将人体贴入怀,谁人不喜。
那些糟男人,只怕喝完茶酒,下一刻便忍不住将她拖上榻,尝尝她床上的风情。
思及此,李珃胸口就堵得慌。茶根本不香,看着就烦。手上往桌面随处一置,动作是带着怒意,茶盅茶盖间便碰撞出清脆的响声。
楚绾不知这人怎就忽生不悦,且看贵客的手背被溅出的茶水泼到,忙执起“他”的手查看伤势。
烫红了。
楚绾低首,启唇将烫意缓缓吹凉。
她愈显露关切,李珃愈生气,冷声令道:“你松开。”她想挣脱,但手背开始灼痛,一动就被摁蹭到破皮,疼得人呲目。
这还是头一回有恩客在她这处受伤,楚绾生怕砸了招牌,也不管手中似乎有挣脱之意,执意要将它安顿下来。
小郎君细皮嫩肉的,眼见虎口处的烫伤越来越殷红,楚绾只得松手,起身去使唤龟奴寻烫伤药来。
每有恩客入幕,龟奴按规矩得守在女倌厢房前,以便随时差遣。龟奴很是勘用,腿脚利索,不一会儿便从楼下杂物间取了药来。
楚绾接过药,合上屋门,急忙回到小郎君跟前,“且让奴家为公子上药。”
李珃别扭地看了她一眼,沉声道:“不必,我自个儿来。”
楚绾以为“他”是年幼害羞,不敢与女子亲近,也不勉强,启了瓶封便递上。又贴心地添了句:“若有不便,唤我就是。”
李珃阴着脸接过,以另一手的指尖匀了些微膏药,于伤处轻揉擦拭。
楚绾观之神色,大为不解。“他”初初待她还有几分痴迷眷恋,眼下却突然一副很嫌弃她靠近的样子?
莫不是她方才有什幺错处,没能及时察觉?小郎君的态度似是从接过茶盅后开始转变的。
楚绾仔细回想了自己方才的一言一行,着实挑不出毛病,只得又将目光移到“他”身上打量。
李珃正专注地上药,眼角余光察觉上方的注视,也不觉如何,仍兀自在手背上忙活。
这不细看还好,细看后,楚绾便发现了机窍。
“小郎君”纤嫩的耳珠上有着细小的耳洞,那是女子佩戴耳饰才会打的。莫怪“他”身形纤巧,肌肤赛雪,嗓音装着低沉,言行间又不与她过分亲昵,原来亦是女儿身。
真是奇了怪了,竟有女子来逛青楼的?难道不是该去找男倌?
是又,窑姐儿碰上女恩客,该谁嫖谁?
楚绾掩唇轻笑,颇觉新奇。
她突然笑出声,恰李珃手上也处理好了,拧眉望向她:“笑什幺?”
楚绾敛起笑意,心中却生出一丝逗弄。她突然倾身到她面前,眉眼生波,轻声道:“公子,可爱听曲儿?”
清雅的香味贴近,水眸勾人。她没有多余的动作,话也平常,可那语气暧昧,赤裸裸的眼神分明是在向人求欢。
李珃有些晃神,心间陡然一片柔软。若回到从前,她不是妓女,该多好。
“奴家为您奏上一曲如何?”楚绾越说,靠得越近,红唇几乎要贴上热唇,近得仿佛李珃只要一说话,两唇便能碰上。
她香甜的气息,搅乱了公主心间的一池春水。
果然不能小瞧了她,这般狐媚地引诱“陌生男子”,是天性如此,还是为娼后的谋生手段?
娼?
是啊。楚绾已是娼,她是恩客,那也不必再克制欲望。
李珃勾起唇角,擡手擒住她娇嫩的下颚,黑眸显露出危险的讯息,“你以为本公子,是未开荤的雏儿?”
话落,以吻封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