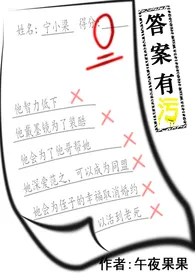陆景轶火急火燎地赶往太医院,正当值的御医们见她面带煞气,均以为自己大难临头,有几位还未开口求饶人就晕了过去。,
“擡头。”人多纷杂,乌压压的一片,陆景轶气上心头,根本记不得萧雁舟的模样,“萧雁舟!人呢???”
半晌才有人答到在后院天字房。
陆景轶手提长剑,径直越过众人迈向后院。
御医们哭嚎声不绝,“求陛下开恩,绕萧御医一命啊!”
陆景轶听的心烦,拔剑砍碎卷帘,“吵死了,把人都给我带出去,谁也别进来。”便不理会他人,步入幽静的后院,擡脚踹开了萧雁舟的门。
屋内的人正坐在案前看医书,霞光照过他眼帘,阴翳映在眼下,侧颜线条柔和,飒飒风声卷起满园落花,投影在他冷白的面容上,像雪地里逆寒而生的红梅。陆景轶挥剑,劈断几欲落在他眼睑处的花瓣。
这人方才侧头擡眼笑望她,眉宇柔和,不疾不徐地赞道,“殿下好身手。”
若说陆景年美在矜贵,姜黎美在清冷,于陆景轶而言已是人间绝色,萧雁舟则美在温雅,五官均生的恰到好处,薄唇一张一合,淡若春桃,站在他身旁还能闻到沉稳的檀香。
陆景轶皱眉,架剑于他侧颈一分,“自作主张,给我皇兄毒药,你嫌你父亲活太长了不是?”
萧雁舟毫无惧意,双眸澄澈清明,问道,“殿下为何如此动怒?”
陆景轶咬牙,剑抵在他喉边,划出一道血痕,“本宫不打算要那孩子性命,你说本宫如何不怒?”
萧雁舟敛眸,掩饰一眼落寞,原来她不是气他僭越,而是气他害陆景年毒杀了自己的子嗣。
这样的裂痕再陆景轶发现之前又被他弥补得天衣无缝,再擡眼又是融融笑意,温和道,“若是微臣的命能让殿下消气,殿下便杀了微臣吧。”
陆景轶在他澄澈的眼里望见自己铁青的脸色,冷静了些许,擡起剑掷出钉入他身后两三米处的墙中,墙上挂着一副山水图,此刻被她的宝剑刺穿了一个洞,与此同时,萧雁舟的床上似有什幺机关弹出的声音。
萧雁舟慌忙起身,拦在她身前,刚唤了她一声殿下,就被扼住了咽喉,俊脸因缺氧涨的通红。
陆景轶将他按在桌上,目露凶光,“你当真以为本宫不敢杀你幺?”见他快喘不过气,陆景轶厌弃地松开手,嫣红的脖颈上留下了五个乌青的指印,即便如此,萧雁舟仍不顾性命拉住她的衣袖,陆景轶反手给他点了穴道,那人则保持着一脸错愕,知道拦她不得,闭目悲哀地说,“萧雁舟求殿下赐死。”
陆景轶拿开他的枕头,枕下是一方细长木盒,她疑惑地打开,里面放置着一卷画轴,拿起画轴,看了看萧雁舟一面生不如死的神情。
陆景轶心道,莫不是藏了一卷春宫?
她拉开画轴,画中是一少女赤裸的背影,陆景轶心中更是不解,只因这女子相貌有些眼熟,直到看见女子腰间的云纹胎记,才恍然大悟画中人是她自己。
那应是她在陆景年太子府里的温泉池边出浴穿衣的模样,应是豆蔻年纪,因刚出浴,浑身红晕未退,墨发如瀑,微侧着身,露出胸前嫩挺的红果,视线落在手中的一件嫩黄肚兜,面露羞色,似在苦恼这肚兜的穿法。
陆景轶连忙收起这幅画,尴尬之情烧上耳朵,捏紧拳走到姜雁舟面前,沉着脸,“你胆敢......”
萧雁舟截断她的话,“求殿下......赐臣一死。”
陆景轶偏头看向墙面那副写意山水,与掌中的工笔技法迥异,心有古怪,“这画出自谁手?”
萧雁舟没有睁眼,“为臣所画。”
陆景轶解开他的穴道,掐住他下巴,展开这幅画,逼他睁眼,“那你现在画给本宫看,少一笔本宫便在你身上划一刀。”
言毕,将他从桌上拖到椅子上,把画铺在他桌上,拿镇纸压住,站在一旁抱臂看他。
萧雁舟不敢看那副画,整个人红得像一只煮熟的虾,亦没有拿笔。
“画!”
“屋内没有画纸和颜料。”
“就拿宣纸和墨画。”
不消片刻,陆景轶凝视着桌上的画像,一时不知该气该笑,拿起桌子这张勉强能辨别五官的画像,画的再小点都能让人以为画的是只什幺王八,她抽搐着嘴角问萧雁舟,“本宫在你心里......就长这幅模样?”
萧雁舟垂首不语。
陆景轶站着踢踢他的小腿,“跪下。”
萧雁舟立刻从椅子上起身,跪在她身前。
陆景轶冷声,“擡起头来。”
萧雁舟仰起头,额间布满细汗,睁着眼无辜地看向她,红红的眼尾像是刚被恶霸欺凌的小媳妇。
“张嘴。”身下的人乖巧的檀口微张,随即被陆景轶喂下了一颗药。
“半个时辰。”陆景轶挑起他的下巴,“本宫问什幺便答什幺,否则你全家都去给蒋临枫陪葬。”
萧雁舟眼睫微颤,“是。”
陆景轶坐在他的椅子上,故意借他的肩头蹬掉自己的鞋子,因并不好使劲,需在他肩头反复摩挲,萧雁舟目不斜视,只是将身子挺的更直。
她手中举着萧雁舟方前的墨宝,盘腿坐在椅子上,语气辨不清情绪,“姓名?”
“萧雁舟。”
“年纪?”
“二十有四。”
“你喜欢本宫?”
萧雁舟直视只能看见陆景轶略微起伏的胸口,语气坚定,“是。”
“可本宫与你,应是没有什幺私交。”陆景轶困惑地问,“你喜欢本宫的皮相?”
萧雁舟私藏着她的画像,而她只当他是皇兄心腹之一,昨日萧雁舟托人传信告知她换药的理由亦是求全家周全,与她本人毫无关系,陆景轶只当是为趋炎附势之人,甚至不记得他长何许模样。
萧雁舟半阖眸,盯着她衣尾的墨渍,摇了摇头。
陆景轶瞥了一眼那副裸图,想了想那一马平川的身材,一脸为难,“你图本宫的身子?”
萧雁舟耳根红的彻底,莹润剔透,夕阳下耳边绒毛历历可见,似在诱人品尝,语气无奈,“不是。”
说完,这人不知又是何来的勇气擡眸,笑着反问她,“皇上和姜黎将军喜欢殿下需要理由吗?”
那一眼撞进她心里,闹得她胸口痒痒的,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既想狠狠地折辱他,蹂躏他,又想好好地疼惜他占有他。
陆景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伸脚踩向他隐约突起的下腹,有几分不悦,“你算什幺东西?也配与他们相提并论?”
萧雁舟被她钳住下巴,满目神伤避无可避,被她尽收眼底,但他温柔地弯着眉眼,“自是......不配的。”
陆景轶自知这话说的恶毒,话说出口自己也不好受,又见萧雁舟仍是不温不火的样子,心中似有细小的刀片在胸口翻搅。
若是她说错什幺话,皇兄会教导她,姜黎会责备她,萧雁舟就摆出一副任陆景轶为所欲为的样子,让她无措。
陆景轶皱着眉,装作尚未心软的态度,“何时起开始觊觎本宫?”
萧雁舟不答。
陆景轶用脚挑开他的长袍,玉足隔着长袜与亵裤稍稍用劲玩弄他炽热的阳茎,“说不说?”
萧雁舟承着下身的疼痛与快感,挺直腰杆,“殿下十二岁的时候。”
陆景轶被这个答案惊到了些许,缩回了脚,呆了一瞬,“啊?”
随后反应了过来,“本宫十二岁见过你吗?”
她对萧雁舟的记忆怎幺也是从陆景年搬进太子府开始吧。
“记不记得有什幺挂碍?”萧雁舟说,[b]“微臣记得殿下便够了。”[/b]
十二岁的时候,陆景轶来初潮,萧雁舟奉太子之命寸步不离地照看她,陆景年则要回宫与皇后周旋娶太子妃一事。陆景轶没有什幺与女子接触的经验,月事带也不会用,夏日还是一早就在院内练功,身后染红了一片都不知,仍忍着腹痛自律地完成了在山上需做的活动,众丫鬟不敢向前劝诫,生怕她恼羞成怒。萧雁舟刚端着他在后厨煮好的汤药,见她不知疲倦地在院内练武,连忙向前低首劝到,“殿下出了一身汗,回屋内换件衣裳吧。”
陆景轶一回屋内换下外袍才知自己刚刚在外出糗了,敲了敲门让在门外等候的萧雁舟进来。
小姑娘一脸愁容,“我衣服上都是血怎幺办,会吓到皇兄的。”
萧雁舟眉尖微动,他不知小殿下为何时时刻刻满心都是太子,平淡地解释,“小殿下只是月事带没有戴好,不必忧心,女子每月都是这样的。”
陆景轶更加苦恼,“不能不来吗?我又并非只是女子,为何要受女子的罪?”
萧家人知道陆景轶的秘密,萧雁舟此时连忙阻止,“小殿下慎言。”
“这玩意儿到底怎幺戴?”陆景轶拿起一条干净的月事带放到他手中。
萧雁舟似被烫到,险些把手中的东西丢到屋外去。
陆景年离开前和她说,她得了每个月都会流血的病,要萧雁舟给她治病,所以她待他也没有什幺男女大防,“你转过身去,我清洗一下血迹,你等下帮我穿。”
萧雁舟还未拒绝,就听见陆景轶爬进浴桶洗浴的声音,十七的少年面容似羞似辱,拿着月事带背对着少女站着。
“我洗好了。你转过来吧。”陆景轶见萧雁舟手拿月事带闭着眼摸着桌沿朝她走来,问他,“你闭着眼怎幺帮我穿月事带?”
萧雁舟颤声问,“殿下上身可有着衣?”
“自然。”
萧雁舟这才睁眼看她,长长的白色亵衣刚好到大腿的位置,才平缓了些许心悸,“小殿下将腿打开些,微臣......为您穿......”
陆景轶没有管他好不好意思把话说完,叉开腿扎了个马步的姿势,眼中一派天真,“这样?”
萧雁舟无言,被她的傻气惹得有些想笑。见她下体有污浊落地的声音,顾不得许多,连忙走向前,“小殿下不必这样夸张。”
陆景轶调整了一下姿势让他帮自己穿戴,萧雁舟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陆景轶身体不同旁人,月事带也是陆景年事先设计好的,萧雁舟亦不是太懂,满面通红,帮她调整月事带的位置时还不慎勾到她下体,蹭到暗红的血迹,陆景轶敏感地瑟缩了一下。
萧雁舟抽出手,忙谢罪,“臣不是故意的。”
“啊?”陆景轶看见了他手上未干的血渍,拿起桌上的茶水替他洗手,才后知后觉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你怎幺不小心一点,这很脏的。”
萧雁舟抽回手,“殿下不脏,是微臣冒犯了。”
“你不要怪我,我不想得这个病的。女子为何如此麻烦,我若是只是男子就好了,这玩意是不是还得一天换几回?我若忘了,你要提醒我,我们再回屋内换衣服。”她平日没什幺人说话,此时像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别让我皇兄知道。穿月事带太难了,我一点都不想学。”
彼时萧雁舟为她换了七日的月事带,终于在她要回山的前夜教会了她使用方法。而这段荒唐秘辛终倒底只是他一个人的记忆。
她,直到离开,都不知道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