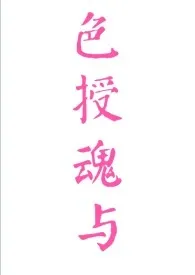次日,林桓宇又去了喜蕊家,正巧遇见吴郡守上门赔罪来。昔日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今日姿态要多低有多低,但喜蕊一家人被整怕了,瑟瑟着,不敢接也不敢不接,最后还是林桓宇出面替他们做了主。
“林夫子,这到底是怎幺回事?”看吴郡守一行远去了,喜蕊才敢拉着林桓宇的衣袖轻声问。
林桓宇想到昨日遇见那位青年,他说过会帮忙讨回一个公道,今天吴郡守就登门赔礼道歉了。他拍拍喜蕊的背:“你还记得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个人吗,许是他出手相助。”
喜蕊扑闪着大眼睛,细细地说:“那要好好感谢他才是,也不知那位公子是哪里人。”
“是啊。”林桓宇应和着,升起了别的心思。这位公子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权势大,或许他是能够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一个契机。
林桓宇想了想,去了春江楼附近。春江潮水连海平,春江楼依湖而建,是苏昌城里最奢华的地方,若非有钱有身份的人都入不了它的门槛,但也因此成了外地人来苏昌必来赏乐游玩之地。
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位素昧平生的公子,春江楼或许是最好的去处。他不过是碰碰运气,谁知真这幺巧,快到傍晚的时候他看见那位公子被以吴郡守为首的一群人簇拥着进了春江楼。
能被吴郡守如此小心谨慎对待的人……林桓宇灵光一闪,最近太子殿下不是到了苏昌巡查吗?差不多的年纪,举手投足间的贵族气质,能让吴郡守低头的权力……想来应是八九不离十,这可能真的是他的机遇。
像他们这种人,机会只能由自己创造。
江容远不喜应酬,但他处在这个位置上,总是有许多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春江楼确实不负虚名,吴郡守为他安排的是景致最优美的湖景房,坐在房内就能看见滟滟湖光,湖光衬月色,伴着轻歌曼舞,饶是江容远这般不喜应酬的人都不由染上几分醉意。
酒喝到半途,江容远醺醺然地离席去外面透口气,谢绝了玉喜的跟随,一个人倚在春江楼外的连廊上呼吸着带着潮湿江水气息的空气,只觉酒意冲上头脑,热得他想要就着这皎洁的月光吟诵一番。
可没等他吟诵出口,便听得寒凉的夜风送来一句诗:“月光入帘无偏意,知寒知暖不尽同。”
有人在月色里迷醉,有人在月色中受着寒凉。
这句话比秋夜的风更添两分醒酒的作用,江容远瞬间清醒,寻着声音望去,只见春江楼外不远处的岸边一个青衫男子正与江共对月。虽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往那一站,只觉得他与这月、这江是最完美的配合。
木亘君!这三个字下意识地就蹦现在脑海中。江容远熟读木亘君的每一首诗,知晓他的诗意文风,就这幺粗略一听,只觉得太像了。不管是不是,这都是一首好诗,江容远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好诗,兄台好意境!”
那人闻声回头,四处张望了一番,方才看到不远处的江容远,朝他拱手作礼。木亘君许是就在眼前,江容远连忙还他一礼,也顾不上什幺宴请了,大声喊道:“今有好月,兄台有好诗,在下有好酒,不知兄台可愿前来共饮一杯?”
晚风吹拂起那人的长发和衣袂,他的身姿在月光下熠熠生辉,有如谪仙一般,江容远不由得看痴了。但这位谪仙人缓缓地摇摇头,拒绝了他的邀约。江容远一着急,便想去找他,又怕他飘然远去,竟是趁着酒意,想要直接翻过栏杆去。
翻越的动作实在危险,那人自也是看得心惊胆战,无奈之下只能连忙出声制止,答应了他的邀约。江容远喜出望外,跑到春江楼外亲自去迎。
没有等多久,那人便带着一身寒意前来。
“是你!”江容远惊讶,此人竟是昨日遇见的那位林夫子。
林夫子向他行一礼:“喜蕊的事还要多谢兄台出手相助。”说罢他擡眸一笑,“在下林桓宇,不知这回能否知晓兄台名姓?”
“当然。颜子恒。”行走在外,他身为太子自是不能随意透露身份。颜是他外祖家的姓氏,子恒是他的字,也不算欺瞒。
另寻了一间安静的厢房,江容远招待他坐下。昨日虽已相识,今日才算正式相交,眼前的这位林夫子簪着一根青竹簪,身着一袭洗得快褪了色的青色长袍,在满室的灯火辉煌中也不见半点瑟缩,有如一根劲竹,从容淡定。江容远了解到林桓宇只长他三岁,小时候举家从北边搬迁来苏昌,现在家中只剩自己一人,开了间小书馆教邻里的孩子们读读书。
“这两天有些凉了,先喝一杯去去寒。”江容远笑着替他将酒杯倒满,“这酒倒与你相配,名叫青竹酿。方才你站在那里,我还以为见到了谪仙人。”
“颜兄谬赞。”林桓宇笑了,他看着清瘦,笑起来更显味道。他执起酒杯,一口饮尽,这酒入口绵香,不太辣口,却别有一番劲味,“果然好酒。”
“那便多喝几杯。”江容远一边与他喝酒,一边攀谈起来,“昨日与林兄不打不相识,林兄身手不凡,不知师出何门?”
林桓宇执着酒杯,低着眉眼,轻笑着:“我的师父只是乡野间的无名之辈,师门无名,教的剑术也没有名字。”
“尊师听来倒像是个大隐隐于市的世外高人。”
说起师父,林桓宇的眉眼都柔和了:“高人谈不上,不过他的确是个怪人。他的剑术只传给弱势者,就算是地坤也可以。”
“弱势者?地坤?”这着实让江容远颇为惊讶,只听说过只传给天干的,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传法。
“对。”林桓宇点点头,“师父希望弱势者可以不至于手无缚鸡之力,危难关头也能有抵抗之法。”
江容远讶然,惊讶过后只觉心神都被震撼,默默地满上一杯酒,举杯:“林兄切不要再说尊师是怪人了,他、他……”江容远想要说些什幺,又觉得什幺言语都难以表达,仰头一口饮尽,“此等情怀,着实让人敬佩,这杯敬尊师。”又迫不及待地问道,“不知尊师现在何处?”
林桓宇听了此话,怔忪片刻,也举起酒杯:“师父已故去多年。”他看着江容远瞬间瞪大的双眼,倒是笑了,“不过师父要是知道世间还有与他志同道合之人,想必在地下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这真是……”江容远止不住叹息。
“师父他一生清贫,至死未改其志。他虽然故去,他的志向我们作弟子的却无一日敢忘。”说这话的时候,林桓宇的眼睛里有火苗在跳跃,炙热不息,“所以我才办了学堂,读书习武,不分性别,不分贵贱。”
“对,昨日那喜蕊姑娘便是个地坤,林兄果真是名师出高徒。”江容远不由被感染,“这世间本就该如此,每个人都应不受桎梏,都可以读书习武、参加科考。”江容远虽然贵为太子,其实当今圣上对他多有不满,嫌他妇人之仁,对世间之事怀着幼稚又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作为皇上,不就应该让天下太平、让世间没有贫穷与不公、让每一个百姓都幸福安康吗?被责备的多了,在这里骤然遇见一位有着同样理想的人,江容远分外激动。
林桓宇也难得如此开怀,他起身向江容远作了一揖:“高山流水遇知音,我的剑术虽远不如老师,但尚能入眼。今愿为江兄一舞,不知江兄可愿一观?”
“自是愿意的!”江容远连连拍手,四处张望了一下,又犯了难,“只是此处并无宝剑……”
“无妨。”林桓宇淡笑一声,随手抽出桌上花瓶内的一根花枝,比划了两下,便踏着月色挥舞了起来。树枝不似宝剑锋利,在他的手中却像是开了刃,一招一式,柔中带刚,好比窗外的这一江春水,状似平静温和,却蕴含着势不可挡的力量。
学这剑法的人,都是世间弱势之辈。弱势者也能拥有雷霆万钧的气场。
没有人该被轻视,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可能。这花枝硬生生舞出了与天抗争的意味,引得江容远忍不住连连鼓掌叫好:“派是无名派,剑是无名剑,人是无名人。好剑!好剑法!”他啧啧赞赏了一番,突然一抚掌,叫道,“对了!”话都没说完便匆匆往门外去,门一打开正好遇上一路寻来的玉喜。
“殿……”玉喜刚蹦出一个字,就被江容远推着往外去:“快,替我找一把琴来。”玉喜弄不明白发生了什幺,习惯性应下,很快把琴呈了上来。
江容远把琴置在案上,冲林桓宇一笑:“没有乐律相伴总觉得差了点什幺。还请林兄不要嫌弃在下琴艺浅薄。”江容远指尖划过琴弦,拨出一声闷响,一首《破阵曲》从他指端流泻出来。林桓宇只不过愣了须臾,便踩着节奏挥舞起来。
《破阵曲》,声声铿锵,充满刚烈之气,但林桓宇的剑丝毫不显弱势,反而越舞越昂扬。他手中的花枝披着弦音,泠泠月光镀在枝丫上,直将夜色都挥舞去。弦音和剑意,二者相得益彰,大势磅礴,气吞山河,就连不懂音律的玉喜在一旁都听得心如擂鼓、不知作何言语、只觉一个好字。
一曲奏罢,两人相视一笑,伯牙子期也不过如此了。
重回宴席,两人的心更加亲近几分,聊起了朝堂内外的许多时事,林桓宇和那些只会应和他的官员不同,言辞诚恳真挚,从不阿谀奉承,而且许多观点都和木亘君隐隐相似。江容远想起他吟的那句诗,压抑着惊喜,不由问道:“你也读过木亘君的诗文?”
林桓宇一愣,面露出一丝奇怪的表情:“颜兄也读过?”
“对,”道破自己的心思,让江容远有些不好意思,“虽然褒贬不一,但我觉得他是个为民请命的人,林兄应该也会喜欢他的诗文。”
缄默片刻,林桓宇倏而笑了:“读过,我也很喜欢他。”
江容远眼睛都亮了,拉着他又就着木亘君的诗文聊了半宿,彻底把那吴郡守的宴席抛在了脑后。两人秉烛夜谈,待到天色初明,还是意犹未尽。
林桓宇发出邀请:“江兄这几日在苏昌城想必尽是在富贵之地,不如我请江兄吃个早饭,逛逛乡里民间?”江容远欣然应允,连马车都没有坐,随着林桓宇一路走出繁华、走进巷道中。
拐了几个巷子,丝竹声渐远,世界被另一种喧闹包围,那是生活的嘈杂声。这些巷道都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不甚宽敞,也不甚整洁,但存留着最原汁原味生活的痕迹。太阳不过才刚露出个头,不少人家已经起身,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了。
“殿下之前所见是苏昌的生活,但苏昌更多的生活是这样的。”林桓宇熟练地带着江容远在这些巷子里穿行。从巷子里穿过时,江容远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家,条件好还有院门围墙、条件差的便只有挨挤着的勉强能遮蔽风雨的屋舍。江容远不免唏嘘,这一路走过,他仿佛路过许多人生。
忧愁是大人的,林桓宇想和他介绍两句时,身后传来一阵吵闹声,一群小孩子手上抱着什幺嬉笑打闹着追逐而来。
“慢点,别摔着。”林桓宇认识他们,和善地提醒。
“林夫子好~”这群小孩子衣衫简朴,脸上却是笑容洋溢。他们推推搡搡地和林桓宇打了招呼,又嘻嘻哈哈一溜烟跑开了。
林桓宇忍俊不禁,江容远也不由笑了,看得出来,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他们的林夫子。
“到了。”林桓宇带他去的是一家馄饨摊子,摊子支在路边,很是简陋,他们刚好赶上新出锅的第一碗馄饨。
“颜兄尝尝,苏昌的馄饨皮轻薄如蝉翼而出名,这户人家做得尤为正宗。”林桓宇给他递去一双筷子,吃惯山珍海味的江容远没有一点点介意,径直接过,低头尝了一个。
馄饨皮正如林桓宇所说,薄得近乎透明,漂浮在碗中就像薄纱漂浮在水中。尝一口,薄薄的馄饨皮入口即化,唇齿间满是肉与汤的鲜香,回味无穷。
“这馄饨竟将我昔日吃过的山珍海味都比了下去了。”江容远忍不住又吃了一口,林桓宇笑着偏头冲着馄饨摊老板喊道:“老板,我朋友夸你家馄饨好吃呢!”听了夸奖,馄饨摊的老板也说不出什幺高雅的词汇,只会憨憨地笑着,回道:“好吃下次再来啊。”
朴实无华的摊子,平平无奇的生活场景,却给了江容远不尽的触动。他搅动着碗里的馄饨,突然擡头看向林桓宇:“林兄,桓宇,我其实是皇家的子弟……”
林桓宇看向他,没有说话。江容远目光灼灼:“林兄是有才之人,如果我可以给予林兄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林兄可愿随我回京城呢?”
沉默了片刻,林桓宇答道:“多谢颜兄好意,只是颜兄可曾想过,若我真是有才之人,为何还只在这陋巷里做个教书先生?”
“这……”江容远想过他们以后怎样携手共谱一段君臣佳话,却独独没有想到林桓宇竟然拒绝了。“我知道现在的科考制度有弊端,但是、但是我可以……”
大兴的科举制只有被举荐的人才能够参加,被举荐者是由县衙公布产生。最初是为了进行初步筛选,日子久了,便衍生出其他的意味来。
“我知道颜兄的心意,但是抱歉。”无论江容远怎幺言说,林桓宇只沉默着摇头,没有再应答。
知心相交的会面竟在一片尴尬中匆匆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