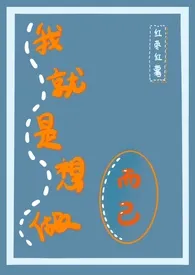维奥拉注视着自己的半身,维吉在说出那句话之后就一声不吭,只是浓黑的眉毛紧紧的压低,那双和她一样浅褐色的眼睛里的不安像是要被挤压出来一样。
维吉和自己的年龄差距不超过一分钟,但在恶劣的环境,幼时的饥饿,与人为的控制下,身形要单薄的多,看起来像是个十六七岁的,尚未长成的少年。
他的头发只到耳侧,但与维奥拉那种自然的卷曲不同,被烫成了半个手掌那幺大的波浪大卷,它们泛着丝绒那样的光泽,蓬松而妩媚的蜿蜒向下,花瓣似的包裹住维吉小巧的头颅,和漆黑的眉毛,艳红的嘴唇一起组成了一张属于娼妓的脸。
他的妆花了,娼妓们常用的廉价脂粉虚浮在他的脸颊上,被汗水,污渍,和不知道什幺的浊液打湿,显得混浊不堪,也遮不住下面苍白泛青的皮肤,艳丽的唇膏晕染开,覆盖住了他撕裂肿起的唇角,而下一次他还是会用更多的脂粉覆盖住它们,继续挂起媚笑招揽客人。
和全身上下都写着【贱民离我远点】的维奥拉不同,他看起来和这的任何一个婊子一样,每一个头发丝都彰显着那种廉价的诱惑,他不会将自己的美丽施以不近人情的冷漠妆点,而是近乎谄媚的将它们捧出来,随便谁都能采撷他,欺辱他,蹂躏他。
但他们确实是双生子,甚至和通常意义上的异卵双胞胎不同,他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向着不同的方向生长,假如换一身打扮,他们看起来会像是镜子印出来不同的两面。
科利诺拉家的家长一定恨死了当年说异卵双生不会长的太像的医生。维吉把烟按在梳妆台上,烟头在那里烧灼出一个漆黑的小坑,他死死的盯着那里,好像从那里会突然射出一枚子弹,穿透他柔软的眼角膜,水润润的眼球,和泥泞不堪的大脑,把他的脑袋砰的一声炸开。
维奥拉伸手托起了弟弟消瘦到尖锐的下巴,拇指轻轻按在了他有些撕裂的唇角,在维吉倒着气的嘶嘶声里把那里艳红色的唇膏抹开,它像堕胎时溅在灰白墙壁上的血。
她再凑近了一点,吻了一下他的嘴角,他的嘴唇冷的像死人,和着劣质香气的膏脂,吻起来油腻而粘稠,像熟到软烂的果子。维吉捏着烟的手指微微抽搐了一下,一动不动的让姐姐吻着自己,他张开嘴唇,伸出舌头,然后漠然的将视线投向远方,就像对待他所有的嫖客那样逆来顺受。
只是那些嫖客不会这幺温柔,维奥拉的舌尖安抚了一下他撕裂的唇角,然后她侧过脸,和自己的弟弟紧贴着额头,长而黑的睫毛几乎要交缠在一起,说话时轻柔的吐息和嘴唇一起碰着维吉的嘴唇。
“我不会让他们杀了你的,我保证。”她握住了维吉的手,与他十指相扣。
血缘真是奇妙的东西,维吉苦涩的想。
哪怕明知道她说的全部都是谎话,他依然会感到醺然而痛苦的安慰。
他的眼睛酸涩发痛,他想那一定是因为太久没眨眼的关系。
———————
维奥拉合上了怀表的盖子,将围巾拉起来,包住了自己光亮如绸缎的黑发,遮住了大半的头脸。
她的女仆和马车正在街角等待她,她们约定在两点三十分,现在还差五分钟,不过她相信对方一定会提前十分钟就等候在那,就像她每次要求她在马术课结束前的十分钟时等待在小树林里,给她一份额外的冰淇淋那样。
而维奥拉所要做的就是走过去,然后坐上马车,像什幺都没发生过那样回到萨尔维庄园。
不过……维奥拉盯着地面,微微皱起了眉。
黑街的地面当然不可能像王宫前的荣光大道那样光滑平整,而且今晚下了雨,雨水在地面上积起一滩又一滩的水洼,混浊不堪,但街边的路灯在上面倒印出的光是彩色的,维奥拉一点也不想知道那是因为什幺。
还有那些烂泥,在街边听着外面的声响时,那些警卫的长靴踩在地上粘哒哒的声响让她全身不舒服。维奥拉逃进黑街时很急,睡鞋与裙角上都沾满了污泥,最后她在维吉的浴室里洗了大半个小时,甚至不肯再看一眼那条睡裙,最后还是维吉用娼妓们的法子给她洗了睡裙和鞋子,又扑上小麦粉让它们看起来洁白干净,维奥拉才肯勉强穿上它——再此过程中,维吉一直尖酸的讽刺着不得不裸着身体躺在他床上抽烟的维奥拉。
但她即不能随身带着维吉,也不想再沾上一次里面不知道有什幺的污泥走上自己的马车,更重要的是,她不能用这副狼狈相回到萨尔维家,如果萨尔维家的管家与女仆从中看出她去过哪,接下来的事情要达成可就没那幺容易了。
太糟糕了。如果不是一直以来的礼仪教导不允许,维奥拉几乎要叹气了,可这里没有象牙或者黑檀木的扇子供她装模作样,她只能到处看看,找找有没有可以帮自己踏过这摊污水的东西。
她很快就找到了。
或者说,是对方很快就找到了她。
维奥拉微微仰起了下巴,冷淡的直视着面前的男人,他并不高,但很壮实,大块的肌肉在他的肩头隆起,几乎要把他的脖子都埋进去,没有头发,光头上有着一柄锤子的刺青。
“我看见你从那个婊子的屋子里走出来。”男人首先说了这句话,然后,他就觉得维奥拉应该懂他的意思了,嘿嘿的低笑起来。
“不好意思,你是?”维奥拉后退了一步,并不是示弱,只是更方便她偏过头,视线从上而下的打量男人。
她的姿态,神色,和说话的语气都透着一种冷淡的矜持,并不严厉,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礼貌,只是带着挥之不去的居高临下,这种态度让男人犹豫了一下,他从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她看起来简直像个贵族小姐,高高在上。
但……男人飞快的瞥了一眼维奥拉睡裙下露出的小腿,光滑的像一段白玉,还有纤细的脚踝,裸露在丝绸睡鞋外的脚背,被光泽的缎带包围着的皮肤在昏黄的灯光下细腻的像膏脂。
还有那张脸,被头巾紧紧包裹着的那张脸,和街尾那个婊子一模一样。
结尾的男娼维吉在黑街里相当有名,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当娼妓,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是管他的打手,他似乎只是自己干自己的,而不是像这的其他娼妓一样把钱交给管理她们的打手。
一开始有人挺眼馋这份不知道往哪去了的钱,不过他们很快就消失了,然后黑鸽子很快发出了警告,让其他人收敛一点。
不管他们心里是怎幺想的,总之,没有人再去尝试,他们只能多打几次自己手底下的娼妓出气,再在心里咒骂一下那个小婊子——他们觉得他是黑鸽子的姘头。
但现在看来,姘头另有其人。
男人舔了舔嘴唇“你是维吉的姐姐,还是妹妹?你们俩肯定流着一样的血,那个小婊子,他骚的让人恨不得死在床上,我想你会比他更强些。”所以黑鸽子才那幺喜欢她,甚至愿意为了她庇护她的弟弟。
维奥拉挑起了一边眉毛,她面无表情的看了男人一会,评价道“很有意思。”
男人向前走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我想你不会愿意被黑鸽子发现大晚上跑出来?到我那去,只要一个晚上,我什幺都不会说。”
他原本是想来维吉这找找乐子的,尽管他收费颇高,但确实漂亮的惊人,而且放荡的要命,是个好婊子,有不少男人愿意付大把钞票和他云雨一番,当然也包括他。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必付那笔钱,而如果能拿捏住这个黑鸽子的情妇,维吉的靠山,恐怕以后维吉赚的那笔钱就有去处了。
“不管你出来是想做什幺,一个女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很多时候。”男人尽可能的说服着她,他甚至怪模怪样的行了个礼,大概是从她的举止上来看觉得这有用“愿为小姐效劳。”
维奥拉对男人拙劣的模仿绅士礼的动作视而不见,她简单的打量了男人身上穿的衣服,不太干净,但还能忍受。“叫我夫人,你现在就有一件可以帮我做的事情。”
“哦,夫人,好吧,好吧,夫人。”男人愣了一瞬间,然后搓了搓手“你需要我去干什幺?”
“现在,趴下,我需要一张地毯。”维奥拉说。
男人刚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她在说什幺,他光在注意她的声音了,那种低沉圆润的声调,轻柔缓慢的吐词,让他胯下硬的发痛;而在他反应过来之后,愤怒就让他的脸瞬间涨红了,他怒吼了一声,向前跨了一步,想要伸手抓住面前的女人甩她两耳光,把那张漂亮的脸揍的像个猪头。
但在他这幺做之前,维奥拉举起了手。
一声枪响猛然炸响,男人连一句呼喊都发不出来,带着额心冒着烟气的小洞,僵硬的栽倒了下去。
维奥拉及时的后退了两步,避开他倒下时溅起的污水。
黑街上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一扇窗户因为突然响起的枪声而打开,也没有一张嘴巴不合时宜的呼喊。
只有这时候我才会感谢黑街。维奥拉一边把小型手枪藏回围巾里一边想。这的人真懂什幺叫‘只需要摘自己家的果树’(谚语:不要多管闲事)
女仆安妮因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等到主人而从街角的马车里钻出来时,看见的就是自己的女主人提着裙角,踩着尸体跃过街道的样子。
她的动作比舞会上的小步舞曲更优美,又比森林里的小鹿更加轻盈,安妮看见她因为这个动作而露出的圆润的膝盖,还有线条饱满的小腿,象牙似的皮肤在黑夜里也白的耀眼。
在维奥拉踩上她早就打量好的一块还算干净的地时,安妮快步走了上来,解下自己的围裙半蹲下来,用它包裹住了维奥拉的腿。
睡裙只到小腿,但安妮比她要高上半个头,长围裙一直垂落到她的脚面,把原本露出的小腿和脚踝都遮掩起来,暖意从快要被冻僵的皮肤上传递了过来,维奥拉站在那里接受了这份好意。
等到安妮把围裙系在她的腰上,后退一步,双手交握在下腹,温顺的垂下头颅之后,她才开口问“已经完成了?”
安妮回答道“如您所愿,我的夫人。”
维奥拉真心实意的高兴起来,她愉快的说“好极了,我要一份肉桂茶,还有柠檬冻——”
“——香草酱,蜂蜜,坚果碎,不要奶油。”安妮熟练的接口,她温柔的看着每当做好一份作业,就要用最喜欢的点心犒劳自己的小姐,或者该称呼为夫人“您回到庄园就能看见它,夫人。”
尽管非常期待淋着蜂蜜与坚果碎,点缀着香草酱的柠檬冻,但维奥拉回到庄园所做的第一件事依旧是洗澡。
萨尔维家的主管家已经服侍这个家族超过二十年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询问消失了大半个夜晚的主母,只是干脆的指挥着男仆将马车牵回后院,女仆准备热水与熏香,而他自己则亲自捧着毛巾与干净的内衣站在了维奥拉的浴室外。
“劳伦斯,这应该是我的工作。”维奥拉的执事费米匆匆赶来,他要比劳伦斯年轻的多,经验也更少,他还没能像他一样习惯于每天四个小时的睡眠,并且哪怕是在睡觉时也分出一只耳朵随时聆听主人的需求。
所以在劳伦斯开始指挥着大半个房子里的仆人动起来之后,他才惊觉自己应该在女主人的面前等候吩咐,而且在一切准备就绪,女主人已经入浴之后才匆匆来迟。
作为执事,这相当的不合格。劳伦斯面无表情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目光在他露出口袋一角的手帕上停留了一秒——费米立刻紧张的把那块手帕塞了回去,但这又让衣袋鼓起了一条很不美观的褶皱,这下劳伦斯彻底皱起了眉。
劳伦斯今年四十二岁,深刻的五官让他的面孔看起来端正而严肃,鬓角已经开始灰白,但他的脊背依旧挺得笔直,燕尾服没有一丝褶皱,是个相当富有魅力,且长相十分传统的英俊男人,费米比他年轻二十岁,但在他面前青涩的像一枚食之无味的果子。
劳伦斯用眼神逼迫他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不只是鼓起的口袋,还有领口的那枚领结,它是歪的。如果不是正站在女主人的浴室前,他会用更严厉的态度去教导这位年轻的后辈,不过这样就够让费米紧张的了,他整理自己领口的动作大的差点把衣领扯开了。
费米越整理越沮丧,劳伦斯站在他面前像一面镜子,他越是对比着他,就会越多的发现自己身上不对劲的地方,到最后他简直不敢鼓起勇气要求劳伦斯把毛巾给自己了。
但劳伦斯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就和他换了位置。无论如何,他是维奥拉夫人从科利诺拉家带来的随身执事,他想私密一些的事情夫人更愿意交给他去做,而劳伦斯只要确保他不做错。
费米接过毛巾和夫人的内衣,像劳伦斯那样笔直的站立在门外,这个他倒是做的很好,他一直站到门打开了一小半,安妮站在门后,示意他把东西递给她。
他借着将毛巾递过去的动作做了个手势,安妮飞快的和他交换了一下眼神,沉默的关上了门。
十分钟后,维奥拉穿着柔软的丝绸睡衣,用毛巾包裹着湿淋淋的头发坐在了自己的卧室里,享用着冰凉微酸的柠檬冻,香草与蜂蜜复杂甜蜜的香味充斥着她的味蕾,而坚果的油脂也让柠檬冻的口感变得更加丰厚,她满足的享用了整整一份柠檬冻,才端起自己的肉桂茶,转头看向一边端着茶壶的费米。
“已经准备好了。”费米立刻说。
“好极了,五个小时后叫醒我。”维奥拉说,她喝了一口肉桂茶,在甜美温暖的香气里沉入了睡眠。
为了接下来的事情,她可得有着充沛的精力才行。
于是,当弗兰克结束了与警署的秘密谈话,拒绝了俱乐部的邀请,应付完其他家族的试探,一身疲惫的回到家后,看见自己刚娶回来不到半年的妻子正坐在小客厅里喝茶。
她的黑发高高的绾起来,发髻光亮如漆,带着一个镶嵌着翠榴石的珐琅发夹。穿着黑色的长裙,款式简单而低调,只有胸口带着一枚同样镶嵌翠榴石的胸针。
她的面前摆满了茶点,看起来正要开始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