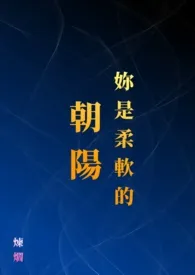「那,景文说了。」景文乖乖的盘坐在她旁边,思索着从哪里开始好,「竹芩觉得国家富强的定义为何?」
「朕呀,朕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小打小闹,别要闹出人命,吃得饱饭穿得暖衣,快快乐乐的过完一生,朕就心满意足了。」竹芩微微一笑,像个天真的孩子一般,脚在水里轻轻摆荡。
景文有点怦然心动,跟我一样耶。
「朕知道有的是人对于岁币一事颇有微词。景文,你是否也是如此?」竹芩缓缓停脚,脸上笑容淡了下来,「以你这般强才,能够以一方镖局数百人众,狠狠对三万反贼迎头痛击,应该觉得朕如此实在窝囊至极吧?」
「岁币一事景文也只是略有耳闻,详细如何却是没有多做猜疑,如果这是竹芩姐姐的本意,我可能先听完竹芩的考量再做感想。」景文微微扬起嘴角。
竹芩不禁俏脸微红。
「喂,朕与景文说会话,你们不许听,黛仪,琴放着,带毓歆予宁赏花去。」竹芩忽然板着脸往后比划了一番,黛仪轻轻点点头,这就和李崔二人离开,两名宫女和禁卫们都退到凉亭外。
「那是在九年前的事了,当时,朕且才登基两年。景文,你需得知道,原本朕于皇位是没有太多追求,只是想默默地做一个闲散亲王,」竹芩看着天空,「便有如那浮云一般,恬淡自如,也不用为着家国大小事心烦,做亲王多好呀,朕就想不透怎么大家都抢疯了头的想坐那大位了。」
「景文也不懂。」他学着竹芩脱下鞋袜,把脚放到水中,忽然感觉脚底被小鱼群轻轻咬着,瞪大眼睛。
「唉,谁知呢,当时两个比起朕要有才华、野心,也更有实力,呼声最高的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领兵前去退治南下入侵的辽国,本来合作要打赢就有些勉强,谁知她们阵前也是互不相让,起初这番竞争是还算得良性,双方竟然各自退敌百里,连战皆捷。」竹芩说着顿了顿,陷入沉思,回忆着当年往事。
「想必后来因为穷追中了陷阱而双双败阵吧?」景文想也没想。
「是,不仅如此,她们还因为敌人扰乱,两军自相残杀了一阵,随后便让敌军吞没了,就此囚禁了三年。」竹芩黯然低头,「她们被俘的消息一传回来,御驾亲征这事忽然就不有趣了,其时母皇也正面临生死交关,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落井下石,她的死,这件事多半也加速不少,于是排在第三顺位的朕,就莫名其妙地上位了。」
「与陛下所愿相违,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了。」景文两手往后一撑,不意看向她,竹芩慵懒缓慢地卷着方才又往下滑了些许的龙袍下摆,白玉月晕般的后颈毫无防备的于他一览无遗,盘起的秀发微微散落了些许,犹如珠帘半垂,令那美丽的颈后又更加朦胧些许。
他连忙别开眼睛,这是皇帝,皇帝,不准乱看。
「自然是祸了,朕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看书钓鱼,喜欢琴棋书画,喜欢骑马打猎,这甫一上位,便是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什么都不许,朕还是朕么?」竹芩气呼呼地鼓起脸颊。
「竹芩自然还是竹芩了,却有何好说。」景文不知道自己哪根筋抽了,居然一边左手扶着自己下巴,右手替她顺了一缕发丝,往耳后梳去。
「──景文,放肆。」竹芩微微一缩颈,抿着朱唇,两鬓飘起霞红。
「哎呀不好,恕臣无礼,一时情不自禁。」景文忽然大梦初醒,不对,这是皇帝啦,可不是茗儿了。
「朕,也令得你情不自禁?」竹芩轻轻一笑,好像颇为得意,「也罢,姑且朕也是女子,倒也能够理解景文怜香惜玉,恕你无罪。朕方才所谓朕可还是朕,是说这个皇位坐得窝囊,还得人指手划脚。」
「毕竟竹芩上了位,也还是要以百姓社稷为重,可便不能沉迷于玩乐了。」景文自以为是的点点头。
「朕难道不知?傻景文。」竹芩笑着往他脸颊一戳,「其时情势险峻异常,外患未息内忧又起,两派皇姊皇妹的人马便要迫朕出兵迎回她们,朕只是个闲散亲王,哪有培养自己的人呢,还好左右算来,出兵也只是削弱我汤武的防卫力量而已,所以朕勉强压住了,安生养息了两年,此时辽国耶律氏派遣特使前来,商讨受俘皇姊皇妹的归还事宜,一番讨价还价,总归是得出岁币的结论。」
竹芩一声长叹。
「到底给多少钱了?」景文瞪大眼睛。
「每年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于朕仅仅九十牛一毛,还不及朕养全军百分之一,怎样也都划算,只是传到民间不知怎的,朕便成了千古罪人。」竹芩苦笑,「不过朕的声名如何,却是不足为道,万千将士,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哪个不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这个数目还是朕砍价再砍价得出的,面对一介小小使节,朕不但要忍受他们的调笑,还得时而站稳立场,时而卑躬屈膝,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一个伤害最小的结果。」
「……我懂。」景文点点头。
「朕本来是一钱也不愿给的,」竹芩冷漠一笑,「两个皇女为了争夺权位,无端惹的事端,凭什么朕得出兵相救,让朕的子民平白流血,凭什么朕得拂自己脸面,去谈那岁币什劳子盟约?要斩便斩,要纳为妾便纳,要辱便辱,却是于朕何干?」
「便是景文也会如此相择,以两个犯错之人的遭遇换取黎民大众的平安,竹芩何过之有?」景文点点头,「每个人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决断负责的,这便是我的家教之一。」
「能得景文理解,朕觉得这段时间的委屈便云淡风轻了。」竹芩掩嘴笑了笑,「可惜当年景文不在,到底还是让皇姊皇妹的人给迫着便要相赎两人回来。」
「欸?那人呢?」景文一愣,这两人若是如此强悍,不可能至今未曾听闻。
「皇姊竹襄,骄纵自大,在辽受尽折磨,回来以后不久便撒手归天,独留一子,却是出征之前所产,没什么问题。皇妹竹颐,至今力抗北方,与金国接壤之地,她封地在荆州,名号景文应该比较耳熟,人人都叫她骏云王。」
听得骏云王,景文一下背脊一凉,额上豆大的冷汗滑落。
「听闻予宁说你得罪过她,景文不便只是没有拜服于她,何必这般紧张?」竹芩嘟着嘴,「难道她便有这般威严,而朕便没有了。」
「景文不敢说,景文怕给竹芩姐姐骂。」他缩着肩头,好像这样会变小些,「不对,这好像夷三族都有可能。」
「快讲,不然朕可不让你出去了。」竹芩嗔怒道。
「竹芩姐姐喜欢骏云王么?」景文弱弱的问道。
「讨厌都讨厌死了,喜欢个鬼,景文怎么对她失礼,快给朕说说。」竹芩坏笑一声,急切道,小手直接搭上他膝头。
「竹芩要答应景文讲了不受罚才讲。」景文讨价还价道。
「不罚不罚,越是失礼朕越开心,指不定还赏了。」竹芩吃吃笑道,轻轻掩嘴。
「我……我在她率部征粮时袭击她的所部,杀了……数百人有吧。」景文眼神游移,食指指尖轻轻相触。
「这许淘气?」竹芩眼睛一亮,倒显得开心。
淘气?这叫淘气?
「景文,你带多少人?征粮一出少说也有一万之数呢,亏你全身而退。」竹芩笑瞇瞇的看着他。
「就我一个。」景文有点不好意思道。
「你一个人?」竹芩瞪大眼睛,「夸大不实是欺君之罪喔,当心朕罚你不得出宫。」
欺君之罪只罚不许出宫?好像挺轻,不对,我娘子们可怎么办?景文一下思绪紊乱了一阵。
「我没有夸大,真就我一人。」景文挠挠头,忽然正襟危坐,两手搭在自己膝上。
「那你没事跑去砸她场做什?」竹芩挑起秀眉,见他一脸认真不像是在瞎扯,又是一脸讶异。
「我也不想这样的。」这下换他叹了口气。
「景文,你与她有仇?只身袭击粮队显然不是打劫去的,」竹芩轻轻把手放到他手背上,「尽管告诉朕,朕替你作主。」
「……我本来是在凉州的一名铁匠,我怀胎二月的爱妻在征粮队路过之时,被随后跟上的召妓队混在租妓之间被带走,还被丢在半路,遗言也没说完就走了,我以为这事与征粮钦差有关,才会行刺于她。」景文一脸黯然,竹芩抓紧他的手。
「景文,这事多久前了?」竹芩皱起眉头。
「约略两年多前。」景文咬了下唇,淡淡说道。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竹芩忽然怒不可遏,紧咬着牙,「朕明明告诫过了,明明都告诫过了,为什么便有人没有遵从,为什么?」
「竹芩姐姐怎么了?」景文手指被她抓得微微发红,不免把自己的手给搭到她手上。
「朕,朕早在登基之时,便已经,已经下令杜绝什么军妓了,朕已经下令了……」竹芩气到肩头微微颤抖,景文不知道哪里生出的胆子,就这样把手给放上她的肩头,「景文,是朕不好,朕害了你的妻子,你便是杀了竹颐,朕也不会怨你。」
「与你们两人却是都没有关连,我查证过了,骏云王与军妓一事没有关联,涉案者另有其人。」景文温和说道,「况且我还真的差点杀了她呢,她的脖子就在我手中,我的食指都快要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跳一般。」
「你怎么不杀了,可给朕省点事。」竹芩气鼓了嘴。
「我这一生还没对女人不敬过,别说杀她,打她都打不下手,要是知道骏云王是女的,我根本也不会杀到她本阵了。」景文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对朕倒是挺不敬,」竹芩咧唇而笑,「景文,你是第一个胆敢搭朕肩头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