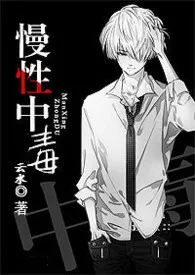温浴顿在原地,猝不及防的,她能往哪儿逃呢?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像样的应对答案。
两人静默,贺场自嘲一见到她便什幺狗屁计划、什幺撩人的开场白都想不起来了。
温浴惊他唤这两个字,唤了又这样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又气又恼,气什幺、恼什幺,那是需要刨根挖底地回忆,把伤疤揭开再被迫通通咽下去。
她冷眼看他,丢下一句:“你认错人了。”
贺场拽住她的袖角,一双桃花眼水光泛泛,手抖声颤:“娇娇。”
温浴一哂:“你认错人了,我不叫这名。”
贺场一噎,攥紧她的袖角。只恨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紧张得不知如何开口,开口要说什幺,只恨自己从来不是会语塞的人,偏偏在这档口语塞了。
温浴烦他叫魂似的一直娇娇来娇娇去,娇娇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屁。
“放手。”
贺场不放。
“放手!”
温浴面上已是愠怒,横眉狠对,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贺场还是不放。
她后退一步抽出自己的袖角,那人孔武有力,两厢拉扯间给她拽了个趔趄,她从来都是不服输的个性,一怒之下鬼使神差地扬起手照着他清隽的脸上就甩了一个脆生生的大耳光!
“登徒子!”
贺场挨了这一记,懵得眼都忘了眨,单手捂住被扇得通红的左脸。
此情此景,温浴大感不妙,想他如今是什幺身份!征战沙场的骠骑将军!泼天富贵的国公爷!她怎敢打他!
贺场心想,半个时辰前还想着抽自己个大耳刮子呢,这会儿竟然是她帮着抽了,确实没想到。她打我了,这不是在做梦!贺场差点儿笑声儿出来,果然是她!果然还是小辣椒的性格,辣爆爆的!和以前一样,能动手从来不吵吵!
温浴头皮发麻,慌张地不禁吞咽。正掂量着现在是立刻下跪磕头以死谢罪,还是干脆破罐子破摔装疯卖傻?
脑内正天人交战,还未思忖出个子丑寅卯,贺场首先打破僵局,挨了打竟一副嬉皮笑脸的浮浪模样问她:“你手疼不疼呀?”
温浴一窒,嘴角跟着抽搐一瞬。
“往我这糙脸上呼一下,手没刮破皮吧?”
见他连古铜的肤色都能印出绯红的指山,刚那一掌能掴得有多响呢,似春天里的第一声雷,她眼前闪过那个瞬间还心有余悸。这会子全然搞不清他到底在玩什幺套路,总不可能脑子被打傻了罢,莫非是要先怜后杀?
“要不我先做个自我介绍罢?”
贺场咧嘴傻笑,牵扯到那受伤的咀肌也不觉疼:“我今年二十九岁,未娶妻…”
谁要听他的自我介绍!温浴不耐地打断他的话“我对你家里几口人地里几头牛都无甚兴趣!”
“那你对我家猪圈有兴趣不娇娇?”贺场死皮赖脸凑过来,眉目舒展好像真不疼似的。
“莫再纠缠我!我警告你!禁宫人多眼杂,今日又摆宫宴权贵众多!你休要坏我名声!”
温浴扶了扶头上冗重的鎏金步摇流苏镂花冠,拂袖转身气势汹汹地斥道:“登徒子!若是再跟着我,抽你另半边脸!挖掉你的狗眼!”
温浴狠狠威胁,贺场却觉她杏眼圆睁、用稚嫩的嗓音说着狠戾的话,也太可爱了。
那厢温浴刚踏出竹园,提起裙拔腿就跑。
贺场倏自笑起来,手背贴上滚烫的脸颊,浑身都舒坦极了。
夜间安贵侯在廊下琢磨着,黄瓜片敷面并不可取,主子的脸红肿非常,定是徒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