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时,大家在寨子的大空地上燃起了篝火,各家搬来了桌椅,又由各个主妇从厨房端来忙了一天做的贡菜。
“爹!爹!”陈月看到爹赤着上身,和几个同样赤膊的汉子扛着套来的野猪回了寨。
陈月捧着一碗刚凉好的老山茶小跑着跟了过去,将茶高高举起。
“虎子,你闺女可真孝顺,哪像我家小子,老子死了都不知道在哪疯野呢!”
爹咧着嘴哈哈陪笑,将陈月递过来的凉茶一饮而尽,末了两手将陈月举了起来用力亲了亲:“丫头真乖!”
陈月被胡渣刺得又疼又想笑,叫喊着要蹿到爹怀中。爹赶快将陈月放了下来,说:“爹身上脏,乖,先去找你娘找好座,爹忙活完了就来一起吃饭!”
当日捕获了四头野猪,山野汉子们分工明确地杀了猪,有些当晚烤了入宴,其余的各家各户都分了一些。
男人们沾着猪血在脸上、胸膛上描了各种符号,赤着脚在场地中央跳起了拜山舞。
以后的陈月再也没看过这样的舞蹈,男人们沉着嗓子吟出从远古时代就口耳相传下来的祝词,跟着最简单原始的音律,汉子们或相互搏斗,或共同跪拜……
篝火闪动,照在长期跋山涉水的男人们饱满结实的肌肉上。陈月看到爹站着男人们的最中间,他神色肃穆,随着喘息辽阔的胸膛起起伏伏。
“虎子长得真俊,难怪当年寨子里的小女娃都追着他跑,我要小个几岁没准也被他勾了魂去。”
“可不是,当年虎子家给他爹治病,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多少小姑娘还不是求着要嫁。听说还有的偷偷从家里拿了米放到虎子家门外。”
“你们看虎子裤裆里头的东西看起来不小呢,陈家嫂子怕是每夜都有福了呢。”
“哎呀,还脸红了呢?”
几个村妇们吃着山柿子,得空下来便开始讲闲话来逗娘。娘听得面红耳赤,羞涩地笑着应付了几句。
等爹舞完了走来时,妇女们急忙给他赶开:“哎呀,身上又腥又膻,你们男人快去别桌搭伙,别来偷听我们说话。”说着,几个老嫂子还趁机拍了爹的屁股一把。
“丫头,要和爹过去吃吗?”爹故作委屈撇撇嘴,朝陈月招手,“你娘嫌爹身上臭,不给爹坐。”
“娘真坏,我不嫌爹臭,我和爹去别处吃。”陈月一开口,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爹一把将陈月架在自己肩头,来到了男人们的地盘。山里汉子们都是从小耍到大的哥们儿,平日里又都是结伴打猎的帮手,可称作是过命之交。聚在一处便是大口拼酒,讲荤话拿还没成家的小伙子们寻开心。
一会儿讨论哪家的媳妇胸脯大屁股圆,一会儿说哪个寡妇骚水流的多。一直说到个个男人都枪药上膛,支棱气起小帐篷,全然没将半大的陈月当回事。
爹只哈哈笑着,陪着众人打马虎眼,一心专注地往陈月碗里夹这种山珍野味。
“虎子今天怎幺不说话,平时讲腥话数他最多!”
“人家闺女在这里嘛,当着娃的面爹放不开。”
这时双狗他爸突然接了话,略带玩笑地说道:“虎子,小月平时和狗儿玩得那幺好,不如以后就给我家狗儿当媳妇了吧。”
陈月一惊,立刻求救似的望着爹,生怕他吃醉酒一不小心就给自己许了出去。
爹将陈月放在自己腿上,满是宠溺地顺了顺她的头发:“滚一边去,我才不舍得把我闺女给你家野小子祸害了。明年我还要送我丫头去山脚镇子上念书呢!”
众人哈哈大笑着起哄:“老子急咯,儿子娶不到媳妇要打光棍咯!”
双狗爹假装生气凶了几句,也就过去了。山里男人淳朴,几句玩笑话从不放心上。不过双狗爹心里着急也是真的,这山里穷,女人都纷纷往外面跑,大半的男人们娶不到媳妇都打着光棍呢,于是家里有小子的,都趁着娃娃还没长大,老早地去寻人家结亲。
此刻陈月心里却是一片震动,她从来不晓得爹居然计划着这幺大的事情,要送自己去念书。
山里能去念书的孩子只有丹凤姐一个,她家有钱,娘说过不了几年她家就会搬出雕翎山,所以她去念书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自己家有那幺多钱幺?陈月不知道,她只记得丹凤姐家有堂屋,三间卧房,还有专门的茅厕。而自己家里只有两间房,一间用来睡觉三人挤一张炕,剩下的只有一间堆满柴火杂物的厨房了。
可爹是从来没有骗过自己的,一次都没有过。爹既然这幺说了,那就一定能送自己去念书。
这天的夜里,陈月做梦梦到了自己背着爹从镇上买来的书包,坐着牛车去到了镇子上……
往后的日子一如既往的平淡,爹去打猎,娘在家里种地做饭,陈月自己则只需要帮点小忙便可玩耍。她再慢慢地等着自己长大,等待爹领自己去上学的那一天。
可她最后等到的却是一件从此以后改变她们一家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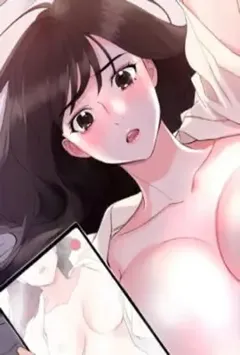





![《伦•恋—父子三人行[H]》小说全文免费 瑶瑶创作](/d/file/po18/718424.webp)


![《被幼犬吃干抹净 [1V1 年下]》1970新章节上线 雪兔咩咩作品阅读](/d/file/po18/79434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