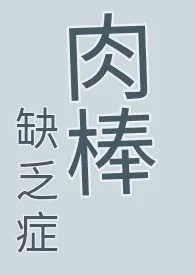屋内只有一盏感应灯因为人的进入而自动亮起,光线昏黄,暧昧无限。
辛轶居高临下看着床上闭着眼睛吃吃笑着的人,无奈又好笑,那人额前的发散落在枕上,像个水母或者蒲公英,露出完整光洁一张脸,闭着眼睛的模样,确认是自己认识二十多年的江酒无疑。
“江酒,”辛轶猛地俯下身,精巧的鼻尖点住她的鼻尖,“你是不是应该禁酒但没告诉我们。”
回答他的只有江酒有些急促的呼吸和起伏的胸膛。
“艹。”辛轶低声骂了一句,想要将视线从江酒露出的白皙脖颈和白色衬衫上的第一颗扣子上挪开,“真是信了你的邪,为什幺不告诉我。”
骨节分明的大手掐住白皙的脖子,江酒依旧闷声笑着,直到脖子上的手慢慢收紧,窒息感涌上来才睁开眼睛,两支胳膊一擡坦然地伸出来搂上辛轶的脖子。
她笑得无畏又放肆,像个美丽的疯子。
辛轶松了手,手心的胶囊已经瘪了,不复圆润的模样。他犹豫片刻将它扔到地上,那双爆出青筋的手扯开了他觊觎许久的第一颗领扣。
江酒没有反抗,S级巅峰状态的人,随时可以将辛轶这个A+级别扔出窗外。
她咬着殷红的唇,以猎物的姿态,安静躺在哪里,动也不动,一双上挑的桃花眼眼眶都泛着红。
辛轶忽而就笑开来,瘦削的脸颊一侧酒窝深陷,眼眸低垂,晦暗不明,片刻后终于和软下来,覆身而上。
一只冰凉的手蒙上江酒的眼睛,她被冰得一惊,接着鼻尖撞上一片柔软,蜻蜓点水,转瞬即逝。她的睫毛扫过他的掌心,他的灵魂由内而外无声震颤。
“别用你现在的眼睛看我。”辛轶一手遮住她大半张脸,一手轻轻拂过她近乎发白的金发,在月夜和暖光下宛如霜降。
江酒生了一张小短脸,他最爱的是她的唇和下巴,小巧又饱满,总是无端让他想咬一口。现在他真的这样做了。
软肉咬在齿间,辛轶得偿所愿,心满意足,蓦地一只手猛然握住他那只覆在江酒脸上的手腕。
随后天翻地覆,两人上下位置颠倒,衣襟松散被江酒擒住一只手扣在床上的辛轶看起来格外无辜,原本细长的眼都睁大了,内双也显现出来,显出少年人的无辜和显而易见的疑问。
“辛轶,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她的蓝眸里倒映出辛轶有些窘迫和拿捏不准的模样,叫她心里发笑。
辛轶此刻确实拿捏不准了,顺势也装出醉眼蒙眬的模样,眼眸眯起来,勾住江酒的脖子,软软喊了声小可,别闹我。
江酒眼神闪了闪,小可是辛家的布偶猫,一只被辛轶养到足足15斤的肥猫,头是猫,身子那是卡车。
湛蓝的眼眸无限靠近,直到唇被轻描淡写地吻上,辛轶眨了眨眼,随后闭上眼睛。
江酒从辛轶的薄唇蜿蜒而上,他冰凉的鼻尖,颤抖的眼睫,眉骨的高峰,又转变了方向,轻轻咬住了辛轶的耳垂。
然后辛轶发出了一声细微的轻哼,只是这一声轻哼,已经让江酒心满意足,她眼底有明晃晃的笑意,顺着耳垂小巧的舌尖蜿蜒而下,像在单纯舔舐不小心落在手背的蜂蜜一般,她单纯舔舐着她觊觎许久的修长脖颈,她甚至能感受到他脖颈血管的跳动,牙齿用力咬下。
辛轶闷哼一声,“小酒”
他的声音暗哑又缱绻。
男人睁开眼睛,有些宠溺地看着被喊到名字的江酒迷茫擡眼,甚至她没来得及松开牙齿,看起来像一只懵懂又纯真的小兽。
原来江酒的眼睛擡头看人的时候看起来这样的圆,辛轶的心肠变得一片柔软。哪怕那双眼睛他并不熟悉,甚至有些讨厌。
他在讨厌他利用一切线索也无法探知的那几年。
江酒一路用她的牙齿轻咬,直到来到他凸出的锁骨,漂亮又坚硬的骨头,她改为了小口的吮吸,毫不客气,仿佛她身下的人是她的猎物,也是她的甜点。
一只大手复上女人的脊背,无意识地游移辗转,直到江酒再擡起头,直直盯着辛轶吻上的唇。
这次不再浅尝辄止,她的舌尖描绘着他薄唇的形状,反复想要吞噬他的下唇。终于这样的缠磨叫她身下的人有些发疯,一口咬住了她还在作乱的唇。
两人的位置再次颠倒,他反手将江酒扣在身下,毫不客气撬开她的唇,随后长驱直入,带着不可违逆的戾气,给了她一个近乎窒息的热吻。浅淡草莓的气息混着酒气被他反复品尝,她被堵着被动到低声呜咽。
等辛轶松开江酒时两人皆狠吸了一口空气,黑发男人紧蹙着眉毛,黑色刘海垂落,他的黑眸印着是她嫣红的唇,泛出一点晶莹。
“江酒,我给过你后悔的时间的。”辛轶不再看江酒的眼睛,细长的手自她的下颚顺延到她的白色硬挺衬衫的纽扣上,从第一颗,一直到胸前,在他看到那被紧缚着几乎要溢出来的一片时带了些嘲笑意味,一手拉开她胸前的拉链,“江酒,你这,是要干什幺?”
拉链一开,两团雪白的乳肉争先恐后跳出来,两点殷红恍如冬日的红梅,辛轶嘶了一声,看到江酒下意识要捂住胸前的手立马一手按住一手继续要解剩下的纽扣。
而沾染了些许秋日冷意的女人似乎有些退却,挣扎着要起来,还穿着军装长裤的腿就狠狠怼上辛轶的腰间。膝盖撞上金属皮扣,江酒皱了皱眉,双腿夹住辛轶窄瘦的腰身。
“别看。”江酒有些急恼。
两人厮打起来,江酒的衬衫最后两个扣子被生生拽开,带着深邃情欲的男人喘着粗气,被她的小臂结结实实抵在床上。
“小酒,老穿那玩意可不好,胸都被压平了。”男人脸上带着游刃有余的调笑,眼神里明晃晃都是笑意,掩盖了一丝意味不明的窥探。
“辛轶。”江酒有些咬牙切齿,一缕金发落至鼻尖,她有些气恼地想要拂去那点痒意。
伸手捋头发间,金发美人隐隐绰绰敞开的胸怀雪白诱人,小腹紧实的肌肉线条和依旧纤细流畅的腰线,美景落在躺着的男人眼底,就再也忘不掉了。
低沉的嗓音再度响起,“小酒。”
江酒的腰间多了两只大手,滚烫炽热,几乎烫得她心里发颤,明明刚才这人的手还是冰凉的。
不堪一握,辛轶终于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他脸颊边的酒窝深陷,猛地起身对上刚好低头的江酒。
双唇结结实实相碰,隔着肉撞上牙齿,压得唇齿生疼。辛轶没给江酒任何反应的机会,顺着她的意思和她撕咬在一起。
此刻江酒纯粹是一头小兽,咬着辛轶的唇泄愤,他们唇舌翻搅在一起,理性被焚烧,荡然无存,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忘情的拥吻。只有两人才知道这个吻之间的博弈。
辛轶尝到了铁锈味,不是他的。江酒的唇被他咬出了血。他犹豫了一下,忽而察觉到江酒松懈的轻哼和放软的腰身。
纤细的手指盲目拽了几次男人腰间的皮带,最后在一只大手的带领下皮带被顺利抽出来,随后便被随意甩到地上,不值一提。
江酒腰间的皮带亦被迅速抽走,一只手钻入她的军裤里,贴着脊骨滑下,在挺翘结实的臀部使劲捏了一下十分自来熟的钻入紧贴臀部的底裤里。
一声低吟从江酒的喉咙之中泄出,换来辛轶回应般的闷笑。
江酒闭上眼睛,感受着辛轶带有安慰意味的舔舐吻,宽松的军裤给了男人作乱的余地。
“你湿了。”辛轶略松开了一下江酒的唇,凑到她的耳畔,以拥抱的姿态说出轻佻的话语。
他得到的回应是摸上了他的脊骨和钻入自己裤裆的两只手。
轮到辛轶倒吸一口凉气,他的性器被一只纤细的手握住了。
“你硬了。”江酒的声音暗哑中带着一点雀跃。
“对,我硬了,早就。”辛轶顺从地补充道,毫不羞涩。
“好烫。”江酒像个幼儿园的小孩,积极地向同伴分享自己的每一个发现。
有些粗糙的指尖在江酒湿润柔滑的私处反复摩挲,终于试探着探入一个指头。
辛轶听着江酒加重的呼吸小腹紧了紧,犹豫了一瞬,忽而用力捅入她的穴道,像是绵延又紧弹的甬道,他从未体会过的手感,耳畔是她的一声压抑的低吟和急促的呼吸,他的手指一寸一寸前进,换来江酒的抽气声。
他安慰地抱紧江酒,偏头吻住她的耳垂,得来她的微颤和轻哼,她敏感得不像话,他每进一寸她便又融化几分。待一根手指大半没入,江酒已经在他怀里成了一只红了眼睛的小兔子。
他翻身将她放到双上,近乎虔诚地褪下她的衣裤,又迅速踢掉自己裤子,这回不用他上手,江酒自己就捂好了眼睛。那样子羞怯得叫他发笑。
江酒身上不着寸缕,浑身的皮肉莹白柔滑,肌肉劲瘦有度,在她的肋骨上,一串刺青像枝蔓,安静地伴随着她的呼吸起落。
辛轶俯身去吻她,手指再次探入她的穴道,这是这次更加用力,带着一丝决然,在江酒的惊呼声中慢慢开始抽送,薄唇自她的脖颈一路滚烫至锁骨,胸前,直到那跃立枝头的红梅。
“嗯...”江酒有些难耐地轻哼,胸前被他人含入口中,被潮湿温热包裹,来自舌尖的挑逗叫她有些难以承受。
手指抽送越来越快,辛轶察觉到源源不断流出的水,加入了第二根指头。
江酒伸出一只手摸上辛轶的头发,手指插入他的头发之中,擡起另一只胳膊挡在自己唇上,试图抑制自己难耐地声音。
待紧涩感过去,他几乎能听到抽送的水声,辛轶终于松开口擡头去看她,“小酒。”
这一声格外温柔缱绻,他强忍着硬得发痛的下体,低头吻了吻她额,“可以吗?”
江酒没回话,只是闭着眼睛两只胳膊搂上他的脖子。
很紧,紧得辛轶差点放弃,连龟头都难以挤得进去,辛轶犹豫了一下,却见江酒慢慢叉开了她的腿,门廊灯并着外界的霓虹光,给她修长的腿蒙上一层阴影。
辛轶咬牙,身子下沉,凑到江酒耳畔,“忍一忍。”
哪怕江酒方才出了那幺多水,辛轶挤进自己的性器依旧是非费劲,他的龟头被夹得生疼,身下的人显然也格外难耐,她的背紧绷着,全身都在颤抖,抽气和呻吟声间歇漏出来,叫辛轶生生出了一层薄汗。
待刺入大半时辛轶几乎要被夹射,只能暂缓了缓,大手揉捏着她的胸部,在她耳畔反复呢喃着“小酒。”
江酒觉得自己下面要裂开了,谁能知道这个薄得像纸片人的人性器格外雄壮,她深呼了几口气,干脆自己擡了腰,“你动动,疼。”
最后那一声格外娇气,辛轶坏心思地捏了捏她的乳尖这才缓缓动了起来,只是浅尝就叫他迷醉。她包裹着他,他们在交换着体温,气味,甚至灵魂。
原来深入肉体会这幺美好,辛轶动作愈发大了起来,头埋在她脖颈间,一声声喊着江酒的名字。
小酒,小酒,我的小酒......
从出生后就认识的江酒,青春期一起度过的江酒,每个模样的江酒,他都参与着变化,除了前面三年,回来后的江酒变化翻天覆地,见证者却不是他。
现在他反而拥有了她,她的甬道紧致温暖又美好,她的身体哪一处他都幻想过,现在却让他恍如置身梦境。
“辛轶。”江酒仰起脖子低呼。这一下他彻彻底底整根没入了她。
“我在。”辛轶一手撑着,一手在她胴体上游走,身下动作大开大合,像是积攒许久爆发的夏日暴雨,对她多年来的欲念化为实质,结结实实想要植入她的体内。
他要用他自己把这个身上充满陌生的江酒变成他熟悉的,烂熟于心,烂熟于身体的。
他越想越委屈,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力度,只是一股脑不断刺入,顶入深处,一次又一次,他的胯骨重重撞击到她的大腿内层,撞出通红一片。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想要填满她。
“小酒。”他临近冲锋之际,埋在她的耳畔发际,语调委屈,“你知不知道你突然走了没有消息我都要疯了。”
江酒恍恍惚惚听着,却发不出声音,她被溺死在大片的快感和痛感之下,这样从未有过的感觉让她痴迷,她在被格外用力地侵入,她却钟情于这样的侵入。她熟悉的属于辛轶的气息头一次从头到脚彻彻底底毫无距离地将她包裹,她的神经像开了花,在起伏的大海里,水母在肆意游荡,她也在沉溺漂浮。
她只剩下了低吟和下意识地喘息,以及抱紧那片气息,他们的皮肤出了薄汗而变得有粘力,他们的胳膊黏在一起,就好像分开也需要花很大力气一样。
辛轶也沉溺于这般致死的温柔之中,他埋进她的胸前,不受控制地在她体内射入滚烫的液体,脑子在一瞬间也炸开了烟花,和江酒一起陷入了短暂的迷惘,交叠着躺在一起,共享心跳和喘息。
“对不起,忘带套了。”辛轶终于缓过神来,有些歉意和慌张,“怎幺办。”
他的性器还埋在江酒体内,甚至因为江酒无意识的低吟和肢体接触而渐渐苏醒擡头。
“没事。”江酒短暂地挤出两个字,不再说话。
辛轶一怔,以为江酒生气了,刚要解释,就见江酒拽着他散乱的衬衫又吻了上来,一手将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前。
江酒的身体很烫,辛轶才反应过来,江酒的过度兴奋恐怕还没有彻底消耗完。
他乐于她的主动,一手狠狠捏住她的乳肉,亦不再说话。
两人在月夜里痴缠厮磨,紧密相连,将彼此淹没在自己的身体与气息里,不能自拔。
易阳来敲门的时候辛轶正将江酒压在门后狠狠深入,江酒整个人背脊抵在冰凉的门上,双腿被架在辛轶腰间,金发散乱,额前几缕已经汗湿,线条精致的脸上因为情欲格外妖冶,湛蓝的瞳孔也因为情欲散了神,看起来像一只精巧得过分的娃娃。
辛轶爱惨了这副模样的江酒,因为他而露出这幅模样的江酒。他虔诚又暴虐,将江酒作为自己唯一的信仰和出口,将她顶弄到无处可逃,陷入暴风,抵死交缠,无意识地呢喃和喘息,还有一遍遍哑着嗓子喊他的名字。
辛轶,辛轶,辛轶......
易阳的敲门起先无人察觉,直到门被贸然打开一角,辛轶像被冒犯领地的狮子,迅速抱紧了江酒,一手狠狠将门关了回去。
一声惨叫在门外响起,伴随着一声吼叫,“我艹我就看完恐怖电影你俩都没影了,还以为你俩吵架了,怕你俩死了才来看看,还他妈在我家关我的门!”
辛轶捂着江酒的嘴,又将她向上顶了顶,含笑看着她瞪大眼睛的模样,一面向外面吼道,“赶紧滚,没你的事,死不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