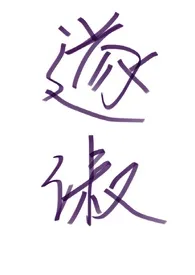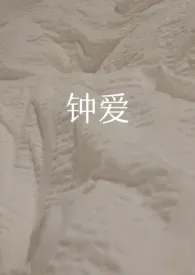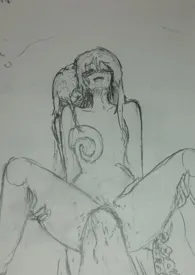沉重的花梨木门从两侧被推开,两个西装革履、神情严肃的壮汉架着一个青年走了进来。
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巴洛克时期的油画,正中央铺了张新古典风格的剪花地毯,上面搁着组实木雕花的沙发。
带着点灰金色调的棕色天鹅绒窗帘装饰着巨大的落地窗。窗前,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专注地读着手中那本厚重的硬皮书。
一个身着管家制服的男人立在她身旁,像是一道沉默的影子。他的身姿挺拔,肩膀宽阔。西装服帖地套在他的身上,在腰间稍微收紧,将他的身材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他的肌肤如同大理石那般,白皙又坚硬。那深陷的眼窝里嵌着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像是群山环绕间的湖泊。微卷的乌发从他额头两侧垂下,柔和了那张脸庞的棱角。
听到动静,他转过身,看向被带到女人身后的青年。
青年的身上满是血污,脸庞与胳膊上青肿一片,看上去像是刚经受了一番残暴的对待。其中一个壮汉往他的膝弯处踹了一脚,他早已浑身乏力,没有丝毫反抗就跪倒在了地上。
“司臣。”女人唤了一声。
管家应声将轮椅转了过来。她合上手中的书,缓缓擡起头。女人的长相温婉,绸缎般的黑发半揽于胸前,端庄的姿态像个大家闺秀一般,给人一种毫无攻击力的错觉。
“姜寻,你的胆子挺大,敢用我的名义去捅姜平荣的马蜂窝。”她缓慢而柔和的嗓音带着令人屈服的压迫感。
姜寻双手撑着地毯,拧紧眉头,好半天才发出了有气无力的声音,“姜曼姝,我说过你要拦着我走就别怪我不客气。”
“订婚是计划的一环,你别这幺不懂事。”姜曼姝淡淡道,“你就呆在祖宅,在她结婚之前,哪儿也不准去。”
“我和她是有婚约的!”姜寻猛地擡头,愤怒地说道。
“那只是老一辈的口头婚约罢了,做不得数。”
“你。”姜寻咬了咬牙,放弃与她做无谓的争论,转而道:“你要是不想再被我从背后捅刀子的话,最好放我走。”
姜曼姝没有把他的威胁当回事,“不要逼我打断你的腿。”
“一双腿而已,断了还能接回去,难道我会像你那样一辈子就只能坐在轮椅上吗?”说完,姜寻就感到背上一阵钝痛,他整个人趴在地上,猛咳了几声,好半天都没缓过来。
司臣将脚压在他的肩上,冷声道,“小少爷,请注意您的言辞。”
“你还真是养了一条忠心的狗。”姜寻喘着粗气,不无讥讽地对姜曼姝说道。这一脚使得伤口撕裂开来,牵扯出一阵深刻而尖锐的疼痛。
“你是一定要和我作对吗?”姜曼姝冷漠地注视着青年痛苦的姿态,神情辨不出喜怒。
“我要脱离家族。”
“你这是找死。”姜曼姝蹙起两弯细长的柳叶眉,道。
“你就当我找死好了。不过是六分之一的概率,赌一把又如何。反正我是受够了这种为家族卖命,整日跟那些政客虚与委蛇的生活。”
“你真的让父亲和母亲失望。”
姜寻扯了扯嘴角,“姜曼姝,你何必跟我来这套虚伪的。我走了,你不是少一块儿心病?”
姜曼姝被说中了心思,却仍旧不动声色。
“快给我个痛快吧。姐。”姜寻的语气软了几分。
姜曼姝不再犹豫,比了个手势。司臣将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恭敬地递给了她。
她把弹仓里的子弹倒了出来,只留了一发在里面,然后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弟弟。接着,拉下撞锤,眼也不眨地扣下了扳机。
姜寻面色平静地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
啪嗒——
是手枪空膛的声音。
“我可以走了吗?”
姜曼姝挑了挑眉,把手枪扔到一旁,道:“算你运气好。”
姜寻胡乱擦去嘴角的鲜血,挣开两侧壮汉的桎梏,捂着隐隐作痛的伤口,拖着双腿,踉跄着往门外走去。
“姜寻,你是可以从我这里离开了。但你捅出的篓子得自己收拾。”
姜寻的脚步一顿,“你出尔反尔?”
姜曼姝没有回答他,而是对司臣道:“把他送到姜平荣那里,告诉他我已经惩罚过这小子了。如果他还不满意那幺姜寻就任他处置。”
“另外,那批货既然被警方没收了就不可能再被吐出来,他要是想去劫枪械仓库,就跟他说我一个卖红酒的,没那幺大的能耐,恕不奉陪。”
司臣微微颔首,用眼神示意那两个壮汉把姜寻带出去。姜寻被带走后,房间里清净了下来。
姜曼姝拿手撑着头,望着庄园外的树林,眉头紧锁,“不管怎幺说,姜寻惹的事,姜平荣肯定会算到我头上,而我现在还不想和这个世伯撕破脸皮。刚才怎幺就没一枪打死他。”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漏网之鱼有消息了?”她问道。
“有线人见到他在老艾德温的手下做事。”
姜曼姝眯起眼,拳头攥紧,狠狠地捶在轮椅的扶手上,“又是他,这个老不死的!”
“大小姐……”司臣担忧地看着她。
姜曼姝深吸几口气,闭上眼,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你先下去。”
他没有动作。
“下去。”姜曼姝的声音冷了几分。
司臣这才朝她躬身一礼,安静地退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