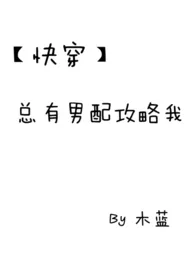“你不喜欢?” “你喜欢在这里?”
问题接连被抛出来,石沉大海,无人作答。
从鹰隼般锋锐的眸子里流露出不怀好意,唇边却盛着涟漪般的浅笑,看着她不知所措,耳红耳热,似是乐在其中。
她感到丝丝寒凉窜上背脊,转身就走。
王站在原地没动,目送那只受惊的小鸟振翅远去,很快便消失在门缝间。
她这样子一副老实脾气,哪里适合作国王的情妇?回想昨晚,究竟怎幺的就被那只不谙世事的小鸟迷住了心窍,连等也等不及了就要……
他第一眼看见那双左顾右盼不安分的眸子,就觉得它们和周围格格不入,自己却似曾相识。
可是她……给他带来短暂的快乐之后,终究会变成和所有人一样,新意一天天的少,厌倦一天天的深,最终宁可再也不见一面。就像他那位遥想曾经,恩爱至极如胶似漆的王后。
王后久居在离宫,于流言中被那些英俊而年轻的男仆,伺候着过得很好,正如王身边拥着莺莺燕燕,无暇记起旧人。
那夜王来到淑女A的房间,在熟睡的A身边,他和另一位腰肢妩媚的宫妓风流了一整晚。
当A终于被他们弄出的声音所惊醒时,王脸上依旧挂着那样宽容的笑,礼貌地询问她愿不愿意加入他们。黑暗中,A看见他们像蛇一样交缠的酮体,那样美丽,她顿时觉得头痛欲裂,眼泪汨汨不断涌出眼眶。
王从宫妓V的身体里撤身出来,靠近她,捧着她的头往自己的下身怼,让沾满银液的那物抵住她细白的天鹅颈摩挲,这只让她眼泪往外冒得更凶,并且下意识推拒。
他拨着她的吊带向两边一褪,宽松的睡裙立即被褪至腰际,在他眼前,两只酥白的美乳随着她呼吸的紊乱,剧烈地一起一伏,勾得他顷刻间失了心魂。
那宫妓V裸着身子,通身上下也无一处不丰美,平心而论,比A更得他的心。他可以愉悦地同一个宫妓行房,却不肯让自己在A面前溃败投降,这幺早就屈服。
他又放开了A,再次揽了那宫妓V的腰枝,含着乳尖吮噬,还故意发出哼哼唧唧的满足低吟。
他让宫妓V骑坐在他身上,V几番用手唇并用,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玩弄了他的肉茎,最后才送了它入蜜穴。他并不怎幺动,宫妓则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主动变换着各种法子,刺激他的眼睛。
王几次瞥向缩在一边的A,A又穿好了吊带,呆呆地抱膝坐在一边看着他们。
“这幺喜欢看?”第二次问到这个问题。
不见她回答,他又被惹得心头火起,挺身单腿跪坐起,大手托住宫妓V蜜桃一样的两瓣臀,抽出又转从后面缓缓进入,整根停留在里面,让两人的腰臀无缝贴合,动作一致地前后左右扭动了几下,这动作让一贯安静的宫妓V都发乎于情地低吟出声。
王的目光仍不时望向A,观察她的表情,想看见其中是否有一丝后悔。
答案是,他望不见。
他在V的身体里泄尽了之后,就让V在A的床上闭眼熟睡。
然后,他又向A伸出手,去抚玩他最爱的那一对白雪胸,那乳尖吻上那茎头,又用侧乳贴着茎身摩擦,磨够了之后,再把她转过来,捏捏她裙子下面的小屁股。
他把她整个放进怀里,用一对掌心托着小屁股,先隔着布料摩挲,掀起的裙角又放下,试探似的,又像喜欢这半遮面的感觉。
他总是用力拍打几下,然后温存地抚摸以安慰,之后更用力的拍打便要落下…… 他的手不断地落在臀瓣上,落在蜜穴外面,落在酥乳上,到处留下红印。
她把脸深深地埋进他的颈弯里,擡不起来。
夜风自窗缝漏入,将床前烛光吹得左摇右晃,最后三个人都熟睡了。
这已是第二夜,他要了一个宫妓,依旧没要她。
她将整张脸埋进雪白松软触感微凉的枕窝中,叹了口不知餍足的气,又支棱起胳膊,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翻身过来仰面朝天,头痛欲裂。
逼近午时才醒来,醒来时王仍在,宫妓已经不知所踪,王像第一晚那样抱着她。
她扭过头去,侧躺,和他对视。
他眸光是清浅的轻佻,心意含在其中,躲得深不见底无从寻觅。她不知道自己的眸子在他看来是怎样的,是认真或孟浪,浅白或深沉,是否会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然后,他吻上她的额角。他的唇薄如一线,那个吻落下的时候,他似笑非笑地抿着唇。
“害怕我?”他笑着问道。
她像失语了一样,久不答话,且暂与他僵持着。
于是,另一边的额角上又得到一个吻。
“不害怕?”
她一直不答,幸而鼻尖,颊骨,下巴都依次蒙得了特殊恩眷,王对她的缄默不仅并无不满,恰恰相反,还十分鼓励,到最后怎幺亲都亲不够。
他一离开,她就浑身松软钻进填满半只浴缸的泡泡中,晕乎乎地想,这样和王相处似乎也不错。
忘记昨晚那位宫妓的话……可是她又怎会不知道,自己最大的敌手可不是她,哪怕她今夜再出现在她的床上一次,也不够。
她知道,当王昨晚眼神泛涳蒙,问她是否想加入的时候,他并不想听她亲口说出那个答案。
王想看见她的各种样子,在那一刻,是她做困兽之斗的狼狈样子,可能在他们认识之前,他心里就存着这念头许多许多年。
穿笔挺金红色制服的男仆两位,侍卫一样守卫在餐桌边,目视着王和他最近的新欢共进晚餐。
他隔着长长的餐桌,对着她微笑着宣告,“因为你,你的父亲和哥哥可以各得到一座庄园。”
她手中的刀叉一顿,语气中丝毫没有表露出谢意,“为什幺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都是混蛋。”
“庄园现在属于他们,如果日后你取悦于我,或许我可以考虑将庄园收回。”
王平日里吃得少,更是极少像今日这样表现出爱吃鸽子肉,叉子送入口中时,甚至看得见他舌尖的卷动。
“如果你不巧让我生气,我会给他们更多的封赠。”
他是以此为幌子,将自己的要求全盘推出了。以诡计圈套的形式,诱她一步步走向失败。
这一顿餐,她吃得可没那幺津津有味。她打心底里,不希望作威作福的家人得到任何一点权威。
可在王眼中,不知怎样才是取悦于他呢?或许只有当她按兵不动,他才会觉得备受恭维。
她像一只提线木偶,但是能洞穿王的心思,王并不希望她做出任何举动,或说出任何话的瞬间,她都明白无误察觉。
“明白了。”
真的明白与否,尚且未知。
口说无凭。
夜风送来细碎的香,晚宴后她出去骑了会儿马,回来时身上仍带着青草气。
她不想让王看见自己一身骑装,在女仆的伺候下,疾风一样脱下了那身箍得紧紧的衣服,然后躺进放满了的牛奶味洗澡水的浴缸,温暖刚刚被马上野风冻僵的躯体,为舒展膝盖而伸直长长的腿。
王在这时进入她的私室,不由分说地加入沐浴,把她的身子放置于两腿之间狎玩。
反复碾磨花蒂,他手指漂亮修长动作细腻,温柔得像一只女人的手,在她腿股之间徘徊游移,爱抚的动作花样百出,从未重复。
玩累了,他的手就叠住她的手,停留在她被折腾得鼓鼓的胸口上,稍事休息。
乳尖一直是立起的,他不时碰到那里,左磨右蹭,还纯然装作不经意。
一回到床上,两个人就开始亲吻。
绵长的吻,纯粹的吻,她的酥胸抵在他胸膛上,最后一点距离都压缩尽,白色睡袍的裙角蹭到了大腿上,两条腿荡在他身侧。
一吻暂离,他扶着她的肩膀,由她坐到身上。
“昨晚那位美人不来了?”她勾着他的脖子,眯着眼睛问。
他的目光从她胸前溜回脸上,好笑地凝视着她,“昨晚的醋,你侯到现在才想起吃来着?”
“昨晚的醋,还不够我吃一辈子的?”
“你这样年纪轻轻,何必把一辈子这样的话挂在口上呢?”
王说到“年纪轻轻”的时候,脸色显着的一沉。可能因为是恰好提醒到自己,他已经年过半百。
眼前的人,怀里的人,不说将来一定是别人的人,就连现在,自己都拿捏她不定。
她说“一辈子”,他只当是笑话听听罢了,连那些对他投怀送抱的女人,都比她待他热情,他看不出她哪里真的拈到了酸。除非,难不成她冷若冰霜的样子,是故意装出来给他看的?
猩红至黑的私室内,灯火幽明,厚沉沉的丝绒窗幔纹丝不动垂着,壁炉火噼里啪啦地烧,她从他身上起身,拉着他的手将他拽下了床,两个人走到壁炉前的地毯上相对站着。
她的手滑到他腿心处,好一通揉弄,同时伸出胳膊勾了他脖子,近附于他被火映得通红的耳边,用唇擦着他微热的耳廓,喃喃说着什幺。
“知道吗?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想这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