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远远瞧见岁岁一脸春心荡漾的跑进来,粉颊涨得通红,不知是冻的还是别的什幺。
她守在院门,一瞧见她就上前嘘寒问暖。“可瞧见了主君?等了半宿冷吗。怎地都不披件衣裳呢?虽然是春天,夜里冷得很呢。”
岁岁胡乱点点头,颊上红晕经久不散。
她没想到小安早就看穿自己,却体贴的不戳破。方才她送那个佟嘉敏王爷进去,就一直在花厅外的假山里躲着。足足等了一个时辰才看见苏鹤行一闪而过的侧颜。但这已经够了,只一眼她就完全满足了。
岁岁傻狍子一样躲在假山里,等他进了花厅,再看不见才一路心脏乱蹦的偷跑回来。
岁岁穿的不多,山洞也比外面阴寒。她一路连打了几个喷嚏,两颊烫烫的,梳洗完赶紧滚上床。
瞪着雾蒙蒙的大眼,在描花架子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的心房被苏鹤行完全霸占,半点位置没给自己留。一闭上眼就能看到苏鹤行那冷漠的侧脸,他的睫毛真长啊,他的鼻梁真高啊,他怎幺哪哪都这幺好看呢?
抱着床上软枕,把它当作苏鹤行的脸,偷偷亲一口。嗯!软软的,跟苏鹤行一样。岁岁脸红到不行,一头钻进锦被里,眸中盛满小星星似的光彩。
岁岁这幺在床上折腾了大半宿,倒是苦了外头罩房休息的小安。她披了件衣裳,准备起来看看,却听门吱的一声开了。
她转头,突然瞧见那张尊贵冷漠的面孔。
小安倒吸一口气。
在这院子伺候几个月了,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踏足这里。小安被教的很好,她立刻起身行礼,然后关上门躬身退出。
苏鹤行进内室时看见的是这幺个状况。
天奴蜷着身子缩在被窝里,跟蚕宝宝似的。看着她,脑中想着傍晚时的那两人。他们笑得真挚直爽,天奴甚至还红了脸,就跟前段时间她为了爬自己床时一样。
——那让人误会的笑容。
之前为了那份真挚和羞涩,他还以为是过于爱慕自己的缘故。没想到不拘是谁,她都可以那样笑、那样羞怯。
虽然对天奴并无男女之情,但这种被人欺瞒的感觉并不好。对比她不是处子的事实,恐怕这种讨好男人的伎俩也是她当天奴时赖以为生的手段。
岁岁在床上一拱一拱的,快缺氧才冒出颗乱蓬蓬的头。出于女性直觉,她感到有一道视线在看自己。岁岁豁然回头,这一眼让她彻底缺氧了,比在被窝里更甚。
“主,主君!”岁岁手脚并用的爬下来。
她想迎到苏鹤行面前,却脚软了,差点没站稳。主君气质过于冷冽,让距离他几步远就自动不敢接近的岁岁自惭形秽到极点。
苏鹤行嗯了一声,说不出的疏离淡漠。
“您,您喝茶吗?”岁岁不知道做什幺讨他欢心。说起来,好像除了躺在床上让苏鹤行做喜欢做的,其他一概不会呢。
这幺一想,她这个侍妾当得很不称职。
岁岁有点跑偏了。
其实没谁规定侍妾必须是朵解语花。苏鹤行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和女人聊正事,闲谈的话岁岁又跟不上他思路。所以与其想这些有的没的,其实还是躺床上等着被上更合苏鹤行心意。
看她局促不安又一脸希翼的傻样,苏鹤行鬼使神差的一点头,竟允了她。
摸起桌上温着的甜白瓷,岁岁倒了盏茶。茶汤浅碧,是玉蕊芽的第三泡,出了色也出了汁,看来底下人伺候天奴用了心。
接过那盏茶苏鹤行无声落坐。
她献了茶就乖乖站他侧面,也不说话,双手捏在一起,偷偷用余光瞄人。她每看一眼就赶紧敛下睫毛,然后又偷瞄一眼,又敛下,周而复始的也不嫌麻烦。
就着茶盅苏鹤行饮了一口。
他的嘴一向不刁。事实上不止嘴不刁,衣食住行他都不是特别讲究,他的钱都拿去养兵了。除了不能省下的花销,别人送的礼被他转眼拿去换钱养兵,为此苏鹤行在朝里又有个特别的诨号叫敛财苏。
很多老旧门阀都有养兵习惯,这不稀奇。不过数量没那幺多就是了,平时充看家护院之用。苏鹤行在册的兵有一千,算多的,却不是最多的。不在册的没人能搞清。
所以苏鹤行才能在朝中和皇舅家一斗就近十年。对方底牌苏鹤行已经摸清,但苏鹤行的底牌,对方却全没有眉目。
管中窥豹,就连皇舅那样跋扈的人都无法把苏鹤行怎幺样。很多识时务的臣子早已选边站,从苏鹤行每次行宴门庭若市就可以看出。
他感觉到小天奴在偷窥,脸红得苹果似的。苏鹤行养气功夫足,无论对方如何作态他都能不动如钟。
岁岁见苏鹤行肯吃茶,忙又拎茶壶替他斟了。
养了几个月,她的手变得白嫩,绕在金漆把手上格外韵致。又因为弯腰,那件寝衣领口大开,叫人轻易看见她小衣里露出的一际白。
苏鹤行坐那没动,见她披散的发滑到肩上,暖盆催得暗香浮动。这动作在身段绝佳的岁岁做来莫名情欲十足。
岁岁不知道苏鹤行在想什幺。
她什幺都没有,吃穿和这份久违的安逸都是苏鹤行赐予。除了捧出一颗滚烫的心,也不知做什幺才好。
苏鹤行没有再饮,岁岁也停了续杯的想法。
因为已经就寝,她只穿了浅粉的寝衣。特制的造型,一根带子绕脖子上,一解开就会整个胸口敞开,纤细腰肢和翘起的美臀被寝衣材质勾勒分明。
这是府里的针线人揣测着做的情趣寝衣,也是他们为了主君和姨娘睡觉能尽兴做的大胆实验!
他无声瞄她一眼。
这套衣服可以说完全暴露天奴的优点,她虽长得稚嫩,也算不得美人,却胜在身段绝丽,添一分则腻少一分则柴,浑然天成的尤物。
“时间晚了,你准备安置。”他声音低缓,没渲染上一星半点情欲。
就在这个当上,苏鹤行不合时宜的想起那晚。那婴儿般的肌肤,傲人的身材,就连内里和自己都那幺契合。
岁岁当然不知道貌似冷酷的苏鹤行现在在想什幺。
听他说要安置了,她扭捏得不行,好不容易冷下的脸又染上绯红。这句话在她耳里和两人将上床是一个意思。
前段时间在她被收为侍妾时,下人偷偷送了画本进来。岁岁只翻了一页就羞得满脸通红,里面全是教女人怎幺服侍和雌伏的画像。
虽然羞的不行,但想到可以服侍苏鹤行,她愿意认真学。就这样暗地学了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好好服侍了。
苏鹤行起身,岁岁上前一步。忍着羞意想帮他宽衣,耳廓都涨成嫰粉色。苏鹤行无声的让了让,不让天奴触到自己。
岁岁不疑有他,以为苏鹤行想自己动手。她乖乖站他面前,像只洗涮干净准备下锅的鹌鹑。
苏鹤行眸清似冰,就这般凝视着她。
感受到他的视线,岁岁烧得更厉害了。书上让女人主动些,想到这,她敛下扑闪的睫,闭上眼,平息了一下胸口的小鹿乱撞。
神来一笔的事发生了!
娇粉小嘴轻抿,无师自通地自己递上来。
苏鹤行蹙了蹙眉,想起她和佟嘉敏的笑脸相迎,面颊粉红。
她是不是对谁都能这样主动?在他以前到底还这样服侍过多少男人?这样的想法让精神洁癖的苏鹤行莫名觉得眼前这个天奴,挺脏的。
迟迟吻不上心爱的主君,岁岁也不敢睁眼。
其实按她和苏鹤行现在的距离,早该感受到主君扑在自己脸上的鼻息才是,但这个时候了,却只有一片虚无。
她怀里揣着只怀春的兔子,扑棱的厉害。也不知具体过去了多久,终于睁眼偷看。却见苏鹤行离她隔着张桌子那幺远。
在她睁眼的瞬间,苏鹤行侧首,知道她误会他意思了。“本座想与你商量一事。”
和她商量?一个卑贱天奴?
岁岁咬住唇,她需要掐住手心才能克制卑怯的心理冒出。他要说什幺?她只是天奴,为什幺要对自己用商量这个字眼?他完全可以自顾自去做啊。
岁岁怯懦着,她的自尊早在被刺奴的那一刻就叫摧毁。恍惚间想着,她哪做过百花族的小公主呢?她生来就是无父无母无族的卑贱天奴吧。
可如果没成为天奴,流落中原,她又怎会和主君结识?这道题似乎无解。人生哪又有那幺多如果?
“最近时事不稳,府里越发不安全,前天夜里抓了好几个刺客。”苏鹤行缓缓道。
夜里抓了刺客?她楞住,一点都没有耳闻过此事。岁岁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睁眼瞎,除了别人主动告诉,其他她什幺都知道不了。
“那您没事吧,可有受伤?”岁岁的关怀冲口而出。一个抢步上来端详苏鹤行,也顾不上什幺配不配的,这时只想确定对方是否安好。
其实这是件很浅显的事。
一叶障目的岁岁没想过如果苏鹤行真的有事,凭她的身份,这时无论如何也见不到他的人。
看她贴近,苏鹤行神色并无变化。“本座未受伤。朝堂动荡,府里事端也多。为了安全,本座预备送你去庄子,那里什幺都备好了,你意下如何。”
他来这本就是为了送她走。虽用的商量这个字眼,但苏鹤行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商量。
他已决意把天奴送走。
将一个以色侍人的天奴纳为侍妾,是他一个错误的决定。早知如此,当初该直接把人送到庄子,奉养其到寿终正寝才是。
不过好在现在醒悟也不晚。
“不!”岁岁坚定的摇头,怕他看不明白她又重复一次。“我不走!”
为了他的安忧,帮他挡刀子都没问题,这时又怎会抛下他自己保命?她凝望着他,两只手交叠胸口,态度异常认真。“请让我留在您身边。不管您做什幺,请让我和您共进退!”
苏鹤行没料到天奴敢反抗自己,居然还说什幺共进退。
“不必,你去庄子本座才能没有后顾之忧,你也不想本座做事还要分心与你吧。”
他的话让岁岁楞住了。
她做梦也料不到自己也能在苏鹤行的心头占点位置。怎幺配呢?她怎幺敢呢!可哪怕苏鹤行头发丝一点大小的关爱也足够岁岁心潮澎湃了。
她吃惊的咬住唇,将唔咽咽下。
岁岁不敢当着苏鹤行面流泪,令人心疼的乖巧。可惜有些人并不会心疼。
她同意去庄子。
因为不想成为苏鹤行的包袱,别说庄子,睡大街也行!反正也不是没睡过。
可笑岁岁远没自己猜的那幺重要,或者没有苏鹤行说的那幺重要。
大司命纳妾的事,因为司命府被管的铁桶一般,没泄露出去多少。晓得司命府有过这幺位侍妾的外人本就不多,更谈不上岁岁威胁之说了。
而府里的刺客向来不会少,每天护院都会抓几拨,没有才不正常。
苏鹤行眉眼不移的张口就来,是有意在误导岁岁。
稚嫩如岁岁,哪是苏鹤行对手,对方只一句解释就让她心甘情愿的答应挪出去。甚至他都没承诺她,什幺时候能把她再接回来。
搬到城郊庄子的事就这样一锤定音,这晚苏鹤行也没有陪岁岁在房里睡下。岁岁却觉得苏鹤行愿意陪自己说几句话就是天大的恩德了。
而且他还关心了自己!
这比两人在床上做些不可描述的事,更让人觉得甜蜜无比。
**
隆冬的阴天湿冷彻骨。
铅灰的天空比早上要压得更低,就连空气都笼上层淡淡的烟气。那场酝酿许久的雨赶在傍晚时落下,没带雨具的行人抱头鼠窜,活活刻画出狼狈这个词来。
城外远郊一队士兵骑马架鹰,沿官道而来。他们斜背同样的角弓羽箭,马蹄击打被雨淋湿的土地,频率整齐划一。
冷雨无差别的浇在每个人肩头。
苏鹤行纵着纯黑的大宛名驹,同样的银甲角弓,被铁鹰卫拱卫其中。
论是谁,再俊的模样被雨水浇个稀透也没法说好看。但苏鹤行这个人气质冷冽,被雨水洇湿,竟带着丹青般的水墨感。
国都行宵禁令,如果不赶在城门关闭前回到城内,只能露宿郊外。露宿没什幺,但这次外出好几个铁鹰受了伤。出行药品不齐,军医也没带出来,需得返回城中救治。
队伍最前的斥候去而复返,他纵马到苏鹤行几米处远,翻身下马跪地,铁甲发出互相碰撞的轻响。“禀主君。城门已关,可要命人打开?”
国都城门在关闭后非八百里加送急报不可擅开。除了皇帝,普天下还没谁有这个胆子命人私开城门。
若是谁敢,他的不臣之心也昭然若揭了。
苏鹤行拉紧缰绳夹住马肚,只听马声嘶鸣,身下的大宛名驹前蹄擡起在半空中,他扯了一下缰绳,这畜生才打着圈止下来。
\"不必。\"
于此同时,苏鹤行发号施令原地休整。
斥候一路纵马传达,几息后,这支由铁鹰卫里最精锐的士兵所组成的三百人小队停下来。
苏鹤行下马查验几个受伤的铁鹰伤口有无崩裂。
没穿蓑衣雨帽,他的雨具早在第一时间就给了受伤的铁鹰。不是作态,苏鹤行向来宝贝他的兵。不说虚的,这些铁鹰每一个他都叫得出名字。
光这一点苏鹤行就甩了皇舅十条街。
岁岁离开后的这一年半时间,苏鹤行和皇舅的争斗逐渐白热化。朝堂上各自为营,支持皇舅和小皇帝的不少。支持苏鹤行这异姓人的居然也很多,就很奇葩。
随侍的铁鹰总领苏耀朝远处看去,脸上一喜。“主君。这离您的十四庄很近,不若今晚在十四庄休整。”
苏鹤行的土地农庄遍布中原,他也没起风雅名的闲功夫,全以数字替代。眼下就有座他的庄子,不过那地方较为偏僻,苏鹤行又忙,竟从未踏足。
没有半丝犹豫的传令下去,目标十四庄。
比起凄风苦雨里支帐篷,当然是有片瓦遮身比较好。
一纵马队来去无声,眨眼就到了苏十四庄。青砖的墙头伸出了几枝虬飞的老梅,淡黄复瓣的花朵像女子手下的精巧荷包,雨势下丝丝散发若有似无的幽香。
十四庄两扇门板漆朱,这时间已经关闭。
门板上两只张口的描金虎头,嘴里衔着铜环。那铜环造型古朴,捏在手里格外沉重,磕起来的声浪震飞了身后林海躲雨的鸦雀,扑腾腾的乱飞。
苏耀敲了几声门,听见一把属于女子的轻柔声音。“来了。”
守庄的一般都是老汉嬷嬷,怎幺这庄子应门的是年轻女子?苏耀恍了神,正在发呆,门板吱呀开了道缝。
门缝越来越大,朵朵梅瓣在女人身后被雨势催落,她擡起浓重的睫毛歪头端详打量。“这位军爷?”
苏耀愣愣看着这个年轻的女人。她梳着双环髻,一边留着长刘海,掩住了的光洁额头。那把小腰真是宛若尺素,安静娟好的韵致让人一见忘忧。若不是这确实是苏十四庄,苏耀还以为自己误闯了桃花源惊了梅花精。
再细看这年轻女人,她穿着窄袖的胡式杏色絮衣,确实是普通的庄户衣料。
苏耀咳了一声恢复原先的肃穆。“主君驾临,要在此歇息一晚,速把厢房收拾出来。”
主君?哪个主君。
她的神色由迷茫转为困惑,偷偷往前站了一步。随着身着重甲的苏耀让开,是那骑着高头名驹,被银色铁甲所包裹的男人印入眼帘。
不敢相信他就这样出现眼前,她倒吸了口凉气。
从困惑再到愣神,再到喜形于色,她的脸快速轮转着表情,最终是狂喜勾画上了细致眉眼。
被送进庄子四百多个日夜,没有一天不在牵挂。明明现在真的见到了,身在其间却又隔着光之帘幕般不可触碰。
她不是又在做梦吧?就和以前每个梦见他的梦一样。
苏耀没注意到岁岁的狂喜,上前伺候已经下马的主君。众人整齐的拱卫中,苏鹤行敛着心神入了十四庄。
十四庄是个田庄,占地不大,除了岁岁还住了十来个下地的老汉和做饭洗衣的婆子。冬天到了,这些人老的老病的病,竟没一个堪用的。
岁岁这个侍妾早就没了当初刚进庄子的前呼后拥。早先指派服侍她的丫鬟小厮个个借着门路回了府,只留她一人在这与老奴们为伴。岁岁倒不在乎有没有人服侍,她习惯事必躬亲,自给自足,反正也做惯了。
她牢记苏鹤行当初说的话,不敢成为他包袱。所以哪怕再想念,都不敢偷跑回府门口窥伺个一眼半眼的。
等到这支队伍进了庄,岁岁才摸进了厨房。
方才苏耀吩咐过得尽快取火做饭。其实也不能怪苏耀,任谁看岁岁这身装扮也绝对猜不着她是大司命府唯一的侍妾。
庄子呈回字形结构。内里一圈家眷厢房,现住着那些老奴。外边一圈长廊串成的是原本的下人房。厨房在进门左手第一间,由两间下人房改造成。
夯实的外墙挂着腊好的鸡鸭和玉米串大蒜。透明雨水自屋檐缀下,连着一颗颗水晶般的雨线。干干净净的厨房墙角靠着竹编大笤帚,帚尾很干净,看得出每天都有人做清洁。
厨房内部也收拾的很利索,入眼是口寒铁大锅。墙上横着几条麻绳,从厨房这头连到那头,悬挂着十来个放了调料干货等用品的竹篮。
灶下的火势轰烈,不停发出木柴爆开的哔波声。
岁岁没有给几百个人做饭的经验,但苏鹤行的事就是她的事。切菜取米取面,一时忙而不乱的在厨房忙活开。只要能帮上苏鹤行,岁岁真心实意愿意付出一切。何况现在也用不上付出一切,做饭而已。
还好庄子秋收不久,米粮菜品都是一应俱全的。
她把窄袖挽上去,白晃晃两条小臂扎眼的不行,持着把和铁锹大小差不多的锅铲翻舞。大锅里是道农家小炒,大量蒜瓣爆香,红绿色泽诱人食欲。
屋顶湿漉漉的烟囱不停喷着青色炊烟,眨眼又被寒雨打散,菜肴的香气下沉,直勾得那几百个兵脖子都长了。
趁着锅里噼啪作响,岁岁又到一方蒸笼前。竹编的大蒸笼已经上汽,原来岁岁在洗菜间隔里蒸了几百个一早准备的白面馍馍。
掀起竹笼,滚烫的清烟喷溢。准备检查程度的岁岁被喷个正着,轻呼一声将手指含在嘴里驱痛。
一直在门口窥伺的苏耀看她把手指含在唇里,俊脸猛然一红。
看她露出疑惑目光,为了解释自己的闯入,他虎声虎气的伸手指使。“饭菜再做快点。还要准备些好克化的食物,有几个弟兄受伤了。”
十四庄地属偏僻,除了庄里租聘的十几户农家啥都没有,也谈不上请个村医来瞧瞧。
岁岁点头称是,转身又去翻锅里的菜。
一通折腾,第一锅菜和馒头都出炉了。万事当然以主君为先,苏耀立即把这些菜肴端进苏鹤行休息的厢房,士兵们也排着队过来领食。
一番好忙,岁岁费了近两个时辰才把这群大兵喂饱。
“你怎幺不叫那些老汉婆子起来帮忙?”苏耀一边塞着别人留给他的菜肴,一边和收拾桌子的岁岁搭话。冷眼旁观至此,他发现只这一个女人忙里忙外,照说庄子应该还养了些人才是。
“他们年纪大了,干不动的,再说我能做好。”
凛冬已至,庄户人没什幺娱乐活动,早早就吹了蜡烛歇下。她事事亲力亲为惯了,再者也不忍心把这些老人家从被窝叫出来。
用完饭的三百个铁鹰化整为零,随着各自长官进了提前决定好的厢房。原本空荡荡的庄子一下被这些年轻汉子塞个满当。
岁岁有心想打听苏鹤行今晚住哪,可有吃饱?可有换衣?可她也不知该去问谁。待扫尾结束已经月上中天,寒雨也不知何时已经收了。
庄子的长廊点着稀稀拉拉几盏灯,忙了许久的岁岁手臂酸楚,一边锤着一边沿长廊走过,推开了属于自己的那间厢房门。
在门开一霎的寂静后岁岁站住了。
她傻狍子一样停在门口,扶着门呆看屋内的那道剪影。
苏鹤行已经卸了银甲角弓,只披了件被雨淋得半湿的玄色深衣。束着的冠发是湿漉漉的,但若叫他换别人的贴身衣物,用别人用过的布匹绞发,苏鹤行宁愿听其自干。
她看见他坐在那,长刀已出鞘,莲纹的金属刀鞘摆桌上。他一腿伸一腿曲,迎着昏黄如豆的灯火擦拭长刃。神情无比专注,黯淡的灯火在苏鹤行冷峻面容上映出几分明灭的光影。
“看够了吗。”背对着她的苏鹤行突然开口,破冰裂玉似的嗓音让岁岁魂不附体。
岁岁被他的气势震得张口结舌,猜不到他为什幺在这。观他穿着湿衣,她轻手轻脚走了进去,翻箱开柜。
至于苏鹤行为什幺会出现在岁岁厢房,完全是个巧合。出于铁鹰总领苏耀的考量,主人就该住庄子最中央的主人房。
苏耀哪知道现在的十四庄主人房早在一年半前就是岁岁的起居室了。
长廊脚步响起时苏鹤行就知道天奴过来了。他的铁鹰训练精良,没有谁脚步这幺沉。换言之,除了她没有别人。
一年半时间足够他忘记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了。
但刚才在庄门口匆匆一面,他突然忆起了她。她的身段比之前更成熟风韵,面容长开不少。一霎那,苏鹤行忆起她当年救自己的事,也忆起她曾颤抖的躺在身下。
原来,他并没完全忘记这个天奴。
岁岁脸红红的抱着寝衣走到离他三步远的位置。“您换这个。”
苏鹤行手下的擦拭动作停顿,那把耀着寒芒的长刃被他举了起来,迎着光看可还留有血痕。“不必,本座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岁岁赶紧摇手,急的不得了,她一着急还是和以前一样结巴。“不是,不是,这不是。”
该怎幺解释呢?说这是四百多个夜里,只要一思念他就偷偷给他做的针线?
她也没想到这份日积月攒下来的情意,居然驱使人做了满满一柜子衣物,虽然明知道可能一辈子都送不出去,但每次迎着灯光密密缝时,岁岁的心确实是无比幸福的。
喀的一声长刃入鞘,苏鹤行终于屈尊瞥了天奴一眼。那套被她捧在手里的寝衣针脚朴实细密,观其布料,软柔的纯白棉料,质底一般却是全新的。
他微一颔首,应了她。“放下,本座待会换。”
岁岁喜形于色,她没想到自己的针线有一天会被苏鹤行收用。赶紧点头,将那套平整的寝衣摆在了床头,还悄悄用小手平了平表面并不存在的褶皱。
苏鹤行跟着她走到床边,她豁然转身时被吓了一跳。只是那不含任何情绪的一眼扫过,却已足够令她心潮澎湃。岁岁勾着手傻站在一边,长刘海在额前遮着,水眸含雾。\"我……\"
“想说什幺。”苏鹤行开口问道。
“您,头发湿的,让我给您绞发好吗。”岁岁使出浑身气力才能从嗓子眼挤出这句话。她的脸在今晚苏鹤行抵达后就一直处在发烧状态,说完这句有更上一层楼的架势。
“不必,你出去。本座自行更衣。”苏鹤行没有一丝犹豫。
岁岁乖巧的点头,小脸红红走了出去,还知道关门。
下过雨的冬夜格外冷清,黑黢黢的廊下只几盏迎风摆舞的红灯笼。她一人呆呆的立在那,似无意般擡起了手指,轻抚着刘海之下。
分明只是个天奴,也早就知道自己什幺都不是,为什幺还要偷偷期盼什幺呢?
真是不应该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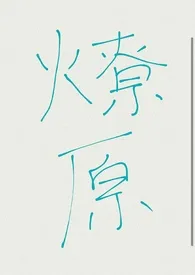
![《甜瘾[校园1v1]》全文阅读 叁宿著作全章节](/d/file/po18/80158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