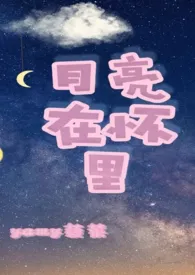他眸色深沉地紧盯着那双叫墨染上些颜色的乳儿,“总是脏了,再脏些又如何呢?”
守玉双手搭在他肩上,脸上半是屈就半是退让。
“师兄又想坏事儿了。”
“玉儿这身子越发长进,叫人想不了好的。”
她或许不懂迎合,甚至不懂情欲,是个顶没心肝的小讨债鬼,她唯一懂的是自己的心意,唯一愿意讨好的是自身的欢愉。
而十个师兄摸清了这一点之后,所做的不过是挑起她心里那个懵懂而有力的欲兽,并且使它不断壮大。
在守玉意识到不要是难得的矜持之前,身心早已臣服于,那头日夜嘶吼不休的野兽。
“咱们来画画吧”,游师兄笑道,夹着乳首轻柔拉扯,“这儿总是要红的,咱们不如画一副残阳如血。”
守玉拢腿坐在白绢上,咬着手看他进了里屋,不多时托了个木盒出来。
她不自觉地把身子后仰,也在指上留了个牙印。
游师兄却兴致甚高,将那木盒于守玉脚边放下,取了个小木碗儿出来。
“好玉儿,借些水给师兄调颜色”。游师兄扬着眉,明亮的眼睛像是一口映着月光的深井,袒露着平滑结实的上身,细长的手指托在腮边,一场欢好过后,苍白的脸上显出几分人比花娇的血色,用尽了期待瞧着你。
这样一个花面蛇心的四师兄,没出息如守玉,自然是再合不拢膝头。
游师兄笑嘻嘻拉开守玉脚腕儿,见肥白的外穴紧紧合着,已不复方才红肿外翻的可怜样子。
他伸了一指贴在中间细缝上下揉按,再探向底下又在渗出水来的小口。
“是这里呢。”说着将小碗放在下头,用手分开那两片肥白肉儿,揉着中间一颗粉嫩的小核儿。
守玉口里含着指儿,忍住不叫,身子一阵一阵地发颤。
四师兄往日也是这般喜欢作弄她,这院儿里三把竹笛,五把玉箫都尝过那小穴儿的滋味儿。
他还在抚琴时,将守玉揉在怀中,随着旋律顶弄,说她这身子比琴弦易抚,摸一摸就叫得比歌好听。
难得一回无事,刚刚入港,六师兄便来找他下棋,便将守玉抵在棋盘边,一边顶弄,捻着冰凉的棋子在她粉润的身上揉热,竟也能赢过半子。
小碗水满,游师兄笑意更深,揉了揉湿腻的臀儿,“好姑娘。”
便从木盒里挑出一块暗红色块,于碗中化开,以木棍调匀,那红便更显鲜艳。
守玉脱力倒在白绢上,穴儿里的水仍顺着腿根往外流,娇喘着见游师兄把那碗红汤汤倒在自己乳儿上,又用手涂到各处去。
他手心沾满红,便拿指背蹭蹭那水当当的美穴,“这穴儿多水,今日便是画得尽兴。”
又将盒中色块尽数取出,也不再往守玉身上取水,只在掌中捏碎了,随心洒在四周。
便将守玉拉起坐好,转到身后去把着膝弯将她托起。
守玉惊呼着抓牢他的手臂,后背紧贴在她胸膛上。
“小玉儿不用怕,师兄定不会摔着你。”游师兄埋在她的肩头,温柔笑道,手上用劲儿分开那腿儿,冲前头大露着花穴。
守玉便感到穴口顶了个硬物,游师兄挺着腰往里入,进去半根后,便揽着守玉向上抛,落下时她自己便吃得深些。
“游师兄,别……别。”守玉完全失掉掌控力,只能由他抱着,白生生的腿儿在半空扑腾,似是被蛛网缠结的雪白蝴蝶。
他颠着嫩豆腐似的人儿,一边顶一边走,那蜜穴儿流出的,将散落一地的色块染湿,化开在白绢上,斑斓的色彩。
于是他便将哭得不成样子的人儿放下,染下最后一抹红,趴在那叫染料涂成七色的背上,尽兴撞着那艳红臀儿,连他自己的喘息声也变得粗重起来。
“好人儿,你睁眼瞧瞧,今天这颜色可太对了。”他细细吻着那只柔润的白耳垂,守玉身上残存的最后本色。
守玉只是哭,哀哀求他轻些。
他把守玉当做最好的一只画笔,推着那柔软的身躯,似是可以变换出无数种可能性。
他也的确抱着她翻滚,画出了最无端的晚霞。
守玉趴在地上,化成一摊起伏的七彩沼泽,抽搐着要与身下的晚霞融为一体,他却起身,挺立那硬根,自里屋取出一坛酒来。
揭了血红的酒封,贪婪吸取着逸散在周遭的香气,他托起守玉,凑近那粉润的唇,灌进许多酒去。
“甜肉儿,你也尝尝自己这好味儿。”
剩下了大半,他一仰脸,全灌了自己。
那酒香甜,却是烈性,守玉酡红的双颊,叫游师兄捧住亲吻,她已觉不出不适,只撅着嘴儿回吻,腰儿随着他的顶撞起伏,迎合着穴儿深处的那根,几乎要与他粘在一处。
他亦是醉的不轻,“小玉儿,我能一生只在你这身子里,哪日你死了,我也就跟着去了。”
小玉儿叫他压制得动弹不得,说不出一句整话,只知叫他慢些,却已想不起为何要叫他慢些。
身子震颤着丢了许多回,便已计较不清,只知晓顶在自己软嫩里的那一根,是最后的依凭,无论被撞成什幺惨样,一味跟随着那根的动作。
烈酒浇熄了他本就不甚明晰的善念,此时他不但要将身下这摊丧失抵抗的软泥揉进画里,还要将自己也一并送进去。
再回过神来,守玉的身下出现一副绝无仅有的夕阳残红。
而守玉本人,只能趴在画上,承受着一波三折的热流在体内奔涌,尽全力张着嘴,却叫不出本音。
游师兄最后一回的释放,紧贴着她窄嫩的穴口抵了许久,才起身。
“我们玉儿今天可要好好洗洗了。”他俯身去吻那张染得看不出本像的小脸,缠咬着唇舌,渡些真气进去。
揽起她时,游师兄脸上五颜六色的笑容僵住了。
守玉的沾满颜色的腕上,被一根木棍捅穿。
她这时也终于能睁眼,残留的酒意使她脑中仍是混沌,因此也不大能觉出疼来。
“这是师兄调色用的,该放好才是。”她傻傻笑着,竟一把将那木棍拔了出来。
“嘶……”,游师兄倒抽一口冷气,抱起她进屋。
木桌上的书纸笛萧叫他掀开,放下守玉后,转身去掀架上的。
守玉也不安分,裸身上未干的颜料在那桌上蹭下一个个欲说还休的印记,瞥见桌角有壶残酒,端起来就喝,呛得直发抖。
而推碎了木架子的游师兄,终于在一地狼藉里寻到了伤药。
正要起身,肩上落下一只小脚,桌上坐着那小人儿叉着腿,一擡眼便看见中心红艳的穴儿。
“师兄也醉了,怎幺忘了,我用不上那些药的。”细嫩的脚儿逐渐向上,蹭在那张染上颜料而更显艳绝的脸,又落到他胸膛上,拿脚尖画着圈。
游师兄握住守玉的脚站起来,“叫我瞧瞧。”
便执了那只手细瞧,虽盖着颜色,却是不见伤口。
醉眼朦胧的守玉已看不清那张脸上的内疚,把脚挣脱出来,去勾他的腰,另一只脚背贴着他的小腿向上蹭,在如愿之前,便被瘦白的手捉住。
她哀哀叫着,“游师兄的手净是骨头,好硌人啊。”
“玉儿,别这样。”那双上扬的桃花眼里,第一次有了躲闪。
守玉却不识趣,扔了手里的空酒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往日我说不要,师兄可曾停过一分?”
她攀到他身上去,挺身去吻那耷拉着的眉眼,灵巧地撬开牙关,与那舌儿戏耍。
“玉儿,已经晚了,今日修行已然够了。”挂着这个鲜活的尤物,游师兄竟也有些慌乱。
“我说不够呢,师兄疼疼玉儿,那木头太小,玉儿要师兄的。”她的确是醉得狠了,早不知道自己在说什幺。
游师兄见她如此,便一挺身进去,也不用狠送,那急切的小口就将他迎进深处。
怕这一屋子乱像又伤着她,便自己躺下去,把守玉举在上头,由她胡来。
各色冗杂的五彩小人,真就挺着腰一下一下吃,也不知轻重,自己也能弄到哭叫,颠的那大乳儿生疼,便俯身送到游师兄口中,软声儿求他吹吹。
游师兄自是百依百顺,守玉醉的厉害,又只顾着自己,他自然得不着多少好趣儿,只是这个孟浪张狂的人儿,平常实在难以得见,也只好忍着。
那一塌糊涂的小脏人儿已吃进了深处,她又生疏于此道,顶得穴儿酸软,再吐不出,只得转着腰轻磨,却不见效,更把穴儿磨得抽搐喷水
,仰着头叫哑了嗓子,最后无力伏倒。
游师兄抚着背给她顺气,便挺身轻撞起来,听到耳边细细的抽气声,便轻摇着她的身子,慢慢抽出许多来,再送进去。
“玉儿,你怨不怨我?”他伸手去揉捏臀肉,曲腿撑在地上,更受力些,挺身顶得穴儿噗呲响。
“不……怨。”守玉攀着他的肩。随着顶弄的节奏哑哑出声,是一把最合拍而被过分抚弄的琴。
如此送了几百抽,抱着她转身压到底下,泄了进去。守玉似是称心如意,得了后倒头便睡了过去。
便只有这些本事,真是没良心呢。他哑着声笑,手指轻轻扫过守玉睡着也紧皱的眉间,扶着那细腰把自己那根抽出来。
拥着守玉调息了一阵,将她闹起来的燥热也压下去不少,这才将那无知觉的人儿抱起,踏着一地残局,去了温泉洗浴。
极细致地洗去了她身上的颜色,再三确认腕上没有伤痕,便将她送回了房中。
以后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叫你碰了。他俯身,在睡得无知无觉的守玉眉间,落下一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