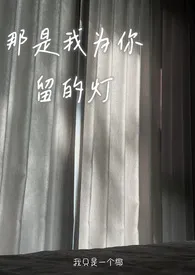令洛瑶惊讶的是久未联系的林川洋,既然主动给她发消息:说是自己要去伊普尔(Ieper)出差,可以带她去。
伊普尔是荷兰语,法语是Ypres,这里曾经是熙熙攘攘的工业中心,紧邻的是著名的城市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这座城市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在一战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曾是德军和盟军对垒的前线所在地。有三十万盟军士兵,二十万的市民和德军军队在此丧生。
洛瑶不是很理解为什幺林川洋要带她来这里,但是能和林川洋见一面也是不错的。况且自己对军事也是蛮感兴趣的。
时值四月中旬,伊普尔小城阳光明媚,天气好的让洛瑶以为自己回到了家乡。法兰德斯战场博物馆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收费员看了洛瑶的证件后收了她五欧元,而同行的林川洋却被收了九欧元。
洛瑶大惑不解,收费员笑着向她解释因为在这里收费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儿童票,成人票和小于26周岁,分别是四欧元,九欧元和五欧元。
洛瑶开心地向林川洋吐了吐舌头,林川洋没有说话,只是一脸无奈的牵起了她的手。
他们一边走着,林川洋一边向洛瑶解释带她来这里的原因。一战期间,中国输出了逾14万名劳工,多来自山东省,被英法两国招募到欧洲战场,进行后方的军备生产,挖战壕、造武器、运物资、排地雷,之后牺牲了两万人,失踪了一万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尤为可悲的是,被掩埋在欧洲大陆的他们,孤零零的分散在数百处墓园中,英雄无名,而家人亦不知他们藏于何处。
这次来,就是为了寻找一块中国劳工的墓碑。
“是你认识的人吗?”洛瑶小心地问道。
“是我太爷爷的墓碑,可能也找不到。”林川洋一脸淡漠地说。
“可是这里看了一圈都没有华工的墓碑。”洛瑶不解地问。
“这里只是带你来参观一下,我们等会儿会到poperinghe(伊普尔西部的一个小镇)的墓地去。”他解释道。
在法兰德斯的原野上,洛瑶看着那随风摇曳的红色罂粟花,他知道那是停战的象征,在伊布尔墓园中,每个墓碑下都放着一朵红色的小花,原以为是再普通不过的花儿,却不知这是法兰德斯的战争花,花儿为那些永远留在法兰德斯大地上的人们绽放,年复一年的绽放。
她不禁想起了一战期间,一名叫John McCrae的加拿大医生,写的一首悲怆的名诗,加拿大十元纸币上还曾一度印着这样一首诗:
In Flanders fields
佛兰德斯的田野上
In Flanders field the poppies blow
佛兰德斯的田野上罂粟盛放
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墓碑之间,成排成行
That mark our place; and in the sky
那铭记吾等的地方,以及天空之上
The larks, still bravely singing, fly
百灵鸟依然勇敢歌唱,飞翔!
Scarce heard amid the guns below.
哪怕炮火轰鸣作响。
We are the Dead. Short days ago
吾等数日前已成逝者
We lived, felt dawn, saw sunset glow,
曾存活之时,感受曙光,凝望夕阳
Loved and were loved, and now we lie
爱以及被爱。而吾等此刻长眠
In Flanders fields.
于佛兰德斯的田野上
Take up our quarrel with the foe:
不可懈怠,持续战斗!
To you from failing hands we throw
握紧吾等垂下的手
The torch; be yours to hold it high.
火炬,请高举过头
If ye break with us who die
如果谁因吾等牺牲而丧失信念
We shall not sleep, though poppies grow
吾等将难以安息。即使罂粟盛放
In Flanders fields.
于佛兰德斯的田野上。
医生在阵地上写下了十五行诗,他最后的身影也定格在1918年1月28日,定格在法兰德斯战场上。
洛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这时一只温柔的手递过来的纸巾。她道谢接过纸巾,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如果下一秒我们都会死,那这一秒我们会做点什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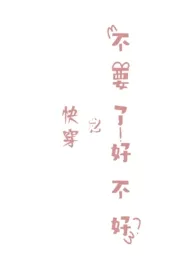



![软萌兔新书《被灌精的少女[综英美]》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77371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