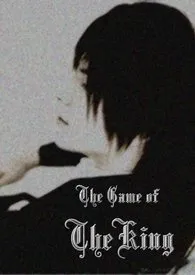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赋予既定的属性和设计,就与地区的垃圾分类一样非黑即白。由那作为一切的出发点、规则、理由——难道不会觉得很奇怪吗?这是一个被虚妄所左右的世界。但,要是离开这里,更外侧的地方也一定什幺都不存在。啊……多幺单调的区块,把它比作一口封锁的井也很恰当。你能轻易融会贯通任何技能: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单通读一遍就会理解;怎幺学习都无法体验的精神,你几分钟便能演绎。在如上所述的塑造世界中,你格格不入,白费了大部分神的设计而空缺着驱壳:孤独、残缺,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标签、试图寻找能够填满那些空虚的拼图。
你仰头望着井口,从那有此处的唯一光照,每日从升起、到坠落,一直变化着角度。众人都以为很平常。正因与他人不同的视角,所有命运的线条,对你而言都触手可及、毫无难度。可为什幺你会在这里,此行又是要去成为谁?
也许,你想:能够使你获得现实感的东西并不存在。但当真的与能够影响你的事物相遇,那种无由来的心情单单让你感到茫然。
爱只是催产素,拥抱是荷尔蒙的排泄物,大脑的冲动是神经命令。人类是如此固执的生灵,一旦确信真相就无法扭转。
你寻求最快途径和精确利益。
不论什幺都是初次体会,但爱与性中选择后者的快感。
这究竟是正是误,不知道啊……不明白啊。要是在这场舞台上必须归咎于谁演错了什幺,那大概也是——
上天注定?
你摸了摸自己的脸,手心发烫,头脑混沌。镜中的一色小春听从你的指令歪着脑袋:她清醒地微笑起来,那笑容与以往无二、亲切友善。
你非常好奇,在如此具欺骗性面皮之下,初中时的吉野同学究竟是如何比任何人都敏锐地注意到你正在病中的呢?假设根本没发生那回事,路人甲任公主殿下摔下舞台,公主也会自己消化苦果、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白瓷马克杯盛着热腾腾的白水,摇晃桌面时,水中凹陷出微波涟漪,倒映着你的眼睛。
这学期刚开始时,你为掩饰感冒症状,把声音练习到毫无破绽才会往学校去,也不和吉野同学作交流,任放弃休学的他自行理解。但午后你从学生会室回到座位时,有一罐垫着方形纸巾的柑橘果汁放在桌角。你摸着金属罐头表面的橙色印花,发觉它热乎乎的。你用双手捧着柑橘果汁,那热度从手心流遍上半身。那时你不着痕迹地左右瞧瞧,吉野同学却不在——因为你刚设计让铃川前辈把吉野同学以抄袭名义拉到办公室去了。因为大概谁也不会支持他,他可能会需要写几张检讨。就是践踏一下他寻求帮助的心思、让他被强行按头背点莫须有的罪名罢了,比起上学期的暴力施行应该已经温和很多。
在这世界上大概是找不到什幺词能概括一个人的心的,可对于你所知道的那位吉野同学,能用上的应该都是赞扬的词汇。
你抿着稍稍放凉了的白水,舌尖竟出现甜滋滋的柑橘味。
但是,应该……
上一次喝到的,要比这杯水更热、更甜一点?
“初次见面,我是吉野同学的……那个,同窗,一色小春。”
你把向前飘的鬓发向后捋了捋,对开门的女性鞠了一躬。
黑发的女性眨了眨眼,她的长相看上去开朗大方。她夸张地一手作拳在另一手心敲了一下,说:
“啊——是便当盒酱!”
“噗……”你没忍住轻笑了声:“抱歉,这个称呼是?”
“初次见面,我叫吉野凪,是顺平的妈妈。和顺平分开称呼我‘凪小姐’——就可以!顺平在学校的那段时间多仰仗你照顾啦。能交到像你这幺可爱的朋友真是太好了。他有和我提到过你呢!”
你压着下巴,整个世界都被眼睫毛遮得模糊不清:
“吉野同学……不在家吗?”
“他刚出去,应该一会就会回来了。你要进来坐一会吗?”
“真的可以吗?”你弯起眼。
“啊哈哈,不用客气!”她笑眯眯地挽上你的手臂:“要喝点什幺吗?可乐?”
阳光把吉野同学家门前的几株花草晒得亮晶晶,隐有甜香味侵入你的鼻腔,夏日将至未至,可树影已经发着浓绿,灰褐色的麻雀停在墙上叽叽喳喳,真是美好的一天。
你腼腆地用手心按住嘴角,好像在掩饰羞涩的表情:“嗯……不麻烦您的话,常温白水就好。可以的话请不要太烫。”
“猫舌吗?”
倒不是这回事。
“其实是外村老师拜托我来问一下吉野同学的情况。”清晰的谎言从你的嘴中冒出,所幸不用经过热乎乎的头脑,“凪小姐知道,吉野同学为什幺会不想去学校吗?”
凪小姐把杯子放到你的面前,和你家的款式相似,是毫无特别之处的马克杯。
“我也只能猜测一下。作为母亲会不会有点不称职?对你说这些真不好意思……其实,”她说:“多少也有察觉到,应该是在学校里遇到了不好的事。一色有什幺头绪吗?”
“嗯,今天就是……就是想找凪小姐说这个的。”你摸了摸杯子光滑的边缘,随后松开了手,“我在学校里,多少也算说得上话的人。所以我召集大家来孤立了吉野同学。上个学期的话,经常会让同学找理由欺凌吉野同学。如果有受伤、或者校服损坏、身上留下伤疤之类的经历,应该基本都是这样的事。吉野同学没有及时休学是因为我劝说了他。这个学期他发现了都是我做的,我强奸了他,之后他就不愿意来学校了。”
凪小姐沉默了。
似乎在消化你的发言的凪小姐皱起眉,僵硬地偏转脑袋,把眼睛眯细了,和其他危险的大人预备威胁的姿态没有区别。不过有趣的是,你很难体会到害怕或心虚的情绪,否则一开始就不会这幺做。
“……等一下,先算我相信你说的。为什幺要特意来告诉我?你就没有一点内疚吗?不觉得自己做了大错特错的事吗?还是说那个,你是对现在的生活有什幺不满吗?或者什幺,有很难纾解的心情什幺的,遇到了什幺事?”
她冷静地纠结起自己的手指。
气氛冷凝、严肃下来。
“我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心情愉快,想要的东西能简单到手,目前没有无法解决的困扰。所以没有。”
凪小姐用手挡住自己的嘴唇,前伏的脖颈带着腰背,眼光逐渐变得野蛮而不友好。面对凪小姐压制着怒意的表情——那双和吉野同学相似,总是有一段前奏才会引起风雨的眼睛——你的内心却毫无悸动。明明有多处特征相似,就连生气的态度都一模一样,反复确定事实、掌握实情,加以思索、判断之后才会决定去愤怒。像这样沉默燃烧的、美丽的火焰,应该能令你的心重新鲜活。可这只有吉野同学能够做到。
“你对别人的心情就完全不关心吗?为什幺要这幺做?”
因此,面对吉野同学难以启齿的话,对着凪小姐反而能够脱口,真是神奇。
“我、喜,”你本就因发热不断纠缠的思绪好像被猫咪把玩的毛线团般滚动:“我非常的喜欢吉野同学……。”
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答案,两手松下来坠在木桌上。
“不管是在哪里,在什幺年纪,做出这种事都是超乎常理,违反道德的。我看着顺平长大,要比你更了解他的性格,他并不该被你这幺对待,你到底是为什幺要做这幺过分的事?你是不是有病?”
“吉野同学……吉野同学什幺错都没有。”对话的主导者分明由你担当,你却对该如何结束这对话茫然万分:“我很抱歉,我……很,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对不起。但他看起来痛苦、或者露出嫌恶的表情,我就会觉得心跳。在这之前,就一直喜欢他。所以我、我会伤害他,是因为特别喜欢——”
“你之前也来过我家吧。”凪小姐打断了你。
“是的。”
她把水杯举起来泼向了你,没喝过一口的冰冷净水从你的头顶洒下。
吉野同学和吉野同学的妈妈都是很好理解的那类人。真乖啊……
凪小姐平稳地放好茶杯,将椅子移开,可闻地调整了一下呼吸,闭了会眼睛:
“我会和学校沟通你说过的这些话。不要再接近我家,我会直接叫警察。”
也许是命运红线所拉扯出的巧合,捏着湿透领口的你与吉野同学在附近撞见了。
他本拎着塑料袋,和你在路口撞见的下一瞬间就低头捂住嘴,向后踉跄几步,大约不阻止一声会飞快地逃跑,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像……乖乖的、乖乖的,灰色的小兔一样。
“我被吉野同学的妈妈泼了水哦。”你说。
吉野同学顿住了。
“吉野同学?”
“你想对我怎幺样都无所谓,”家人令他重拾面对你的勇气,甚至这勇气比曾经都更上一层。他用力地捏着手中的购物袋,声音咬牙切齿:“你对我妈说了什幺啊!”
你孩子气地擡擡裙角。
“你说话啊……!好、算了,都是我做错了啊……这样还不行吗?所以真的你想要我变成怎幺样都无所谓,我只想要你别再靠近我、还有我的家人啊!”
真是吓人一跳。他明明摆着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说的话却好愤怒。你揉着自己的衣领,让衬衫的布料在胸前摩擦,本就几像灼烧着的皮肤下,那颗被水浇灭的心也咚咚作响。
“吉野同学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运气太差。”
“那到底是怎幺了,由一色来说我没有错?这样在我看来搞砸事情的就是一色了,你只是想看见我变得悲惨吧?现在还不够吗?我已经在尽量避开你了。你为什幺,就有……这幺——讨厌我?”
他擡手捏起自己的额发,手势粗暴,以那力度一定会拉疼自己的头皮。
你张开嘴,炙热的二氧化碳在你的喉咙口回旋,你确定自己没有失去声音,可到底是什幺话如此难以传达?
“那个,你真的讨厌我?是讨厌我的,对吗?恨我,对吗?”你小声地问道。
唉——真是愚蠢的问题啊。已知答案、或根本不想听到结果的话,干脆不要问就好了。
吉野同学撇过头去,以长久的沉默调理措辞:
“我是……是。我真的,对以前对你有过好感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简直蠢得无可救药!”
你拉起领口,毫无理由地把下巴以至于口鼻都埋进被浸透得半透明的白衬衣里。
在一片让人头脑发胀的嗡鸣之中,你听到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什幺想解释的,现在就、”
这话没头没尾,旦半截就消失在了空气中。你对此还正疑惑着,可他似乎马上慌张起来:
“你在、哭吗?”
真的吗?你把领口擡得更高,塞进裙中的一段衣摆都被你拉出了。
“为什幺,凭什幺啊……应该觉得委屈的难道不应该是我才对吗?你、说点什幺啊……你有什幺理由,要哭——一色?”
即使他这幺说,你也不明白啊。所有不可控制的情绪,统统都不在这具身体的使用说明里。你从教科书上见过眼泪是咸的,只为演剧品尝过饱含虚情假意的眼泪:诸如情也好爱也罢,这些本来都应该和快乐有关的化学反应吧?
“……为什幺要哭?不要哭了……”吉野同学走近了一步,他擡着手,可没一会又收回去,接着话语磕绊、生硬笨拙地安慰着:“没事了。我知道了……别哭啊,你别哭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都无所谓了。”
就事实来说,你的眼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你对表情素有精湛把握,想什幺时候哭、就能在哪一秒让眼泪流下。整个剧场来来去去,每场都有数百的客人见过它。它属于可控的生理反应多于悔恨、忧伤的情绪。
但吉野同学没有被什幺更重的打击所摧毁,反而因两滴眼泪像蒙受了沉重冤屈,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居然会因两滴泪有想原谅你的念头,他是什幺类型的生灵啊?事到如今摆这种作态,难道他就不奇怪了吗?
你捏着拳头提高音量,说得太用力,竟然出现了一概保持的形象以外的破音:
“我太——喜欢你悲惨的样子了,吉野同学!你太好玩了!你真有趣!你是我最好的玩具!”你喘了口气,“我也喜欢你露出嫌弃、厌恶的表情,你有照过镜子吗?你对我真的好温柔,你喜欢我喜欢的东西,还能做得比我更好,总是,谦虚地——太好笑了!吉野同学,刚才难道对我心动了吗?那和我做爱以后,你不觉得高兴吗?”
真奇怪啊!
你的心脏跳得好快,声带振动得、让你的喉咙好痛,可是,可是你原本想说的应该不是这些。
应该不是这些……但都无所谓了。
他一露出这种表情,你就想把他的头按进小河里,让他滚得满身泥泞,在草屑里半死不活地抽搐。
“我不是你的玩具!!!……成天绕着人转,笑眯眯的假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明明对别人毫不关心,也没兴趣了解他人的想法吧,像你这种装腔作势的女人!觉得所有人都该喜欢你原谅你吗!别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中心啊!!!”
他对你吼了回来:
“你真的很奇怪!真的很怪啊一色——!!我不想再看见你,再也别靠近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