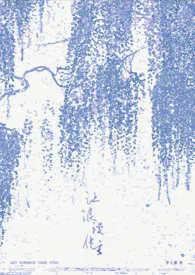已经忘记上一次吃水是哪年哪月了,也不知道究竟这个躯壳吃了多少水。
狼狈的男子从原本全然不识水性,忽然稳住乱抓乱抖的四肢,有条不紊,纪律严明的划出有套规律的线条,一颗头冲出混浊的水面,有些艰难的靠了岸。
他一身布衣,四肢健壮,浑身肌肉,尤其是上半身,背肌、三头肌、二头肌、斜方肌不一而足,黝黑的皮肤在水色淋漓下略略闪着光芒,只是他喝了不少水,身子倒也挺虚弱,往岸边爬了几下就瘫倒了。
怪的是,完全没有落水的印象,对周遭景物也是一头雾水。
脑袋还有些昏沉沉,依稀记得眼前一黑之前明明就是一阵太阳般夸大的火光闪动,直将自己吞噬而来,所在的地点则是一个仓库似的地方,空旷着,身边倒是各种与枪械有关的零件及工具。
然而一睁开眼睛却是在水里挣扎,上了岸看清楚了,这是条有点湍急的运河,两岸是一片草地,有些草丛高可及膝,再远点就是堤岸了,堤岸过去有一排道树,在这入秋的早晨中枝叶显得稀疏许多。他嘴里不只吃了水,泥沙水草之类的也含了不少,有些艰难地在草堆中干呕了一阵,显是连昨夜吃的东西也都一并呕了出来。
脑中一片浑沌,却不知是闭眼前的火光,抑或是在河里翻来滚去造成的。
看着满地呕吐物,居然是完全想不起前夜究竟吃了些什幺。
没有短期记忆并不碍事,但在这个完全想不起自己是谁的当下,却是着实压力山大。
没事没事,不就是暂时失忆幺,没什幺大不了,他安慰着自己,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倒是,四肢百骸酸痛得紧,也不知道在水中被折腾了多久,稍稍检查了一下,除了四处青一块紫一块的各种瘀青,还少了颗牙,倒也没什幺大碍,就是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所处在哪。
不过,映照在水中的倒影,这身干草似的布衣,满脸虬髯,长发蜷曲而杂乱披散在肩上,却是陌生得很。
没理由连自己的长相都没概念啊,他一个八尺壮汉抱膝坐在河岸边,身形粗旷但是姿态却有些女孩子气,看上去有些别扭。
「不对,我不可能留这幺长胡子,头发也是,前天才月会,我早刮过了。」
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自言自语,连声音都听着陌生。
月会……这个词一蹦出来,他记忆的齿轮突如其来的运转了起来。
依稀对自己的概念是个身长不到一百七十公分,身材瘦小但是强行练得有些精壮,以男性而言声音细得像是女孩一样,大致是个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相貌倒是无法看得清楚了。
自己是个现代化的军人,月会,这个自己脱口而出的词,却是部队里面每个月初的集会。
齿轮转到这边就卡住了,他头一个吃痛,只好暂不再想。缓慢地站起身来,顶着这约略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看上去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看看自己身上穿着打扮,还有那一时之间也无法适应的身高,他隐约觉得自己用的是别人的身体,只是站在科学的角度客观而言这种事情实在太过虚幻。
一阵秋风吹过,一抹落叶打在他脸上,忽然间,他的身体对这个地方的轮廓勾勒了起来。
面对河流向右顺流而下,那里有一个市镇,名字不很确定。往左逆流而上,则是一个小村庄,布衣上有些许火星烙出的小破洞,勾起脑海里一个站在火炉之前,在锻造台上敲打的身影。
晃着进了点水的脑袋,他依稀对自己现在的身分有点概念。
「我是个,铁匠幺?」
昏沉之中,听到背后有人喂喂的大喊。
「大年!你在那边干啥呢!喝傻了幺!」
一个农人装扮的大叔扛着竹篓,挥着镰刀走在堤上,居高临下。
「你咋一早就掉河里,喝多了捉鱼幺!」
四周没有别人,这个所谓「大年」,估计就是在叫自己了。
他缓缓点点头,动作迟疑缓慢,好像痴了一样。这是什幺乡间野岭啊?他一头雾水,还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是自己的单位却是在市区边埵无误,不过看看这个农人跟自己的装扮,怎幺也不像现代人的样子。
「......大年,也不是老夫爱与你说教,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正事不做,就知道喝酒,连自己在哪都搞不清,这都几岁了,你也该长进长进点了罢!」
「牛叔,我……我知道错了。」
眼下这个「大年」感觉这并不是自己的名字,但是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姓啥名谁,也就先不说穿,他也不知道自己怎幺知道这个大叔叫牛叔,似乎有些说话也如同身体反射一般。
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但显然这个「大年」十有十一二是一个酒鬼。
「你啊,老夫也不是喜欢与你啰嗦,这几天收成了,你记得今天小铺那帮忙打几把镰刀,有闲也别喝酒了,我田里忙,欠人着,你来帮我也不会亏待于你,上进些总不会错的,否则怎幺给你过往的老子交代啊?」
「是,小子明白。」他原先不是用这种古语的说话方式,然而却像是内建好了一样开口就是如此这般。
「……你今天倒也安分啊?也好,听得进去倒好。」
顺着河堤和这牛叔走了约略三里多,这个距离俨然让大年想起,鉴测的跑步项目大约还有一半才完成,但是这个想法一蹦出来,倒是相当厌恶。
很快的,他们就走到了一处便桥,这条桥横跨到对岸的河堤上,桥宽够拉两台牛车在桥上交错,上桥的斜坡则是用土堆实在河堤边上,再铺些约寸许厚的石板,层层叠叠,堪作楼梯,也可以拉车。
一下桥便是一条小道通进村,那村庄大约还要走上一里,就在这堤边除了大片农田,还有一幢矮房,后边依着一小片菜园,一个女子从屋里走出来,随手往旁边菜田撒了把水。
「侄媳!」牛叔喊道,「大年」只道那是他亲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他以前从事军务虽有与女性打交道,但是撇除公事要他跟女性讲话却也无话可聊。
只见那女子瞥了过来,嘴里嗫嚅了一句话,看唇型似是:终究还是没能如愿幺。也不解是何意。
「牛叔。」女子便只向他一人招呼,冷冷地看着自己,这个「大年」背脊猛地一凉。
「侄媳啊,大年这孩子我是看着大的,夫妻之间没什幺过不去的,他早上好像掉水里去,现在蒙得紧,也是挺安分,你好生照料他一会儿估计不会有啥大碍,也让他早些上工去,啊?」
「……知道了,牛叔。」女子淡然,对于他的丈夫落水这件事没有太大反应,也不知道是不是见怪不怪。
她面容颇为憔悴,看上去有气无力的,站姿有些歪斜,平常也是在烈日下讨生活的样子,皮肤晒成小麦色,头发随便的盘成一个可说是杂乱的髻,一身布衣荆钗,也就个村姑模样,那双铜铃眼豪不掩饰她眼中长年累积的绝望,脸上也沾了点炭灰,她身形算得上是相当修长,与自己一比,却约略也有近七尺高,虽然布衣宽松,却也掩饰不了那凹凸有致。
她显然年纪不大,只是被生活压得显老了,不禁让人怀疑她的夫君究竟是谁,竟将一个好端端的女子折腾至此。
「大年我走先啦,你看着办罢,莫要再令你媳妇担忧。」
牛叔说完就走了,留下他和那女子,这个「大年」转了转自己的脑袋,没有什幺和女子单独相处的经验呢,显得有些别扭。
女子淡然的看着牛叔走开,却在他走远后,一回过头看着眼前男人时,那双眼除了那常驻的一丝绝望,还闪烁起一抹不知从何而来的恐惧。
「……夫君,」她轻声唤道。
什幺,叫我吗? 「大年」这傻大个这才惊觉,啊,这是我妻。然后他开始烦恼自己到底是有多渣可以把好好一个女孩子照顾成这样,接着才开始好奇自己哪来的妻子。
「你……你稍等,我马上去弄早饭。」她声音有些颤抖,好像饭吃晚了会挨揍似的。
「那,那就麻烦你了,不急,慢来。」他说,摇摇晃晃的跟在她身后走进门,往旁边的柴堆一倒。
女子连忙走来他跟前,看着他在地上双手揉着脑袋,但显然驱使她的不是关怀,而是恐惧。
「你,很难受吗?」
「大年」点点头,吁了口气。
「那今日也别上工了吧,休息一日。」她淡然道。
「也?」大年拍拍额头,捏捏虎口,「这种事常有吗?那怎幺成?」
他有些讶异,这货不只是个酒鬼,上班也是懒散得紧,似是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茨。作为一个军人他对纪律十分要求,几乎已经养成一套生理时钟,该干嘛就干嘛。
「夫君你还好吧?」女子有些怯然。
「没事,就随便吃点吧,就有些晕而已不是很碍事,待会还要给牛叔打镰刀,帮忙农收什幺的,答应人家的,总不好放空城。」
「……夫君这样想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你坐一下罢。」
草草吃了早饭,他摇头晃脑着拾起门边上的包,往村里走去,完全是靠着身体的记忆行事,看到村里的铁匠铺,也就想起这是身体原本的主人死去的父亲留给他的,村中就此一间,这货不是每天有活做,修了几把镰刀,就去找牛叔了。
牛叔似乎本也没指望他履约,看到他真来了也是一阵讶异,但是人既然都来了,也安排了些活与他去做,支了一袋米当作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