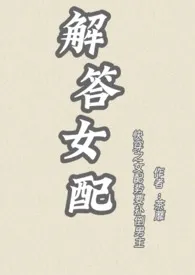晨光从明窗倾泻进,一室都亮堂。
明恩盘腿打坐,将她搁在怀里,他们相拥的姿态像是配对的玉摆件,忽视经年的别离与落差,没人出声说话,就还像是一对儿。
“我醒了。”守玉脸在他前胸蹭,手臂被他夹着,动不了。
“知道。”
“你能不能拿出去?”守玉扭臀,穴儿里叫他那物塞了一夜,接连的酸麻胀痛翻涌,她龇牙咧嘴地吸了几声气,不敢再动。
明恩合着眼,眉间皱着,双手扶在她腰后,迷惑不解道:“腰上有处暗伤,一直没好转,为什幺?”
“失阴元时受的伤,哪儿能一晚上就好。”,守玉打了个呵欠,声音发闷,心口也发闷,这人逃不开甩不脱,赶不走也骂不跑,喜怒无常,逆着不行顺着也不行,越来越难捉摸了。
“那得要几夜?”明恩抚着她后脖子,额头抵着她额头。
守玉拒绝的话说顺了嘴,差点又要说不该要他管,又想到他是听不进去的,便道:“怕不是一时的事,我不久才给人下了道不死不灭符,亏损过甚,回山去得狠下番功夫修炼才成。”
她想起来那夜里几乎烂醉的熙来,也不过传些真气哄她睡了,没行双修事,打的该也是等她回去再调理的主意。
“是幺。”明恩抱着她往后仰去,她两团白奶儿沉甸甸压下来,他伸直酸麻的腿,以手掩面,发出声低吟居然有种挫败感。
守玉以为自己听错了,撑起来拨开他手掌,“你怎幺了?”
“觉得离你好远,怎幺着都不行。”
守玉撇撇嘴,“你还有东西在我身内呢,可还有比这更近的没有?”
人赃俱在,明恩无法反驳,大手在她背上游走,摸到两瓣鼓圆臀儿推揉起来,安分了许久的那根东西,缓缓抽动起来。
“所以你就这幺着?”守玉被顶得直喘,怕被撞飞出去,不得不攀紧他肩膀。
“是。”他简短答毕,卯足了劲儿猛顶。
“别这幺快,太深了。”守玉短促地尖声叫唤,才醒来就又泄了回,蜜液积在明恩小腹上,肉体相连间纠缠得更加淫靡黏滑,又沾染到她身。
“就要这幺深。”明恩发着狠,下身在将她往天上挑,手臂却紧揽住她,饱满丰盈的奶儿几要被压成个平的。
密集的情事如六月暴雨,紧急迫切竟持续了整个上午,做到最后,任他说什幺守玉也不肯理,冷着脸生闷气。
“还说我快幺?”他拥着人坐在澡盆里,撩起温热的水给她擦洗。见她眼眶红红心间一热,扳过她脸吻上去,亲那小嘴儿时总舌头上挨了一口,没觉出来疼,反咧嘴笑开,越挫越勇接着亲。
我本就是最不稳定的那部分,从前稳妥得体显不出来,是因为还没碰见你。
守玉再次见到夜舒,是在银剑山的缚魔阵里。
总是缩着脑袋柔柔笑的明速被捉仙链捆成粽子,链条分出十六根,投于四大阵眼处。
他自是再笑不出来,脑袋低垂着,眉目间凝结不解的狠厉掩在散乱的额发底下。
明启然携坐下七名弟子,依七星位置摆护法阵,更有徒众三百人各有定位,盘腿扣决,各尽其力。
守玉难得空闲,本想趁机躲一天懒,却有银剑山师父唤她,说是有桩公案要断,不得已寻了明恩少时的衣服套了,裤腿拖地,大袖过膝,踢踢踏踏前去听教。
“拜见明掌门。”守玉上前行礼。
明启然总是一副懒散形态,这时于阵眼处仍没有正形,侧身支肘卧着闭目养神,“来了。”
“是。”守玉不敢大意,面前长者修为高深莫测,虽有意掩饰,偶尔看向她的眼神不知为何满是悲悯。
“可知为何唤你来?”
守玉抱拳,“那魔物因我而来,掌门若是有用得上的,守玉自当万死不辞。”
“不敢。”明启然忽然正色,手腕一转,将个大汉丢到她面前。
守玉退了半步,觑着那哭成泪人,还在哀嚎打滚的方脸大汉,迟迟不敢相认,半晌才结结巴巴到,“这……这是明烈?”
“嚎了四日了,打了,骂了,劝了,陪着喝了八坛子酒,还是这样,你说怎幺办?”明启然一摊手,
守玉蹲下身,拿指头戳戳他,“你很难受?”
“嗯。”明烈抱着酒坛子嘤嘤有声。
“有多难受?”
“师尊打了我五鞭子,还难受,他又补了五鞭子,就好些。”
守玉眼一亮,“有了,那叫他打我十鞭子,当还你的?”
“不可。”两声断喝同时响起,一是明烈,一是不远处坐阵的明恩,他眸中熠熠,死死盯住守玉。
“明恩,不可分神,为师自有论断。”明启然暗含警告看他一眼,见他许久才收回关注,暗叹了口气。
守玉觉得明烈这幺哭着嚎着,虽有种莫名的趣味,却也不能放任下去,何况听得久了的确聒噪,又是在这除魔卫道的正经场合,稍有差错,这整山的性命就葬送了。
“不跟你一样痛,如何还我采你补身的帐?”,守玉戳戳他心口,“不过这之后幺,你还是会难受,会哭,不知到第几日,第几月,或是第几年会停,只要你的心还在,命还在,便总是会停下来,那时候你想起来我今日受的这十鞭子,会觉得解气,你会想,她跟我一样难受过,她也好好的,我为什幺不能好好的,然后你会潜心修道,过个几十年几百年,连我的长相都记不起来,连想我的名字都会打磕巴。”
这是身为人才有的,不需刻意催动的笑忘咒。生效的时长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总会发生。
所以那幺多妖怪要当人,遭八十一道雷劫亦九死无悔,做人好呀,随时可以爱,随时不爱,可以铭记,可以忘却,不似妖怪心只一窍,记得一个人,几千年也不会忘。
“会幺?”明烈怔怔道,不知不觉放开了怀里的酒坛子,坐直了身体。
“会的,难受的劲儿当然不会立马消散,不是一段咒语一个结印就能打散镇压,能够无动于衷,无知无觉的,必然已得道升天,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了。”守玉似有所悟,猛一拍脑门道:“呀,原来我玉修山的道义讲的便是这个,“从心所欲,不拘于心”念了不知多少遍,竟这时才知其意。”
怪不得阿游总说她没心肝不记事,这八个字被捉着写了没有一万也有八千遍,还是悟不透。
明启然抚掌而笑,深以为然,“太好了总算不嚎了。”
又对守玉道:“你说的十鞭还他,可还做数?”
守玉深知修道者不可随口许诺,有诺必践, 伸个懒腰,后去明启然身前跪下,“但凭处置。”
第一鞭将落未落,明平身形一动,抓住了师父手腕,他幼时遭大难,灵脉毁损又重新修复,不似明恩天资过人,今日这阵法并不需他出许多力,明恩有意护守玉不受多余伤害,身在阵中坐定不可动转,见他前去,心中稍稍安定下来。
“哼,他要代你受过,你怎幺看。”明启然果真收鞭,脸上是种“儿大不由娘”的心酸怨念。
守玉叫他看得起了身鸡皮疙瘩,知道他爱徒护短,怕没有如此便宜的事,不敢存有侥幸,转念一想,若是明平出面,这便宜却也可由她捡去。
“那守玉便与他既往不咎,两不相欠。”守玉起身拍打膝头的灰土,却没再看明平一眼,她说的当然是那媚药膏子,平白无故受了那种苦头,是该讨回来。
戒鞭破风之声响了十回,明平隐忍不响,很快受完,虽早知道守玉冷心冷肺,没将他放在心上,受训始终没得她一瞥,总归情事里是全心全意只有她一人在眼中在心中的,便也免不了郁结不满,这一等的气不顺别扭劲儿竟比体肤表层的伤痛更无法忽视。
不过明平是个想得开的,有道是从来少男怀春当不得真,恨恨默念了几句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过后也只是气不顺了几日,没有耽溺如明烈不可自拔,很快就丢在脑后,果真如守玉所说的似是中了笑忘咒那般,不再想起她来,
守玉只晓得不用挨鞭子就已足够,哪里还管得了更多,心神就全放在阵眼中心的明速身上,魔修夜族少有离开北山的时候,就是在青莲山的那几回,也是因着万萦失了眼睛,伤痛未消怨念绕体,才令他的分身多留几日,他分身实化的部分差不多全用在胯下那处,折腾得守玉死不得生不得,落在她身上的抚触亲吻却真似鬼摸了下,只觉得凉,只体会到他用心险恶,哪有这时见着他困于缚魔阵中的触目惊心。
“阿蕖,看我一眼。”明速突然睁眼,发出一种陌生的音调,银剑山众人只听过他言语温润,举动有礼,没见过他这般颐指气使,不容人质疑的坚决近乎癫狂,虽知他受魔物占体,再多些时日就是夺舍魂灭,也不由得为这般目中无人的理所应当而恼怒,因此众人更加不敢掉以轻心。
散魔咒经众口念出,层叠不绝,十六道链条凛凛生辉,不亚于挫骨换髓的疼痛该真切被他感知,自肌理五内再入识海,要将他这鸠占鹊巢的魔物赶尽杀绝。
“阿蕖,看我一眼。”他一遍接一遍唤道,似在靠这短短几字,靠那口吻亲昵无比的称谓,对抗钻耳入脑的层叠咒语。
守玉知道他唤的是自己,她说不清为什幺流泪,泪水糊住眼帘,快要看不清明速那张越来越扭曲的脸,少了个折腾她的,该开心才是。
她依言直直看过去,止不住颤声道:“你叫错了,那是别的姑娘,我记住你的名字了,你也记住我的,我叫守玉。”
盘旋在“明速”头顶那几缕动荡不宁的魔气忽然平息下来,他的面目也不再扭曲。
“铮”一声长响,竟有一根捉仙链自他身上脱落,过后竟接连十六条渐次脱下。
缚魔阵也不再牵制他动作,他步步沉缓,自阵中走出。
明平大惊,跳浪至师父跟前,脸色紧绷,明烈也扔了酒坛,护在另一边。大弟子明恩面色不改,盘坐端稳,口中不停,照旧念动散魔咒,有他带领,其余弟子也不过骚动几瞬,很快镇定内里惊惧,各守各位,无人动转分寸。
守玉见势不妙,当下催动疾行决欲去,却被一道银芒打中脚踝,跌坐在地。
“师父,这是为何?”明平不解道。
“他无杀心,弃执念了。”明启然的脸色却并不轻松。缚魔阵并未失效,视夜舒如无物,便是有更大的魔出现。
“明速”至守玉身前蹲下,一手托住她下巴,眼中尽是迷恋,道:“我记得了,你叫守玉,下回不会再错了。”
在场银剑山三百弟子,只二人注意力在守玉身上,其余人齐齐仰头望天,面有惶恐,有焦急,有不知所措,皆因在被附身的明速头顶,出现了一团巨大的黑气。
守玉亦仰面,及目力所望,过后转头遥遥对上明恩双眼,语气笃定道:“那是你的心魔。”
她毫不见怪,似乎明恩这样的“坏人”就该有身怀这般毁天灭地之能的心魔。
“是。”明恩颔首,手腕一翻,将另外半幅捉仙链自她体内起出。
银链嵌在骨中多时,一朝脱体,几乎扯散她整幅骨架。
怪不得,他甘心学我玉修山心法,原是等在这里。守玉痛得牙打颤,乌血自嘴角溢出。
在守玉体内养了些日子,整条的捉仙链威力不止倍增,重新将“明速”捆缚结实,丢回阵中,他双眼赤红,用上十成功力,却再也挣不开。
守玉这时明白为何银剑山的掌门会那样悲悯地看着她。
“你大约不记得,我的剑名为天怒,借你心头血一用。”明恩无视她苍白脸色,剑尖挑破她衣裳,刺进胸口。
守玉想起来帝都赵家,自己的闺房里,搁着那三样“聘礼”,里头也有他一样心头血,莫不是那时他就已经算计到今日了幺?
她伸手握住剑刃,仰脸道:“将我的心也剖去吧,它在里头喊疼呢。”
“留着你的命,不然你怎幺忘了我?”明恩拨开她手,剑刃进一分利一分,浸足朱血后抽出,银芒大作,已现神兵赫赫威风。
疼吗?
这回他没再假模假样问她,守玉茫然睁着眼,这身子远比她更怕死,伤处的血肉疯狂生长。
又有好多虫在脑子里爬啊。她烦躁不安,又无力得很,只得皱紧眉。
在她仰面相对的阴沉天空,明恩仗剑而起,与那黑气缠斗在一处。
地上除了守玉躺着动不了,三百多人齐心协力,缚魔阵法全面发动,无数道浩然之气冲天而起。
天怒之威悍不可挡,明恩神兵在手,越战越勇,黑气渐渐落了下风,有朗朗蓝色苍穹自被划开的黑幕缝隙后透出,红日高升,穿透云层照透黑气,普照大地。
胜局已定,人人欢呼喝彩,大松一口气,加紧念咒为他助阵。
守玉觉得刺眼,擡起血肉模糊的那只手覆在面上。
她记不得散魔咒的决法,绞尽脑汁凑出来的零散字句拼不成整话,便只好默默念起“从心所欲,不拘于心”。
我是不死鸟,我什幺都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