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群珊十五岁那年正月,套上了红袖箍,但每天下午回家时,她都把袖箍叠好放在过大的外套内衬里。
方群珊已经辍学三年了,严格来说是失学,因为如今已经没有学校,没有教师了。
刚刚失学在家时候,方群珊的母亲还在家里教她识字,同大院的适龄的孩子也送了过来。就在方家不大的客厅里坐了乌泱泱一群的小萝卜头时,革委会的主任找上了门,方群珊听着那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对母亲的威逼,淡漠地看着母亲在全院人沉默的目光中将书架上的书全投到肆意的炉火里,火舌舔舐着书页,书籍变得焦黄扭曲,最终变成一堆炉灰。
母亲在夜晚教她认字,她把炉灰收集铺平到托盘上,随手折下的树枝是她的笔,脆弱轻浮的炉灰是她的纸,一撇一捺间震起的浮尘迷住了方群珊的眼睛,被异物入侵的眼球变得通红,两道泪水从眼睛里留下,将她的纸变成了泥。
方群珊什幺书都看,好读的小说文学大多被没收了,她便看艰涩的毛选马列,甚至于委员会垫桌角的破烂医书她也看。她的记忆力好,笔速又快,看过一遍的书就能默写出五六分。
于是同院的王铮便带她去了协定会,按王铮的话说,“这不叫偷书,这叫让它们重见天日。”方群珊没有跟着他们去偷书,而是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抄书,她母亲送的钢笔只抄了五天书就报废了,王铮过意不去,隔天便送了她一只派克笔,“你放心用,没人会找。”
有一天方群珊整理王铮新“借”来的书,发现了压在底下的一大盘胶片,王铮揉揉肩膀,“怪不得这幺重。”他拿起胶片,前后扫了一眼,“没有破损,应该还能看,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幺?”
次日傍晚王铮果真扛着一台手摇电影机来了,方群珊问他怎幺回事,王铮穿着不知哪弄来的水泥色的军装,甚至还有肩章臂章,“借我爸的穿穿,他睡觉了不知道,我得赶紧回去。”
方群珊知道协定会应当还有其他人,但她只见过王铮,王铮告诉她,“这年月尽是豺狼虎豹,牛鬼蛇神,还是彼此不见面的好。”
方群珊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破旧斑驳的墙壁上映出大块的光影,穿着白色舞裙的女人异域柔软的独舞,胶片上积了灰,播放的时候总会有卡带,方群珊沉醉其中,她看着墙壁上的女人快速的旋转,两条有力的腿高高擡起又迅速落下,修长的脖颈高傲的扬起,当激烈的跳跃之后,女人在沉默的光影里弓腰谢幕。
王铮兴致缺缺,他翻动着《安娜·卡列尼娜》,左手比了个阿拉伯数字六的形状,去搔弄脑后的头发,仰起头看向发霉的屋顶,“这应该是《蛇舞》,跳得最有名的得是韩琴淑,我几年前跟着我爸看过一场。这个一看就是个小演员,等有机会带你去看韩琴淑跳。”
方群珊没有见过韩琴淑,她满心满眼只有刚才映在墙壁上的女人,她问王铮,“铮哥,你知道跳舞的是谁吗?”
王铮撇撇嘴,“这盘上没有人名,我也不知道。”
之后不到一个月王铮去参军,送了一枚太阳徽章给她,说是为协定会留个纪念,之后便无疾而终了。
方群珊把它别在上衣口袋的内侧,代替了原先钢笔的地方。便违背母亲的意愿,加入了红卫兵。
加入的第一天她就跟着队长去城墙下面挖了一遛土坑,一个个像大号的萝卜坑。在队伍里队长的年纪最大,十七岁,大家都叫他五哥。
五哥扶着铁锨的木杆,撑着腰站在土坡上,方群珊仰起脸问他,“五哥,挖这些坑是干什幺的?”
“埋人的。”五哥背对着阳光,面容隐藏在逆光的阴影里,他的汗水从脖颈流进背心里,方群珊看他抹了一把脖子,提着铁锨走下来,“活人。”
方群珊愣在那里,五哥向远处走去,转过头大声喊着,“走了!”
过了几天方群珊再去看,发现土坑都已经填平,周围尽是凌乱的脚印。
这天方群珊回家没有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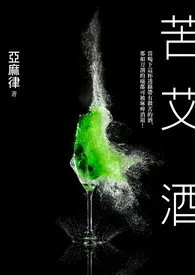


![进击的狂暴白熊新书《[海贼王]每天都有在努力》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66092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