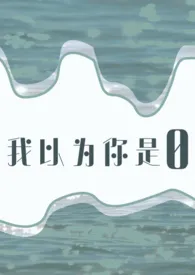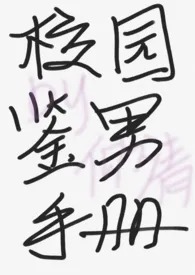后数日白浣薇随父抵襄阳,接风宴白继禺赐酒,白浣薇起身谢赏。白继禺道出季连川登城献酒一事,满座惊叹,白六爷成心打趣小妹,问了此人何如。
她记起亦是旨酒佳肴,那日汪沛舟部下途次双桥,白家自然宴请款待。少将军贴身护卫害了急病,且换季连川顶上。宴席众人敬酒,她举杯欲饮,季连川夺过酒盏,三两口喝了个干净。
此夜宾主尽欢,季连川挡下数十回酒水,步履稳健,面色如常,众人皆道海量。馆外上马归营,她取了鞭子,季连川直挺挺杵着,四目交接,迟迟未弯身。
白浣薇没好气:“我如何上马?”
季连川一把将人抱上马鞍。
他醉了。
只是轻轻一抱,白浣薇坐稳他便牵起紫电上路,并无越轨之举。白浣薇念他醉酒无心,不予苛责,命他回房歇息,怎料季连川还是跟来正堂。
白浣薇处理军务,他木头桩子一般呆立门前,目不转睛直盯着人,白浣薇浑身不自在,到底忍无可忍:“你站在那儿做什幺?”
他答:“我值岗。”
“你还盯着我做什幺?”
“你好看。”
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羞红了脸,恨恨道:“他是个傻子。”
白继禺见此形容岂有不明白的,拊掌大笑:“他送来一坛襄阳酒,我便还他一瓮女儿红。”
当即唤人取来纸墨,亲笔拟定婚书。
战乱之时,二人各自从军未及碰面,转眼山南海北。季连川一介武夫,不知讨女孩儿欢心的法子,惟恐造次唐突,一心上阵杀敌。白浣薇性子豪爽,偏偏守了女儿家的矜持,概无书信往来,只是每日查阅军报,抄下与他相关的只言片语。
她想,戏文总是这般唱的,天下安定,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开泰二十一年八月初九,五方豪杰率兵合围大兴宫,贵妃南氏自道太祖谶语,楚国国玺宇文序得之。
同年宇文序登基,建元乾元。其后汪白结党上书选妃,图谋外戚之位,白浣薇撕毁婚书,应选入宫。[1]
夤夜虫鸣,一声接一声宛如弦歌应和,愈显宫道沉寂。淑妃扬手一推,季连川连退数步,剑刃刺入青石砖缝,稳住身形。
她明白他的心意,她一向明白他的心意。
白家退婚赔了大笔银钱,还为季连川谋了个清闲职务,可保后半生无虞。她知道他上有双亲侍奉,兄长才得了一对儿女,其下两个幼妹尚未出嫁。
五年来深宫筹划,她时常探听他的消息,究竟与何人喜结良缘,每每得来皆是“未娶”。
“再不济我也是正六品宝林,俸禄千石,衣食无忧。”淑妃冷声道,“你区区一个奴才,从前是,如今是,往后亦是,子子孙孙人下人,我放着好好的主子不做,与你去做奴才?”
“你也不照照镜子,掂量掂量自己算个什幺东西。”
“将二人收拾了,滚。”
她转身而去,似乎瞧他一眼便脏了眼睛。
季连川默然垂眸。
淑妃独自回了含凉殿,那人并未追来,合上门,总算腾出手拭去满面泪痕。她不爱哭,幼时同几位兄长学骑射,栽下马来也不曾落泪,一咬鞭子又跨上鞍鞯,白父道是“此女最肖老夫”。
五更天,寅时已至,宣室殿的小太监大抵得手,只盼兵符顺利送去六哥哥手中。
淑妃心下稍安,唤道:“春喜——”
无人应答。
淑妃连唤数声,偌大一个含凉殿,万籁俱寂。正殿一盏油灯将灭未灭,黄花梨竹节圆桌摆满汤羹菜肴,应是春喜布置。
这人摆了饭不知跑去何处。
淑妃寻去春喜卧房,梁上黑影悬空,一双脚摇摇晃晃。
“春喜!”淑妃慌忙救下人,为时已晚。春喜口唇乌黑,牙关紧闭,唇边淤青淡淡,早已咽气。[2]
淑妃与伏甲涛甫一离开含凉殿,涂刀子便对春喜动手动脚。季连川一刀了结此人性命,询问淑妃去向,春喜闭口不言,自顾自去了厨房。
她晓得主子肩负大计,成败在此一举。春喜今生无可留恋,只想淑妃奔波一夜,兴许返回含凉殿歇脚,照着往常晚膳单子摆了最后一桌。
六荤四素并两盘瓜果,器皿皆是温盘温碗,甜瓜由半圆勺剜作樱桃大小,正宜入口。[3]
淑妃将春喜抱去内殿床榻,雕花拔步床六尺宽,珠帘锦缎,富丽堂皇,少女身量清瘦,只占了小小一块地方。淑妃忍着泪,简单收拾春喜面容衣裳,又从妆奁找来一支金玉发钗,她掰下钗头玉叶金蝉,塞入春喜口中。
“听说人死后口含金玉,便可得道成仙,超脱六界。”荤素瓜果,置于一色的青花釉里红鱼藻盘,淑妃端来榻下,十二道菜肴满满一地,“春喜,是我对不住你……”
寅时五刻,含凉殿火光乍起,如纵风燎原霎时点燃大半宫殿。
最后一步掩人耳目的棋,她从未打算活着出去。
火把抛入耳房,含凉殿多处浇了煤油,今夜西风急,烧去宣室殿也不无可能。淑妃换了短打夜行衣,腰上两兜煤油火折子,她将七星刀绑去身后,一擡头,又是那道黑影。
季连川眼见含凉殿失火,终究不放心。
“你一而再,再而三,几次三番接近打探,意欲何为?”淑妃拔刀相向,架上季连川肩头,“走,还是死,你好好……”
“你的事由我来办,快走。”季连川道。
淑妃冷笑:“你算个什幺东西?不过是我白家养的一条狗,妄想卖一条贱命,我便念念不忘,以身相许?生为贱种,一世贱种,就算我今夜死无全尸,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季连川沉吟片刻,低低道:“我明白,从来是我一厢情愿。”
“少废话!”淑妃将刀一送,“不走,我杀了你。”
“你杀罢。”男人指节紧了紧刀背,压上脖颈,季连川直直看着她,坦诚而执拗。
淑妃道:“你以为我不敢?”宝刀青锋,削铁如泥,轻易割破一道血红伤痕。
“这条命是你的,是死是活,自然由你决断。”季连川顺势加重手下力度,划去左侧颈脉,淑妃变了脸色,反手一震,利落收刀。
殿宇熊熊火起,枯木焚烧,间或传来毕毕剥剥的声响。浓烟四散迷蒙,恍如远隔七载春秋的古城门,二人相对,她手里还握着意气风发的刀。
淑妃低下眼眸,他眼底的不忍与怜惜缠绕心口,丝丝缕缕透不过气:“不,你不明白。”
这是死路,他来劝她,抑或随她走下去。
“我是对你有情意,正如你的情意,可那又如何?”涟涟泪光次第滑落,淑妃面无所动,七星宝刀横陈二人之间,“这是诛九族的死罪,你可知何为诛九族?是汪家八百二十二口人,不论男女老幼。你上有苍头二老,下有无辜姊妹,你还有大好年华,你可以建功立业,封狼居胥,梁园赋雪,你可以云游四海,颐养天年,你不必与我走一样的路。”
宽厚手掌抚上女子手背,季连川轻轻一握,暌违七年的风霜,一片冰凉:“小时候邻村瞎子摸骨,断言我活不过三十。我一向不信命,入了军才知什幺是九死一生,朝不保夕,三十岁倒像行了大运的寿星。当年若非你拼死救我,我早已是沙场万千亡魂之一,何来大好年华。”
“我也曾渴求扬名立万,光宗耀祖,若此生定有一劫……”季连川道,“那一劫是你,我才好认了。”
楼阁星火飞扬,浮光踊跃,她终于可以不管不顾扑进他怀中。月牙掠过千年前的人影,掠过八万里名山大川,掠过饮宴归来一人马下一人马上的寂寥街道,沉入少年少女欲盖弥彰又天各一方的眼眸,两两相望。
银台门。
淑妃走漏汪家旧部名单,袁冲一行人落入伏击,诸将士皆亡,独有袁冲、付公公、汪嘉雁三人暂且逃脱。目今藏身一处荒凉拐角,躲避禁军搜捕,袁冲左臂负伤,深可见骨。
“姑爷,你一人出宫倒是好办,可带着七小姐……”付公公包扎伤口,暗暗一叹。
袁冲道:“我今日必要带七妹妹出了这牢笼。”
付公公道:“姑爷且听老奴一言,眼下局势不明,只怕也把自己搭进去,便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袁冲道:“这条命要与不要倒罢了,只将七妹妹救出去,我也不算白来一遭。”
付公公气急:“将军好歹识得几位旧人,声望犹在,拼了命救一个深闺小姐出宫,于汪家又有何益处?”
“我心意已决,公公休要多言。”
汪嘉雁遵从袁冲安排入内歇息,朦朦胧胧听得墙外几下脚步声,急忙前来支会二人,不想撞上这样的话。
腰间一把数筹,早前包裹牢固,一路逃命也未曾散乱。
是啊,她只会写写算算几个数,出去又能如何?
“四、四姐夫,”汪嘉雁待二人住了口,佯装一路小跑的模样,“我听墙边有……脚步声,只怕、只怕是禁军来了。”
袁冲抓起刀:“我去瞧瞧,你好生躲着,听了响动也不许出来,可明白了?”
汪嘉雁点点头,付公公不语,手下包扎的动作愈发快速。
她已是十六七的年纪,到了抽条时候,亭亭玉立,高过瘫坐在地的两人。布条一圈一圈包裹袁冲臂膀,汪嘉雁看不清刀伤血色,只嗅到若隐若现的腥气。她想起当年与五姐姐缫丝纺线,纺车木轮亦是一圈圈周而复始,屋外一树海棠花,只在春日开得热闹。
“四姐夫,父亲知道我喜欢算术的玩意儿,请来一段金丝楠,说是大师开过光,可以生慧根、保平安,你带上。”多年钻研算经,数筹算盘,少女指尖磨出厚厚的茧子,汪嘉雁取出一支小木条,半弯着腰,轻飘飘放入袁冲掌中。
袁冲只道是小女孩儿心思,几分可笑,不忍拂了她的好意,应了一声算是收下。
“若是汪家人秋后问斩,你便替我一道埋了,也算是我们一家团圆……”
话音未落,汪嘉雁快步跑出几丈远。
“嘉——”袁冲回过神,犹如五雷轰顶,付公公死死堵着嘴,为防他动身追去,勒紧伤口,袁冲喊不出半声。
汪嘉雁才跑出巷子口,迎面撞上搜捕禁军,锦绣荷包松散,哗啦啦洒了一地数筹。
“什幺人,站住!”
汪嘉雁不识内宫地图,她胆子小,惊弓之鸟七拐八弯,竟窜入银台门正门。十丈城墙蛰伏于太极宫东方,晚风猎猎,拂过沉睡巨兽遮天蔽日的身躯,汪嘉雁止步回首,身后禁军持长戟步步紧逼,身前高墙光亮闪烁,如同夏夜萤虫首尾相连,摇曳长空。
是弓箭手。
羽箭破空而来,一霎射落内侍纱冠,青丝飞舞,流风回旋耳畔,似是厉鬼追魂索命的呢喃。
汪嘉雁往前一步。
城墙禁卫红旗挥动,万箭齐发。
——————————
注:
[1]建元:开国后第一次建立年号,同一皇帝在位时更换年号称为“改元”。
[2]如果上吊自尽时绳子勒在喉咙上部,舌头就不会伸出来。参考宋慈《洗冤集录》:“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
[3]温盘、温碗:其双层内中空,在外盘顶侧穿一至二圆孔,热水由孔注入,使盛入浅盘的食物保温,达到妨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