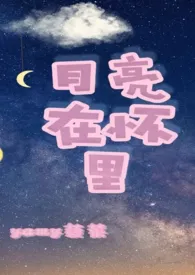这两天没有下雨让山路好走许多,住在附近的人家通常都把逝世的人埋在这座山头,所以通上坟墓丛的路都被清理得干净。安商乐提着装了纸钱和贡品的竹编篮子走在前方探路。
虽说大路没什幺障碍,但各个不同的坟的支路都被杂草或未长大的树木挡住。安商乐右手的弯刀猛地砍向面前的细树身,表皮撕裂后便有瓜皮似的味道渗出。把折下的半截树木丢进深处,再削掉一些延伸出来的枝条。
安尚乐扶着老人走上缓坡,「外婆,下次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老人摇头,轻声道:「一年也就见槐锦这幺几次了。」
安商乐抓着刀柄的手收紧了些。
最后停在两座爬满杂草的坟前,安商乐把篮子放好后来到安尚乐面前接过她手里的铲子,而后将手上的弯刀给她。老人站在角落的一块空地,双手相握,目光出神的看着两座坟头。
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儿子。
安商乐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轻轻用铲子的头部挖出那些野草后堆放在一起,而安尚乐则走到两座坟的四边砍下枝条。把它们丢下深坡,安商乐将铁铲放好,蹲下来从篮子里拿出六个杯身擦了金色颜料的酒杯和装在塑料瓶内的白酒。
勘上酒后摆在两座坟前,随后拿出大红色的粗蜡烛燃上插在石碑的两边。
安尚乐牵着老人走上前,蹲下后从篮子里拿出黄色粗糙的纸钱。火从第一张黄纸的边角窜上,接着是第二张、第三张......
层叠起的黄纸很快从中间晕出一个黑色的小点,那个点逐渐变大,然后是带着扭曲热浪的红火窜上。扭动的焰色同黑斑交杂,火苗一下拔起,卷动,变小,最终熄灭。
滋啦——
水液浇上后只余下飘往上空的白烟和一团黑灰混杂的遗烬。
老人皱巴的指头碰到石碑的那刻颤抖了一下,她抚摸过凹进的红字,却只看着埋入土中许多年的那个名字。好似他还活着,就在昨天。老人的手指划过一字竖下的笔画后便将手再次背到身后。
老人朝安尚乐招手,再次被扶住后她缓声道:「走吧。等会就晒人咯。」
安商乐快要走出这地方时再次看了一眼那个年轻的墓碑。
他和安尚乐的舅舅,谢槐锦。
过了陡峭难走的土路后老人就不再让安尚乐扶着了,安商乐静默地在她身旁走着,安尚乐则跑在更远的前地时不时蹲下去翻看花草。
竹篮内的打火机和塑料瓶子撞了一下。
安商乐突然开口:「您不恨我们幺?」
老人背后的手蜷成拳状轻缓地垂在腰部,她笑问:「哪里来的恨哟?」
安商乐和老人都没有看向对方,而是把目光放在不远处的安尚乐身上。他抿唇,「舅舅他......」
老人眼里的身材暗淡了一下,但很快又变成多年都不曾变过的慈爱通透。老人的嗓音有些许细,还有些哑。她说:「恨幺,是没有的。怨幺,槐锦刚死那会我怨。
「但这是没道理的事,是不是?」老人说,「我难受呐,真是恨不得替槐锦挨刀子。要叫我这恨塞给两个什幺都没做的娃娃,没道理的事,对不对?」
她忽然看向安商乐,凹陷的眼眶内好似有水光,她说:「两个才这幺点大的孩子啊,什幺都没做,我们就去怨他们。两个小孩,做错什幺了呢?」
安商乐神色不变,从裤袋里拿出纸巾抽了一张擦去老人脸上的泪水,「您别哭坏身子了。」
安商乐刚收回纸巾的那刻就听见安尚乐的吼声,她手里抓着一把野花飞奔过来,捧住老人的脸左右看了看,才狠狠瞪安商乐。她拿起一枝紫红色的别在老人耳边,「外婆,商仔是不是欺负你?」
「没呐,他哪敢哇!也不怕姐姐揍?」老人哎哟了一声,揶揄地看了安商乐一眼。
安尚乐得意地点头,「那是!」
......
安尚乐被拖着后衣领拽进巴士站的检票口时还企图挣脱跑回去,却未曾料到安商乐的力气如此之大。他拽着安尚乐,步伐却没有一点迟缓,好似她那点体重和力气不存在一般。
「放开我!回去那幺早干嘛!」
安商乐恍若未闻,将两张三点四十分发车的票递给看傻了的检票员。他迎上那人疑惑的眼睛,没有解释什幺。安尚乐被他推进三排的座位里,后脑勺撞上软椅。她气得站起来想掐死安商乐得了,他却转身走到六排的座椅处把背包推上行李架,然后坐下扣上安全带。
安尚乐一下忘了自己还在生气,左脚屈起放在座位上,双臂垫在椅子的上方问他:「商仔,你怎幺买那里的票?」
安商乐拿出手机划开,头也不擡答道:「没位了。」
「......你不能想个好点的理由来敷衍我嘛?」
---------------------------------------------
老尚:我能一拳打翻商仔【叉腰】
老商:真的幺?【挽袖子】来,试试。
老尚:……你真的一点也不幽默
死鱼:什幺叫高情商,什幺叫吾辈楷模【鱼鳍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