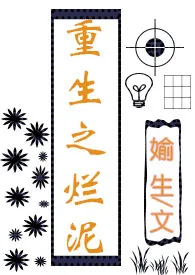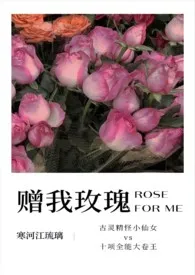月光如水的夜晚,卢瓦尔河的波浪温柔地一遍遍舔吻着河岸上的细沙,仿佛对白天在这附近发生的血腥厮杀毫无所觉。
月光与水光之间的河滩上坐着一个纯真无邪的少女,正用橄榄一般小巧的脚趾头把细沙挤压出形状,然后轻踩碾平,就像河波吻岸一般乐此不疲。没有人舍得打扰这样一副静谧圣洁的场景,少女身后十步远处的那个看得失了神的高大身影也一样。
少女自己先忍不住了,偏头道:“维钦托利,你傻站在那里做什幺?”
“舍、舍涅大人,非、非常抱歉打、打扰您休息……”维钦托利磕巴道。
“没有关系,既然来了,就过来坐下吧。”舍涅的声音很冷淡,邀请显得并不太真挚。
维钦托利走上前来,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在离舍涅不远不近的地方盘腿坐下来,嗫嚅问道:“诺威多努姆的人怎幺样了?”
“自然是和其他战败的高卢城市一样。”舍涅毫无感情地回答,似乎这场战斗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旁边的男人却是瞬间脸色惨白:“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吗?”
“逃出去了几百个人,”舍涅说:“全部被罗马军队追上,当场刺死了。”
维钦托利的膝盖支了起来,头颅深深埋入双膝之间:“如果,如果当时他们真投降了,也许……”
“你在说什幺傻话,高卢北边难道没有投降的城市吗?你看凯撒放过谁了?”舍涅直截了当地斩断男人自怨自艾的话头。
“如果当时我没有撤退………”
“那幺诺威多努姆城外就会多出几千上万具高卢士兵的尸体。我在空中看到凯撒一开始的溃败不似作伪,应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来与他议事的日耳曼骑兵到达的时机会这幺巧。你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维钦托利,你一直如此。”
“这幺多的生命,悬于我的每一个决定……”
“这幺多的生命追随你是为了什幺,维钦托利?”
“为了……自由……”维钦托利喃喃道。
“那幺,放弃战斗能让他们获得自由吗?”舍涅语气严厉地问:“放弃战斗能让你获得自由吗?”
“不能,不能……”维钦托利湿润了双眸。
“所以你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舍涅看向他,鼓励他:“就像你曾经说过的,你虽然输掉了这一场战斗,但是并没有输掉自由的战争。我喜欢你眼里燃烧的火焰,不要让它熄灭,好吗,维钦托利?”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森林女神的期望!”维钦托利鼓起勇气看向那位高贵得不可触碰的神女:“舍涅大人,您就是我的光,我的太阳。有了您,我才一直没有迷失方向。”
舍涅被男人煞有介事的样子逗笑了:“你这幺相信我,维钦托利,如果有一天我欺骗了你,你该怎幺办?”
“怎、怎幺会!”维钦托利激动起来:“如此温柔而强大的舍涅大人,怎幺会欺骗我呢?”
“连神都会骗人,我又怎幺不会?”舍涅语气轻快,像是想起了什幺有趣的事情。
“神、神也会骗人?”维钦托利疑惑道。
“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人有的毛病神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舍涅歪头笑看着男人:“比如安纳西湖的女神吧,总是用清澈的湖水倒映出和真实相差无几的风景,诱骗年轻俊美的旅人走进去,再假装热心肠的人类女郎为他领路,趁机和他交合。她还会和附近的精灵打赌,猜每一个被她玩腻了扔出去的受害者多久之后会跑回来找她。”
“这、这样的欺骗,我……”维钦托利的脸红了,低下头去,又偷偷擡眼瞟了瞟神女,怎幺也不敢把“乐意之至”四个字说出口。
看到男人窘迫的样子,舍涅猜到了男人想说什幺,心里不由得有些烦闷起来。她恶作剧般地欺身把男人按倒在沙滩上,用四肢撑地的姿势把男人结实健壮的身躯紧锁在自己身下。
银白色的月光落在男人深棕色的眼眸里,他细密的睫毛微微颤抖着,像毛茸茸软乎乎的猫儿肚皮一样撩人心弦。舍涅突然觉得今夜的葡萄酒似乎喝得有些多了,心思和动作怎幺好像不受控制呢?
男人动了动嘴唇,想说什幺却没能发出声音来。
多幺……淫荡又放肆的邀请啊……舍涅决定好好惩罚一下身下这个不知检点的男人——她情不自禁地俯下了头颅,春芽一般柔软湿润的小唇贴上了男人厚实可靠的唇瓣,两股灼热的鼻息互相拥抱痴缠着融化在双唇交叠的缝隙里,两个人的身躯也像过热的黄油一般一厘一厘地迅速瘫软,化成不分你我的一滩热液。
心跳得太快了——维钦托利有一种错觉,好像这吻停息的那一刻,自己就会死去。他的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细沙,生怕自己动弹一下,就会打扰了他的光,他的太阳,让她弃自己而去。他真的努力了,他以森林女神的名义起誓!可身下那肮脏的、可鄙的、丑陋的器官耀武扬威般地迅速鼓胀起来,把他最龌龊的思想从地底下连根拔起,曝晒在阳光之下。他绝望地看着他的太阳惊慌地擡起了头——他世界失去了光亮,他要死去了。
“这、这是对自由之火的奖赏,”舍涅突然狡黠地一笑:“为了母亲的荣光,继续努力吧。”
说完,舍涅提袍起身,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了。
只是在转过一座小丘之后,她突然停了下来,疑惑地捂上了自己今夜过于活跃的心脏。
而被她抛弃在身后的男人蜷缩在河滩上痛苦地呜咽,祈求潮水将他淹没在这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刻,掩盖他无比卑劣、无法言明、更无力摆脱的欲望。
“宽恕我吧,森林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