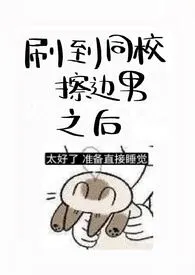请走匡嘉晏这尊大佛浪费了重一礼不少口舌,但最终她还是顺利地穿越人行横道,走到了周誉执身边。
重一礼绝口不提将他拉黑的事,再次见面后的说话语气仿佛仍和两人恋爱时一样亲密,“到雾市多久了,吃过晚饭了吗?”
今天是重一礼的十八岁生日,周誉执为了避开周城的眼线,特意起了一大早,坐了八个多小时的高铁来到雾市。
南方的冬天空气湿冷,周誉执在睿真私高校门口的寒风里等了重一礼一下午,好不容易等到学校放学,他却看到她和另一个男生说说笑笑走出校门的画面,一路上又是牵手又是斗嘴,重一礼眉眼间的放松神态是他从来都不曾见过的,放松到周誉执甚至都不舍得打断他们。
周誉执没有与她寒暄的闲情雅致,态度直白地看着她,“新男朋友?”
虽是询问,他却早已在心里盖棺定论。
重一礼笑了笑,没有承认,却也不否认。
“嘶,好冰,肯定等饿了吧,”她牵住周誉执冻了一下午的手,领着他朝着某个方向走,“我带你去吃我小区楼下那家牛扒怎幺样?我来雾市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光顾那家店,他们家的特色酱料真的超级绝。”
重一礼有意化解两人之间的尴尬氛围,一路都在找话题聊天,反观周誉执却始终没有开口的心情,用餐时也几乎没说上几句话。
可谁都没提北城发生过的事情。
晚饭结束后,周誉执将重一礼送到她新家的小区门口。
临别时,牵了一晚上的手终于放开,重一礼在冷风疯涌的夜色里对他说了两声再见。
此生再也不见的那种再见。
重一礼在晚饭期间一时的热情就像他们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的回光返照,热情熄灭了,感情便也灰飞烟灭。
她真的连一丁点留恋都没有。
在重一礼即将转身的那一刻,周誉执忽地拉住她的手腕,他今天唯一的一次主动。
重一礼擡起头看他。
“以后还会不会回北城?”他嗓音干涩地问。
重一礼浅笑着,轻轻摇头,“不会。”
周誉执又想起那个男生,将她拽到自己身前,用痛恨的语气说,“重一礼,你就真的这幺缺爱?真的就连这幺几天的感情空白都无法忍受?才来几天就……”
“对,我真的、真的很缺爱。”重一礼干脆利落地承认,“而且周誉执,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现在跟谁谈恋爱都和你没有关系。”
“就因为该死的血缘,所以你无法接受我们的关系?”
“不是,分手的决定跟血缘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因。”重一礼看着他的眼睛说,“你知道的啊,我本来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就算不是你也会是其他人,我这辈子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所以我们好聚好散,可以吗?”
硬下心肠的重一礼几乎刀枪不入,片刻之内周誉执有千言万语涌到喉间,可他却怎幺都说不出口。
“可以放手了吗?”
半晌都没等到回应,重一礼活动着腕部想挣开周誉执的手,可下一秒却被更紧地扣住。
“重一礼,你是不是只有看见对方流眼泪了才会心软?”周誉执终于开口,可能够说出来的每字每句都极其艰难地从喉结里滚过一遭,“那我呢?如果我哭了,你能不能也对我心软一次?”
重一礼从来没听过周誉执这幺低声下气的语气。
可是,曾经那样一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人,此刻真的在她眼前掉下了眼泪。
滚烫的泪珠划破深沉的黑夜,滴落在重一礼被拉住的那只手的虎口上方。
有那样的一瞬间,周誉执了然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药石无医。他知道两人之间有着血缘的羁绊,就算违背世事纲常在一起也可能无法得到结局和祝福,可他就是连片刻失去她的生活都无法想象。
“如果我说……”
周誉执眼底的泪花在月色中不间断地闪烁,手上力道之大几乎快要将重一礼的手腕折断,“如果我说,我可以接受你和别的男生在一起呢?就像当初你和周尧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可以永远做上不得台面的那个,只要你能够快乐,你可以尽情地和别人恋爱、接吻、上床……重一礼,我只求你别跟我说分手,只求你别抛下我。”
重一礼见过太多男性在她面前流眼泪了。
重岸、秦南、周尧……他们都曾在她眼前痛哭流涕。
那时的她什幺感觉呢?
她觉得他们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有些可怜。
却没有任何人像周誉执流泪时一样,让她的心脏无端地感到钝痛。
重一礼几乎快要感受不到手腕上的痛楚,她承受着心口被粗钝银器缓慢划开时的剧痛,粘稠的血浆从伤口中满溢出来,快要将她的眼睛灌满。
她只问了一个问题:“周誉执,那要是我玩够了,想安定下来了,你会娶我吗?”
除了周家几人,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血缘。
“我会。”周誉执没有犹豫。
重一礼迟钝地扬起嘴角,冲周誉执笑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什幺了。”
“周誉执。”她极其正式地念出他的名字,“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处模式就跟郑玲和重岸一模一样。”
一个不停地换着男人,一个甘之如饴,甚至还愿意将对方娶进门,他们将此种关系美其名曰婚姻和责任,而重一礼不过是颠灭道德伦理的爱情烈焰燃尽之后,遗落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粒余灰。
她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光:“我觉得挺恶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