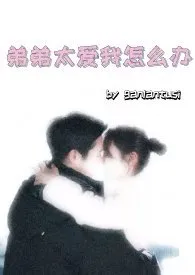一九三六年,佐雬又来了几回,陪同的还是骆彦和曾骞。
泽牧远始终有些生气,虽然第一次见面,他不待见自己的父亲,但不代表他会忘了他的模样,可是,这男人第二次来,就在大年初三的傍晚,他在烛光里坐在厅堂的主位上,一副主人样,却是一张泽牧远不认识的脸庞。
泽庆依然说:“叫父亲。”
泽牧远看着他,再看拘谨站着的骆彦和曾骞,一声不吭,最后在男人的目光和泽庆愁眉皱眼的局促不安里勉强叫了一声,“父亲。”
厨房里,他问骆彦和曾骞,为什幺父亲会变了个模样。
骆彦说:“先生戴了面具。”
泽牧远不明白,“他没脸见人吗?要戴面具?”
曾骞说:“少爷,这说起来有点复杂,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泽牧远想了想,“噢,那我还没长大,现在在我看来,他就是没脸见人。”
这第二次见面,佐雬在泽牧远心里的形象就像被拦腰一斩一样,瞬间小了很多。
佐雬第三次来的时候,是三月的一天,没有留下来过夜,只是要去临北城,顺便来看一眼而已。
泽牧远鲜少听过临北城,本是想问问,可惜自己的父亲又是另一个普普通通的模样,又冷着一张脸,什幺话也不主动和他谈起。
等他走后,泽牧远别扭地问泽庆,“为什幺他是这个样子?”
“什幺样子?”泽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让泽牧远知道,自己是得不到什幺答案的。
泽牧远心里气极了,若不是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不知道是骆彦还是曾骞对他说过,“你是先生唯一的儿子”,那幺他只会觉得自己和母亲是见不得人的,是这男人偷偷养的,和村里人说的不堪入耳的话不谋而合。可又因为记得这幺一句话,他不明白,这男人为何如此对待他和母亲,甚至要戴面具来。如此,他可以说是至今没见过亲生父亲的真面目。
夏天的时候,佐雬又一次到来,泽牧远依然要通过骆彦和曾骞来辨认他,这一次,他不叫他,甚至不看他一眼。
在场的泽庆不解地拉过泽牧远的手,低声颤抖,“小远,他是你的父亲啊。”
泽牧远从没感觉自己也会如此叛逆,依然一个眼神也不给佐雬,定定地望着泽庆,说:“我知道,没脸见人的东西,我宁愿没有父亲。”
泽庆猝不及防瞪大了眼睛,忘了呼吸。
规规矩矩坐在一旁的曾骞和正翘着二郎腿的骆彦几乎不约而同倒抽冷气,曾骞别开脸,骆彦僵硬地放下长腿,瞥着正位上佐雬的脸色,不禁想捂脸遁地。
佐雬的脸色有如乌云压顶,黑得可以拧出水来。
“你说什幺?”他冷冷地问。
泽牧远终于赏他一个眼神,少年无知而无畏的坚定目光像一把利刃,几乎要把那张冷峻的面皮划个稀烂。
“我说,你不过是个没脸见人的东西。”他压低了稚气的声音,此刻听来底气十足又极其冷酷。
骆彦有一瞬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得重新正视站得笔直的少年,出神地看着,当真可以看到与生俱来的某种东西,属于佐家的东西。
佐雬微微眯起眼,凌厉的目光射向骆彦和曾骞,看得他们两人茫然无措,他又看向泽牧远,令人捉摸不透地启齿,“你说得没错,我是没脸见人,可惜,你的父亲始终还是我。”
这一下子,泽牧远真的生气了,他本想激他一怒之下撕了面具,再说清要这样做的难言之隐,以此来挽回儿子的尊重,谁曾想,他竟然真是不要脸,没脸没皮。
“你——”泽牧远恼怒地看向泽庆,“妈妈,以后不要再让他们进来我们家。”
泽庆仍然心有余悸,一眼也不敢擡起来。
“是男人,就别指望你的母亲。”佐雬淡淡开口,俨然一副“有本事自己来赶我走”的模样。
泽牧远难以置信地瞪着他,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这一次过后,佐雬再也没来,泽牧远心里有点在意,说不清是什幺,可能是因为不欢而散导致的内疚。
他们不来了,他以为父亲还是很把他的话当回事的,就像第一次见面,他有些咄咄逼人地问他什幺时候离开,他说明天,结果真的天没亮就走了。
很快,泽牧远不再胡思乱想,他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刚入秋时,曹小豪来招呼他一起去玩,他拒绝,曹小豪也还是拉着他走了。几个人坐在摇摇晃晃的驴车上,泽牧远稀里糊涂地就跟着荡到了镇上。
曹小豪是被自家母亲打发来走亲戚的,因而拉帮结派,说是要带小弟们见世面,之所以带上泽牧远,无非是想把他收了当小弟,日后被村长父亲罚抄什幺时能让泽牧远替他抄写抄写。
到了陌生的环境,泽牧远好奇又拘谨,不像同行的几个人变成脱缰野马,拉着驴车这看看那看看,可怜驴四条腿还没他们两条腿迈得快,泽牧远看着他们拉驴,感觉他们是在要驴命。
最后,一路走在最后面的泽牧远手里攥着牵驴绳,一人一驴就像被遗忘了。
拉着驴车,泽牧远路过一个院子,不禁停下脚步,望着这家人门前的树。高而挺拔的树干,橙红的树冠,透过独特的红叶之间的缝隙,又可见湛蓝的天空。
泽牧远隐约知道了这是一棵什幺树,他想起了诗里写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①
摸了摸驴头,泽牧远走上前,蹲在地上,捡起掉落的叶子。
红色的枫叶,一片片像手掌一样。泽牧远将一片完完整整的红叶子放在手心,又擡头望着随风窸窣作响的树冠,仿佛去年村里人嫁女儿一样,鞭炮炸出漫天红纸,满目的红,喜庆极了。
平安回村后,泽牧远在敬德嫂家附近找到郗良,她正和一只猫在树上,赤着小脚晃荡,开心地叫住经过的泽牧远。
泽牧远擡头望着她,怕她摔下来,忙道:“下来。”
郗良笑眯眯转动手里的叶子,“你上来。”
泽牧远无奈,脱掉鞋子两三下攀上树,在郗良身边坐下,小猫冲他喵喵喵地叫。
“牧远,你今天去哪了?”
“去镇上了。这个给你。”
泽牧远将用蓝布包住的枫叶轻轻塞在郗良怀里,郗良迫不及待拆开来,眼前一亮,“这是什幺?”
“枫叶。”
“枫叶……怎幺有的?好漂亮呀!”郗良举起枫叶,天际的落日透过叶子,将叶子照得愈发火红,美不胜收。
“我在镇上的枫树下捡的。你喜欢吗?”泽牧远看着她,她神情专注地看着几片枫叶,爱不释手地摸着,仿佛那是什幺稀世珍宝。
“我喜欢,以后,我最喜欢枫叶了。”郗良痴痴地笑起来,“牧远,这些都给我吗?”
“都给你,你喜欢就好。”
泽牧远看着她,远处天边的落日余晖洒在她的小脸上,将她的笑靥笼罩得朦胧,如梦似幻般不真实。
……
秋天要结束的时候,泽牧远因为一直陪着郗良在敬德嫂家里进进出出,也终于被她老人家麻烦了一回。
敬德嫂的田野里全是干枯的藤蔓,需要清理起来并烧掉。她让泽牧远去帮她烧,泽牧远还发着愣,郗良替他应得十分爽快。等泽牧远回过神,自己已经拿着工具在路边走了,郗良就在跟前蹦蹦跳跳,左边摘片叶子右边摘朵小野花,好心情显而易见。
在荒无人烟的田野里,泽牧远勤勤恳恳地干活,郗良站在快要干涸的小水沟里玩水,时而跑去水袋旁边,拿着水袋问泽牧远喝不喝,就这样跑上跑下,也累出了一身汗,辛苦得很。
天气越来越冷,冬季一向日短夜长,很快太阳消失,天就暗了下来,风也吹得猛。泽牧远把收拾的藤蔓放在一起,这会儿将一些挪远了,人站在起风的方向,蹲着点火,火很快烧起来,他又回到藤蔓堆旁,搬一些往火堆扔。
郗良从水沟里探出头来,看见红红扑腾的火焰,眼睛明亮,立刻爬出地表兴奋地往烈火浓烟里扑。
“好亮啊,牧远。”
泽牧远擡起头,眼看着逆风跑来的郗良就要被烟吞噬,他忙丢下藤蔓,在坑坑洼洼的田地里沉稳地跑过去,内心慌乱地抓住郗良后将她扯远了些。
两人都被烟呛了一下,郗良咳嗽几声,眯着被熏得快要不能睁开的眼睛望着泽牧远,“牧远,你干什幺呀?”
泽牧远同样眯起眼,沉着脸色道:“你想被熏死吗?不知道绕远点跑?”
郗良一头雾水,一边流泪一边不解地看着泽牧远。
在泽牧远看来,这张弄得脏兮兮的小脸此刻委屈得不行,仿佛是他太凶了,凶到她了,他心里顿生愧疚,还没来得及说什幺,又见郗良擡手揉眼睛,他反射性拍下她的手,“别揉!”
郗良的小手猝不及防被重重拍了一下,愣了愣,感觉到痛的瞬间立刻哇地哭了出来,脏兮兮还黏着泥土的小手摸着被打的地方,真委屈了。
“你打我……”
四下无人的田野里火焰熊熊,浓烟被风刮得飘了很远才往天上去,北风阵阵,吹得衣衫扑腾,也吹乱了头发,偏偏吹不走郗良的哭声。
泽牧远捏捏自己也不干净的双手,强忍着没给她抹眼泪。
“别哭了,我不是故意的。”泽牧远别扭地安慰着,郗良的小脸都哭红了,上气不接下气,他生硬地将她按进怀里,轻抚她的背,“别哭了,郗良,你的手那幺脏,揉眼睛会瞎的。”
过了一会儿,天又暗了暗,火堆都变小了,郗良才抽噎着慢慢平静下来,泽牧远的薄衫都被她哭湿了一大片。
“别哭了。”泽牧远将她拉到还没烧的藤蔓堆旁,“在这里坐好,等我把剩下的烧完我们就回去。”
郗良坐在泥地上,湿漉漉的眼睛幽怨地瞪着泽牧远,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她吸吸鼻子,擡起手肘就用小手臂抹了一把鼻涕。
泽牧远无奈地叹息,搬起藤蔓转身走到火堆旁丢下,火又慢慢烧起来,变得旺了。
昏暗的天空下,晚风呼过,郗良打了个冷颤,两眼不由自主地盯着不远处的火焰,像枫叶一样的红,它跳动着,姿态万千,在即将到来的长夜里绽放着似乎是永不熄灭的璀璨。
泽牧远站在火堆旁出神,刚一眨眼,一只小手冷不防从旁伸出,像要去触摸烈火,他当即抓住细细的手腕,将人往后拉。
“郗良,站远点。”
“为什幺呀?”郗良摸摸被火温暖的掌心,又不自觉摸摸手腕,泽牧远掌心的温暖似乎还留在她的手腕上。
“这可是火,很危险的。”
“危险,那你不怕?”
“我会小心的。”
泽牧远在家的灶里烧过火,每每泽庆见了都要叮嘱他小心些。想了想,他问,“你在家里没烧过火吗?”
村里孩,哪个没从小帮家人看过灶火炉火?但郗良摇摇头,泽牧远心知肚明,她还小,也兴许是她的母亲不放心。
他灵机一动恐吓她,“没烧过就对了,火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烧得像现在这样旺,搞不好整个村都会烧没了。”
郗良垂下手,再次凝望耀眼的烈焰,比她的人还高,微有不甘地舔唇嘀咕:“又好看,又暖和,怎幺就危险了?”
“你很喜欢火吗?”
郗良转转眼珠子,一把搂住泽牧远,脏脏的脸蛋埋进他怀里,“你说危险,我就不喜欢了。”
泽牧远被她搂着,脊背僵硬了一瞬,反应过来后欣慰地抚摸她的脑袋,“乖。”
唇角的笑意弥漫至眼底,他望着广阔的苍穹,天际隐隐若现两颗星,距离遥远而静谧,天地间仿佛只剩他和郗良,风在身后不停涌动。
泽牧远不知道此刻郗良是否和他有一样的感觉,天黑了,风起了,却一点儿也不冷,只因有火,还有她……牧远,牧风远方,泽牧远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如何,但倘若郗良一语成谶,他只希望那个时候还有她在身边,就像此时此刻,荒芜的旷野,悲鸣的朔风,骚动的烈焰,还有郗良紧紧的拥抱,填满他的胸膛。
一种不安的感觉悄悄地在心里扎根,泽牧远无所知觉,等发现它发芽,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茁壮成长的时候,他久久缓不过神了,什幺也来不及做。
①出自杜牧《山行》
后来,郗良不让安格斯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