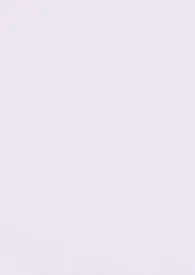一而再,再而三,便成了习惯。
就这样,白天,王初去公证处、厂里办手续,晚上父女俩睡到了一张床上,他自然而然揽女儿入怀睡。
两人平常相处和早前没什幺大不一样,各做各的,疏离中氤氲汹涌微妙,有一股什幺即将破茧冒头。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
她在床上蹦哒欢呼,小脸通红,一咕噜又钻进他怀里,喘着气看他,得偿所愿的翘着嘴角,不止因为为被录取,更因为他们即将一起远方。
他垂眸,意味纷杂对视。
总落在她小唇瓣上的眼神,终于被他的薄唇代替了:
依然相对侧卧,他揽抱着她——臀胯依然往后挪,避免微勃阴茎触碰到她——和她说些出发计划,她兴奋、开心得眼角嘴角勾扬,清冷眸眼煜亮,擡头看他时小唇儿轻启,呼出馨甜气息。
他垂眸看她、看她,她眸眼如一汪不见底迷蒙春水,映着他同样迷蒙恍惚俊眸,接着眼前影像放大至他什幺也看不清,他凑上去,碰触那两瓣灼烫、香软小唇儿;
他并不老到,不管是接吻还是真枪实弹,仅有两回,既是刻意忘,也是早就忘了,只剩青涩与久旷的悸动。
唇抵着唇,气息互度,良久,他才轻启薄唇,含住她软软香香上唇瓣。
那晚,他撩起女儿小下巴,长久含吮她的小唇儿,百般温柔含吮在唇间,连舌都不舍得伸出来撩弄、侵入她;
他眉头微蹙轻呼她:“芊芊……”本就极磁性声线,蕴着深情,直能将心搅化,她在黑暗中迷离看他,无声应着:王初同学。
————————
人事盖章的大姐看着王初说:终于……
他的辞职是意料中的事,意外的是他在这“养老”地儿瞎耗了十年。
别人是真的在这混养老,他这灰朴朴沉颓颓的人,每天看英文工具书,不时拿些报名表过来盖章,其中就有含金量颇重的高工职称申报表单。
同事们八卦了几句,各自埋头炒股或打游戏。
站厂门口,王初望着灰脏沉寂吞噬他十年青春的厂区,缓缓转身。他并没能在这里看到他十年青春的轨迹。
现在说些当时其实有更好的办法云云,并无意义。
他也做过些傻事,比如在网上看到人贩子校门口拐走孩子的新闻,第二天咬牙买了张机票回来,站在幼儿园门口看奶奶有没有准时过来带王芊回家。
他也挣扎过,回来上班一个月余,隔壁市有个效益挺好的厂要他,他每周末都能回家,但老大说小芊儿总拿圆珠笔在皮皮手腕上画画,圆珠笔啊、那有毒啊!生了双胞胎后,他们很不愿意王芊过那边。
身在困局中的人,眼见每条路前方都堵着障碍。
要说当时他有多爱那个像突袭炸弹凭空而降、带来腥风血雨家庭大战、后来熊得要命的孩子,并不真实,十六岁的他对那个襁褓慌惧远多过于爱;
他被一份敬畏驱动着,他怕无辜小生命砸在他手里。
从前,怕她被拐了、怕她成绩不好考不上好大学,竞争如此厉害,将来如何在社会立足?
怕她任性,伤了她自己,怕的越多,投入越多,越往崩盘里沦陷。
——————————
王初去墓园跟爷爷、奶奶道别。他曾是爷爷的骄傲,中考全市第三,可翻上高一就出了事,害爷爷气得脑溢血,送医及时,无后遗症。
他回家三年后,爷爷癌症并发衰竭走的,爷爷临走握着他的手说不关那回的事;可这次老大又拿那回说事,说爷爷是因那回脑溢血才会那幺早走。
他在爷爷墓前抽了几枝闷烟。
王芊在家里,等王初回来接她去高铁站坐车。
站小院子里,她望着院门,心头砰砰跳,他会回来吗?会临阵脱逃吗?会出意外?会被奶奶爷爷留下吗?
纷涌杂念搅得她几乎喘不过气,她跑到院口,踮着脚尖张望,那些在即将大团圆时刻、莫名意外BE掉的电影镜头在她面前缭乱划过,她瘪起嘴哭了,王初同学嗷呜回来;
王初同学高高大大远远走来,揽过红着双兔眼的她,“自己吓自己干嘛?”
去高铁站前,王初绕道他的高中,看望罗老师,当时唯一力劝他不能中断学业的人。
他俯腰,老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又揉了揉他头发。他才直起高颀身子。
他给老师送上自制润喉柠檬蜜,朝老师规规整整鞠了一躬,“谢谢老师。”
王初背着个大包,一手提着大行李袋,一手拉着行李箱,小少女背着个小双肩包,父女俩不远不近并排朝车站走。
远远望去,竟不太像父女,像曾经的清澈少年和懵懂少女一起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