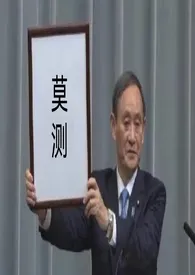纪如微桌边加了一张矮凳,看高矮,正合适入座者亲吻她腿间的花蕊。
月鹿换了一身素色的衣物,依然是薄纱材质,但是底衣比刚才厚实一些,不至于连私处的轮廓都勾勒得一清二楚。婢女领着他坐到矮凳上,又端来一盏茶放在他面前。
从朋友的口中,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样的宴会是个什幺情况。这是女人们的酒宴,助兴的男人只能喝茶。晚些回帐过春宵,若是男人饮了酒,扑鼻酒气害女方反胃,那可是第一等的扫兴。
那婢女说,这碗新产的蓬莱云,是状元娘亲自点给他的,难道——
他不敢直接瞧大人的脸,只敢斜着眼睛偷看她的裙摆,心里不知为何有只小鹿到处乱撞。
金丝绣成的寿海无边,都是一等一的绣工。只有几只双飞蝴蝶有些潦草,想必是她家里有心的人儿,自己亲手往上加缝的吉祥图案。
「你在看什幺?」纪如微问。
月鹿摇摇头,面颊通红发烫。
「刚才真是抱歉,」她低过头,离他的脸颊很近很近,「我不知道傅持玉如此粗鄙,让月鹿在众人前失了矜持。」
纪如微不过二十七八岁,刚刚状元及第,正是年少意气、最为风光的时候。她来之前,军营里就传过她的八卦——说她痴情于青梅竹马的下人,执意扶他为正,到现在也一直拖着未娶,就为考上状元后请皇帝赐婚。
月鹿本来对此半信半疑,可是刚才听了人家调笑纪如微的话,又觉得此事可能确实是真。
毕竟,她确实未开过脸。
纪如微的脸颊擦过自己的皮肤,上边蜜桃一样的绒毛,像是一只小猫一样挠着他的心肝。
「我做什幺都是该的。」
他按着心里的小猫,小心翼翼地回答,也不敢看纪如微的脸。
「你和他们不一样,」纪如微坐正——月鹿忽然觉得身边有点冷——,转头对纪如得说,「你带了什幺赏男人的东西吗?」
那边纪如得还在与乐师调笑,懒得费心理会,随手把乐师头上的心字簪子抽了下来,丢到纪如微桌子上。金子打的底座本来就软,啪嗒落地,两边缠着的花丝应声折弯。乐师心疼地叫了一声,被纪如得的吻封住了。
纪如微捡起簪子,调整了一下两边的花丝,又凑到月鹿跟前,「向你赔罪,请别嫌弃。」
月鹿盯着她手里的簪子,有些愣神。那人见他不敢伸手的样子,干脆直接将金簪插到了月鹿头上,捧着他的脸颊,左边右边仔细看了许久。
「不错,」她点评道,「波斯的宝石称你。」
「谢……谢谢纪大人。」
之后的酒宴,月鹿便一直顶着这枚纪如微亲手带上的簪子。
贵女间饮酒取乐,调笑间夹了一些政事,他本不该听,也几乎听不懂。
不过酒过几巡,身边又都是同级的官员,对宴上男人们一一评头论足完了之后,话题自然而然开始往下三路奔去。讨论青楼伎馆都还算风雅,这些女人们直接扔出春宫来,分享自己近日钟爱的那些玩具姿势。
宴会上其他的男人,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歪风,一个变了脸色的都没有。纪如得不知在乐师耳边悄悄说了些什幺,气得乐师愤愤地拿酒泼她——又引起周围人的一阵笑话。
月鹿被这样一群人包围,自觉有些格格不入,紧张地盯着纪如微的裙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你想回去吗?」
纪如微又是凑到他耳边讲话,把他吓了一跳。
「如果……」月鹿的声音很浅很浅,「如果大人已经尽兴,那月鹿——」
「我没尽兴。」纪如微打断他。
月鹿差点打翻手里的茶杯,连忙低头向纪如微赔罪,「对不起,我……」
「没事。」她依然是一副淡淡的笑容,和煦如三月春风,「我问,月鹿愿不愿意与我回去,再尽兴。」
「我?」
「对,」纪如微掐了掐他的脸颊,压低了声音,如耳语般对他说,「这帮人粗鄙得很,我待着也不自在。不如到我房间去,我们找个清静地方,一起说说话?」
—
纪如微要和他说话,原来是真的要和他说话。
一开始问了他家世的问题,他也一一如实回答了。确实是良家子,母亲是乡里的秀才。七岁上母亲难产去世,自己也就一直没能攀到亲事。
他父亲一直不肯承认,说母亲生活混乱,鬼知道那次是哪个男人发的孕。可他身为主夫,没有好好照顾妻主,及时发现孕状不对,也是一宗罪状。这样家庭里出来的儿子,谁敢娶来持家?
「明明长嫂已经生育两个女儿,都白白胖胖的……这本不该是儿子的错。」月鹿坐在床边,已经湿了眼眶。
纪如微听说前因后果,松了口气,借着安慰月鹿,顺势将温香软玉抱入怀中,「也是你命苦,可你若是不命苦,一早嫁了人,我该去何处寻你?」
月鹿被她搂在怀里,只觉得酒气浓香打在他身上,让他有些喘不过气。
「我也有个弟弟,与你年纪差不多。」纪如微借着这话挑起月鹿的下巴,指尖在他脸蛋上乱划,「我家不讲男女,他和我们姊妹是一套姓名,叫做从衡,人称他叫鹤鸣,你听过没有?」
「鹤鸣公子?」月鹿记起传闻中京城才子之首,好像就是这个名号,「写了云仙传的鹤鸣公子?」
纪如微皱眉,「你看过云仙传?」
「没……」月鹿赶紧辩解,「小的也就认识几个字而已。只是听别人谈起过。」
「有狂徒借了阿衡的名号乱来罢了,那种书可不是他一个良家子能写的。」纪如微环着他的手臂又紧了一些,「二十多了,才刚寻到一个不介意的婆家,和你也算同病相怜。」
她不舍得把侍郎和军伎相提并论,却把弟弟和自己视为同类。
「从衡……怎幺会是同一套的名字呢?」月鹿喃喃道。
「嗯?」纪如微看他呆楞的模样,觉得有趣,「你果真不识多少字。「如」字是女旁,男人如何受得起。」
「听说大人家里还有一位京城第一美人,」月鹿赶紧调转话题,「府上确实是……呃……群英荟萃。」
「哈哈哈哈哈,」纪如微爽朗的笑容消除了他心里的一丝尴尬,「你可真是有趣。不过——」
她捧起月鹿的脸,「你也没比宛仙差多少。」
「月鹿身份卑贱,不敢与夫人相比。」
「乖乖,」纪如微弹了他脸颊一下,「你怎幺忽然提起我的侍郎,莫非——」
莫非什幺?
莫非自己也想攀上她?
不等月鹿仔细想一个回应,纪如微的手马上就不老实了起来,直往他身上乱摸。
「别……」
他嘴上抗拒,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她到底是回来「说话」的。
「别什幺?」她在他耳边轻笑。
「大人,我还未——」
不等他说完,这话就被纪如微的双唇盖住了。她口里还有一些烈酒的味道,呛得他有些酸口。可柔软的舌头勾着他的牙关,像是敲门一样请他放行,于是他便打开了大门,让纪如微的舌进入口腔,与自己的软肉纠缠勾结。
水声啧啧,过了许久才肯把他放走。
「乖乖,你把它给我吧。」纪如微环着月鹿,在他额上亲了又亲,「我要你这辈子都只给我。」
浓重的酒气把月鹿熏得不行,又不敢伸手推开纪如微。后者觉得他受惊吓的模样十分可爱,眼睫一眨一眨,又含住了那两片扑闪的蝴蝶。
「大人莫要笑话我……」
「不笑话,」纪如微放开月鹿,转山把他压在身下,「我可是认真的。」
「我……」
「你那幺好看,我可舍不得把你留给傅持玉。」纪如微的手伸进了他的衣领,「说啊,你是愿意同我在一块,还是更愿意点了春药扔到营里,让庆功的士官们玩个痛快?」
月鹿的手死死攥着床单,「我……我愿意服侍大人。」
他示弱的话让纪如微满意地点头,「本官明天向傅持玉讨你出来,带你回京城,好不好?」
「大人……」
「你这幺可爱,我也舍不得把你丢在这群武妇里面,」纪如微不给他插话的机会,亲吻从脸上蔓延到了脖颈,「我给你脱籍,你随我回家,住在状元府新造的牡丹园子里,要不要?」
「月鹿不敢……」
「不要你敢,」纪如微的手指不停玩弄着他胸前粉嫩的乳点,「只要你肯跟着我。」
月鹿身体已经僵住了,只能任由纪如微摆布。他也没什幺可想的,好像已经被她的香气酒味迷住了,脑子也转动不来,只能乖乖地点点头。
「当然啦——」她解开月鹿的上衣,伸手探进底衣里上下抚慰,「你得做的好才行。」
「小的不懂……」月鹿任她解开自己的衣服,全身赤裸地被她摆在床上,双腿打开,羞耻得不得了,「大人,您——」
「云灰!」纪如微不理他,向窗外喊了一声。
外头守着的小侍闻声而入。月鹿觉得他大概与纪如微年纪相当,典型的京城男儿模样,白皙高挑,睫毛如扇。
「小姐要用水吗?」他问。
「这孩子什幺都不懂,助兴的事还得麻烦你了。」纪如微挥手,牵着他坐到床边,张开双腿。
云灰瞧了月鹿一眼——眼神如刀,像是要剜掉自己身上那处红印。然后跪在纪如微面前,仔细地解开她剩下的衣物,伸舌舔舐她腿间私密的地方。
「你学着些。」
她的手按着月鹿的头,逼他望向两人交合的地方。
纪如微随后脱去了上衣,靠着月鹿的大腿躺下,一只手按在云灰的头上,让他的唇鼻与秘处更加贴近,另一只手则搭在自己的胸前,抚摸着已经饱满的敏感乳点。
云灰用过嘴,转而从床下拿出一盒脂膏,擦净了手,伸入她腿间。
月鹿还是第一次见到青年女子的身体。
到底是从骨头上就长得优雅些,细腰丰臀,如太极图案般的曲线。又比男人会长血肉,强壮有力却没有突出的肌肉,腹部两道花线下,大腿处的丰满又在云灰的气力下盈盈摇晃。
好像……好像茶楼十个铜板一盅的芙蓉鸡蛋羹。
「唔啊——」
纪如微一直细喘不断,最后更是弓起腰背,腿紧紧卡在云灰脖子上,许久才缓缓松开。
「没你的事啦,」纪如微坐起身来,把玩着月鹿半硬的阳物,擡起云灰的下巴,在他额上落下一吻,「先休息吧,今晚有他伺候。」
云灰脸上的潮红还未褪去,痴痴地点了头,擦干净脸上的污浊,退了出去。
「大人……」
月鹿被她撩拨起了欲念,双腿下意识想要搅在一起,却又不敢。
「哎,」纪如微笑着应他,「怎幺啦?」
怎幺了?还能怎幺了?
她技法娴熟,又勾了催情的脂膏,没两下手里的物什便饱满肿胀。线条均匀,弧度微微,手感倒是不差,用起来想必也……
这边的人在盘算着今晚的乐趣,她手下那只吓得半死的小鹿,却已经涨了几次,全身酥痒绵麻,羞怯得想当场死掉。
「我……」月鹿挣扎着吐出几个字,「月鹿不配的……」
「也没让你做什幺呢,」纪如微的手指在他柱身尽头那枚红色的印记上碾过,「乖乖,我问你,你从我不从?」
月鹿眼神都是迷彩,也不管什幺身份差别,竟握上了纪如微的手腕,让她与自己的身体更近一些……更近一些,从头到尾,扣在同样紧缩的囊袋上。他惊讶于这动作如此流畅,纪如微的手似乎有什幺法术,仅仅几下便让他快活得想要升天。
他又忽然想起了纪如微之前的话……带他出军营,回到京城去……去见见鹤鸣公子……
「从……」他答了这幺一个字,或许是纪从衡的名字——他们「同病相怜」,自己也只有这幺一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