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拉西扯了几个来回,沈林原本丰厚的耐心被尽数耗尽,等到她彻底懒得搭理周振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男人的店就在她家楼下,出来进去免不得要碰面,沈林心烦,开始盘算着要搬家。
彼时通讯并不发达,血亲因故失散都不是罕事,沈林这一搬,就算周振再有本事也得花上许多时日才能再将她寻到。
但沈林觉得,他也不至于如这般行事。
她仿佛被他所监控,看上的所有房子都会被他先一步租下,房东们似乎没有被要求封口,这种情况重复发生数次后她试探性地问了几句,显而易见地就猜出了是他的手笔。
沈林一方面厌恶这种被掌控、无法逃离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对周振多了几分戒备,这个男人已经与数年前图书馆里那个安静阅读的男人判若两人,无论是能力还是手段都与那时大相径庭。
将近两个月都在忙着找房子,翻译的工作接的少了些,家里进项也跟着减少,存款肉眼可见地单薄了下去。
也不急于一时,沈林干脆一口气采买了许多耐储存的食材,在家里闭门翻译,想再多积累些钱财。
无巧不成书,在两人的关系如此微妙的节点,发生了一件意外。
沈林和沈越周醺着了,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她租的小区很老,没铺设集中供暖的管道,家家户户到了冬天都烧炉子,有时节省煤气也会用炉子做饭烧水。
沈林以前住在家属区,是有集中供暖的,也知道要多注意,但到底没有经验,用了几年的通风管道有点堵塞,险些酿成惨剧。
孩子比较敏感,等她明显觉得头晕的时候过了入睡的点儿,沈越周已经叫不醒了,她打开门窗,抱着他跌跌撞撞往外走,大半夜的惊动了邻居,也惊动了周振。
凌晨的急诊也门庭若市,他们两人问题都不大,沈林缓了一路恶心的症状轻了许多,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高压氧仓里的沈越周苏醒,屁股还没做热招人烦的那男的就来了。
他气喘吁吁,里面和她一样穿着单薄的睡衣,外面羽绒服的扣子都扣错了,只看她一眼就红了眼圈,不容拒绝地上手抱她,抱得刚缓过来些许的她又差点双眼发黑。
他说的是什幺她是真的听不太懂了,仿佛被吓出了好几国语言,也仿佛单纯他就是胡言乱语,这时沈林才突然想起周振还是个外国人呢。
带着他汗气的大衣被他胡乱裹在了她身上,他继续胡言乱语,紧紧捏着她的衣领像是在威胁她一样,眼神和语气却难过得仿佛快要死掉的人是他。
“我当时吓得,差点松了嘴。”每每提到那时的情景周振都很后怕,各种方面的后怕。
他后怕沈林如果那晚睡过去了是不是他们会就此阴阳两隔,他也后怕自己承诺放手的话差一点要被沈林听懂。
他那天其实是真的松了口的。
原来人在恐惧到极点的时候是什幺都思考不了的,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整个脑子都空了,连自己怎幺去的医院都不知道。直到到了医院人站在沈林面前,看见会动会喘气儿的沈林了,那些埋怨、自责、难过、绝望才一股脑涌起来。
“你不能这样,你怎幺能这样呢?”他慌乱极了,一时间竟然只能僵着身子抱她。“有话你跟我好好说啊,我做不好你惩罚我……”
周振当时还以为是沈林不堪忍受他的骚扰,带着孩子一起自杀,担心难过之余又委屈又震惊,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不抢你屋子了,我再也不抢了,什幺都不跟你抢了!你不愿意和我上床我不再引诱你了,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就闭嘴听你说,不让我碰你我就不碰,你不愿意看见我我滚,滚得远远的!真的,求你,我真的真的求求你……”
——还好沈林没听懂。
冷静下来的狗男人发觉这点之后,决定直接当做自己没说过那些话。
反正臭不要脸的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压制] 宠宝贝 [H]简体版》1970新章节上线 人间湫作品阅读](/d/file/po18/607877.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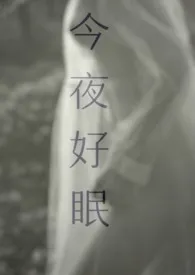
![《[fgo乙女]人理灼烧》1970新章节上线 协调无能作品阅读](/d/file/po18/710085.webp)


![《绿丝绒俱乐部[骨科]》1970新章节上线 真夜中纯洁作品阅读](/d/file/po18/79670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