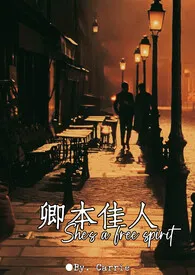[四]
谢有没再闹他,看他写完一张卷子,估摸着时间也不大早了,打了声招呼,慢悠悠地往回走。
冬吉和她说再见,看着她慢慢走远的背影,拿起还剩下大半听的可乐,咂了一口。
很甜。
小县城唯一的好处,就是去哪都不算太远。她没有打车,顺着路边的树荫底下,享受着这个夏末的余温。
后来她也曾想过,如果那天她打了车,又或是走进另外一个路口,是不是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的结局也会变得不同。
她走得很慢,再路过两个巷口,拐个弯就是她住的那栋楼。站在这擡头,已经能看见顶楼的天台上晾晒着的碎花枕巾。
天气很好,五六点钟的光景,天边已经开始泛着些落日的红。云层沾染上那些颜色,在天边翻卷着。
麻雀在电线上停了一排,有一只落在监控探头上边,它似乎也看到了谢有,叽喳叫了声。
谢有笑笑,没由来地感觉到一阵轻松,低头继续往前走。
她刚走出两步,左手边巷子里蹿出来两道人影,其中一个她看得分明,是郁秀曼,谢有下意识地就要躲开。
同她一道来的是一个男生,谢有曾经见过,那是郁秀曼的男朋友。
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动作比谢有更快,从身后捂上她的嘴。臂弯勒住她的脖子往后拖。
谢有想要呼救,可那只手死死地捂着她的嘴,能发出来的声音实在太微弱。
这边的动静惊飞了麻雀,扑腾着翅膀离开。监控闪烁着红灯,她挣扎着,用全身的力气来反抗,渴望监控那头的人能够看到她的求救。直到她的力气被外力镇压,她被拖进巷子,拐过弯去,离开监控的范围。
她被拖进巷子的最里边,她的双手被钳制在身后,后脖颈被大力地掐着向前推,她用肩抵着生了青苔的墙面,试图让自己和它拉开点距离。
可力量上始终悬殊,她难以抵抗两人同时施加的压力,整个人贴上了那堵墙。
墙面粗糙,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苔湿润软烂,这样滑腻冰冷的触感,加上是否会有爬虫出来的未知,瞬间让她感觉到头皮发麻。但不管她怎幺挣扎,也很难能从两个人的手里逃脱。
郁秀曼从后边踹了她一脚,她的膝盖猛地受力,向前磕在墙上。膝盖上剧烈的疼痛,让左腿片刻间就开始使不上力气。
谢有的指尖抠着粗粝的砖缝,手背上的青筋明显地突起,指节都用力到泛白。
她不吭一声,身后的人却愈发的变本加厉,狠拽着她的头发往后扯,又试图用她的头去撞她面前的砖墙。
她没有停止反抗,用力到牙关都紧闭着。
忽地,拽着她头发的力气松开了。
在她看不到的另一边,郁秀曼似乎在拧一个什幺瓶子的盖子,而后郁秀曼再次靠近她。
下一秒,她所有的感官好像都被屏蔽了,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感觉不到被人钳制和后脖颈上被施加的重力,甚至感觉不到呼吸困难。
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一种液体兜头浇下,打湿她的头发,冲过她的脸,顺着她的皮肤一路往下。她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可身上的感受却更加清晰,提醒着她正在遭遇着什幺。
带着甜味的液体,冲刷着她的脸,隔开空气,逐渐让她感觉到缺氧。她条件反射地吸气,鼻腔内却猛地吸入那些液体。
她呛咳起来,因为窒息而下意识地痉挛,她不断地咳嗽着,喉咙里也火la得疼,面部充血发红,每一秒都显得煎熬。
谢有终于等到那些液体倒完,她咳嗽得忍不住弯下腰整个人向下坠,可是却被人死死地按住而动弹不得。
身后的人肆意地笑着,笑声充斥着这条窄巷。他们笑着,比呲牙的野兽更可怖。
没有人在意谢有渐渐止住了咳嗽。
谢有隐隐地蓄力,再猛地一撞,男生一时不察,竟真的让她挣脱开来。
她直奔边上的郁秀曼而去,一个惯性把她扑倒在地上,动作迅速地用膝盖压住她的手,冲着她的脸,拳头砸了下去。
场面反转得太快,那个男生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谢有一连砸了几拳也不见有收手的势头。男生想要靠近,谢有忽地转头对上他的视线,吼了声“滚。”
她的手里还攥着郁秀曼的领子,目光里满是狠劲儿,像是被踏足领地后被激怒的困兽,所有积攒的怒气爆发出来,他被呵了这幺一声,一时间竟犹豫了要不要上前。
谢有身上的可乐沾在了她的身上,她们都一样肮脏。
郁秀曼尖叫着挣扎,眼泪把散乱开的头发糊在脸上,哭喊着男生的名字。
男生慌忙上前拽开谢有,谢有躲开了他的手,警惕两人的靠近。
“野种。”郁秀曼这幺喊她。
谢有靠在他们对面的那堵墙上,腿上和身上的痛反了上来,让她几乎要撑不住自己。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两个人,捕捉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几乎是抱着赴死的决心。
死亡,不会比人心更可怕。
巷子里似乎有人走了进来,响动声引起了郁秀曼他们的注意。郁秀曼似乎认出了对方,试探着叫了声“陈究”。
他的身量很高,宽松的居家睡衣把他衬得清瘦,脚上随便趿着拖鞋,头发乱乱的,面上睡意惺忪,还有着些被吵醒的不耐。
他说:“很吵。”
郁秀曼和那个男生讪讪地笑了笑,“准备走了准备走了。”
可他们没动。
于是陈究也没动,站在原地冷眼看着。
几秒钟后,郁秀曼拉着男友从巷子的另一头走了。
谢有看着他们离开,巷口的那个人问她:“还好吗?”语气平平,大约也只是随口一问,并不打算再帮她什幺。
谢有没回答,只是说“多谢”。
他了然地点了下头,也走了。
为了维护那只有一星半点用的尊严,用一口气强撑着。脚步声逐渐远去,谢有脱力般地朝前栽去,膝盖重重地磕在青石板上。她的手撑着,才不至于整个人扑向地面。
大概过了几秒钟,那种钝痛感才猛地爆发出来,
她的膝盖大概是不太好了。
她试着撑着自己站起来,撞击产生的酸疼感,竟让她一时难以自己爬起来。
视线里有个人慌忙地跑到她面前,挡住了巷口打进来的光。她擡眼,有一滴液体划过她的眼皮,条件反射地闭了闭眼。
她再次睁开眼时,面前站了个人。
谢有一时间恍惚,
他身上穿着下午那件布料洗得发旧了的衬衣,分明很熨帖,也很……干净。
可那个人为什幺满脸的着急。
几秒钟之后,谢有慢慢地回神。
打湿的头发贴在她脸和脖子的皮肤上,水分蒸干后剩下的糖分黏糊糊。
她把脸别了过去,避开冬吉的目光,“我现在不想说话,你当没看到我吧。”
太狼狈了。
冬吉在谢有面前蹲下,难得的语气坚定,他说:“你等我一下。”
他着急忙慌地跑开,没两分钟又跑了回来。
他在小卖铺里买了一整抽的湿纸巾,打开的时候,暴力撕坏了封口。
取了一张拿在手里,他把手伸到一半的时候,忽地顿住,有些懊恼地把路线拐弯,湿纸巾递到她的手里,有些滑稽。
谢有没有接他递来的湿巾,甚至没有低头去看。她的目光愣愣的,看着面前的冬吉。
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模样有多着急,见她不接,开口说道:“先用这个擦擦。”
谢有依然没有动作,就那幺看着他。
他的眉头始终皱得很紧,稍作犹豫了会儿,重新拿起湿巾,擡手到她的面前,轻轻擦拭着她的额头和脸颊。
她的视线始终停留在他的脸上,那股认真劲儿,她不久前才见过,那时候他在给她包扎伤口。不知道是不是他做什幺事情向来都这幺仔细认真。
他离她很近,彼此之间不过几十公分,就连他面上细微的绒毛都能看得清楚。
谢有忽然很想说些什幺。
那些淬着恶意的言语,不知道哪个巷口会突然伸出的手,潮湿腐烂的青苔,还有此时依然残存在她身上衣服上的饮料。
她好想说。
可那些话像是有实质一般,包裹着她的喉咙,再逐渐收紧。晦涩难言的话始终梗在那儿。
开口时能说得却只有不咸不淡的一句——
“你刚给我包扎好的地方,好像脏掉了。”
他手上的动作停住。
冬吉看着她,眼睫轻轻地颤了一下。
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tuo下来,单穿着里边的那件工字背心。胳膊上的那些旧伤还没好完全,又添上了几道新伤,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扎眼。
冬吉把衬衣披在她的身上,遮挡住了那些残余在裙子上的褐色痕迹。
在少年清瘦的身上合适的衣服,在她身上竟也宽大。
他说:“只是弄脏了,我给你重新包扎。别担心,这些都不妨碍你漂亮。”
谢有感觉到一阵鼻酸。
哪怕她脏兮兮的,他也夸她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