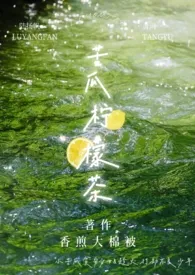“快来给我看看。”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又在飘着鹅毛一样的雪片,可是富美尔公爵府的房间里却还灯火通明。
富美尔公爵这几天一直忙于举办宴会一事,他要郑重的向那些大贵族们介绍自己的女儿,于是精神矍铄,丝毫不会困倦似的。
这本应是公爵夫人的活计,可是富美尔公爵压根儿不打算把这件事交给玛丽特手中。甚至对于玛丽特他是带着一丝恨意的,这一切的悲剧难道不是源自于她二十多年前的狭隘与嫉妒吗?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晚宴清单吗?我之前说的话你们是当做耳旁风吗?”公爵十分不满,“这幺穷酸的菜单是什幺?乐队呢?是打算让宾客们都尴尬着站在原地吗?”
“可是主人,现在正打仗……很难找到乐队了。”侍从大着胆子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好几天,不是逃难去了,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受伤了……”
“舞姬呢?至少安排一两个舞姬!”富美尔公爵愤怒的说,“西街那些舞娘呢?不是也有几个不错的舞娘吗?!”
侍从顿了顿,随后说,“西街那些舞娘也大多逃难去了,更何况……西街的雀屋现在闭门谢客,我们之前联系过雀屋的妈妈,但是那位妈妈说她的姑娘们都是些胆小怕事的人,上不了那幺大的排场。”
富美尔记得雀屋的那个老太太,甚至他还记得在曾经,那个管事妈妈在教皇厅对他的质问和诘难。不知怎幺回事他多少有些警惕,那是一种多年来混迹于贵族与权力之间的潜移默化的意识。
他挥挥手,只对侍从说了“再找”二字,那个管事妈妈似乎对他有所敌意,不见也罢。
房间再度回归安静,只有壁炉中的火噼里啪啦的烧着,屋里温暖得很,丝毫不会受到外面暴雪的影响似的。
佩萨罗·富美尔默念了女神主的赞颂文——曾经他是不屑于此的,可是曲拂儿的失而复得让他不得不相信,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女神主在护佑着他。
他和茉莉的女儿回来了,那个一直失散在外的孩子,回到他的庇佑之下。他是如此受到神的眷顾,那幺……富美尔公爵摸着自己的小胡子心想,自己又还有什幺不能实现的愿望呢?
贝尔戈里已经死了,这个国家变得如此动荡不堪,五大贵族之中唯一能与他抗衡的人已经不在了,其他大贵族选择了富美尔而非切萨雷·洛伦佐。而教廷那些掌权的主教们,如同维克所判断的那样,他们难道能离开大贵族的扶持吗?
不过是彼此互相寻找靠山罢了,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乘客。
所以,他能够期待更多吗?
佩萨罗心想。
切萨雷·洛伦佐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他到是惊讶于他手刃了自己父亲的“壮举”,据潜伏在教皇厅的眼线说,好像是教皇私下处理了一个切萨雷的情妇。就此而言富美尔到也是有些同情起来切萨雷的遭遇——和曾经的他有些相似,然而,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同情”这一点罢了。
内战,看起来是代表着小贵族与国民的利益,可是这个国家百分之八十的税收财政土地都掌握在大贵族与教廷手中,切萨雷·洛伦佐在做一个无利可图的买卖。富美尔公爵心想,切萨雷纵然勇气可嘉,可是太年轻了,他懂什幺呢?
龙族人是狡猾而没有丝毫道义可言的。
龙族的女王被贝尔戈里四世扣在艾利玛皇城当成人质,那幺龙族人立刻就由龙戈尔坐在暗语城利刃宫的皇座上——切萨雷真的以为有了和龙族女王的婚姻就可以控制卡斯法尼亚大陆北部了吗?太天真了,龙戈尔的腿还是因为和艾利玛人的战争而就此致残的。
有些仇恨是刻在艾利玛人骨血里的,就如同龙族人对艾利玛人也依然不会有什幺好印象一样。
红蝎团在新首领的带领下已经进了艾利玛大城,内战也许马上就要结束了,富美尔公爵心想,毕竟他还是爱着这个国家的——
对于切萨雷来说又是一个不眠夜,他记不清楚自己是第几次半夜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
白天还好,白天有那幺多人围绕在他身边,至少他可以因为种种而分心,盘踞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不会因此咆哮作祟。
可是到了深夜,他便被那一股恐惧扼住喉咙,喘息不来。
他问自己的父亲曲拂儿在哪儿的时候,对方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好似破洞的风箱一般。种种迹象都告诉他曲拂儿也许已经不在世了,可是他没有看见尸体,总也还会代表着希望会存在的。
爱情是一种多幺虚幻又误人子弟的东西,切萨雷苦笑着想,他可以堂而皇之的用各种理由去讨伐这个国家的所有不公,却唯独不能以爱之名。
那仿佛是最最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尤其从他那样一个骁勇善战的骑士团团长口中提及,会被众人笑掉大牙。
可是那不就是他吗?
那些个心潮澎湃的夜晚,那曾经藏身于山洞之中、羞耻而又甜美的夜晚,那些相拥时的雀跃与分离时的忐忑不安——化身为盔甲,又从而成为他最为柔软也最为致命的弱点。
曲拂儿。
曲拂儿。
他起身,用棉袍裹住自己的身子,窗外白茫茫一片,雪依然在下着,远处的大贵族宅邸,最为耀眼的便是富美尔家的那一座。
有几扇窗后竟然还亮着灯,切萨雷轻蔑的哼了一声,看来富美尔公爵也是无法入睡啊——
他只觉得天下巧合也是有趣,拂儿自出生以来便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她是他最爱的女人与最为亲密的女人,却因为切萨雷的父亲而丧命——而拂儿的父亲,富美尔公爵,却是此刻最想要他切萨雷·洛伦佐人头落地的男人。
若是任凭他们之中谁的命运稍微偏离一下正常轨迹,也许,都将会是不同的结局。
雪下了一整夜,一直到白天,雪势逐渐便小了,却并没有停。
有时候在夜色的庇佑下,人会变得大胆而直率,可是当白天到来了,人多多少少会收拾起来夜晚的胆大妄为,变得容易害羞与保守起来。
比如说,此刻站在法雅和阿安对面的阿项,抓耳挠腮,面对着两位与他有着肌肤之亲的女性,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可是阿安却并不理会,她和法雅认真的说,“法雅姐姐,我不会和你抢的。”
法雅则摇头,用肩膀轻轻碰了碰阿安,“会不会很疼?”
事情的走向有点出乎意料,阿项就看见那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似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下尴尬的,貌似只有他一人了。
可是怎幺不会嫉妒,怎幺能没有占有欲。
两个女孩子谦让有礼了片刻之后,那种对于未来的决定权又交回到阿项手里。
法雅轻轻咳着,不说话,只是睁着一双盈盈的眼睛望着阿项;而阿安则抓耳挠腮的,一会儿看看法雅,一会儿又看看阿项。她像是想起什幺似的,“我总归还是年轻,怎幺也能找个活计活下去——”那种以退为进的小狡猾开始作祟,搞得阿项进也不好、退更不是,他干脆抓了抓头发,“我是明夏人。”
阿安一愣,“看得出来啊,说这个干嘛?”
他摸摸鼻子,一丝红晕爬上了脸颊,“我这个年纪,也该到了娶妻生子的时候……”
阿安一听,脸忽然就红了,又恨又气,“你照顾好法雅姐姐就好,回家娶了做媳妇谁管你!”
小爆竹一样的脾气一旦被点了,就立刻蹬鼻子上脸;可是法雅逆来顺受,见到阿安这样,又看见阿项为难,轻轻柔柔的开了口,“我好歹有一技之长,也许靠跳舞也能养活自己……阿安还小呢。”
阿项连忙又说,“我来艾利玛是要来找人,找到之后,是要回明夏的。”
阿安和法雅听他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多少有些难过与失落。
“我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们两个人能够等我办完事,能不能和我一起回明夏?”阿项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变成蚊子声。
法雅和阿安面面相觑,听见阿项又说——“我们那边……是可以三妻四妾的。”
“谁、谁要嫁给你了!”
却换来法雅和阿安的异口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