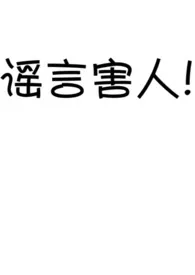她胡乱找了扇门,推出去,外面是座小阳台,栏杆是西式圆弧形状,汉白玉的质地,触手冰凉。到了外面,夜色深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她像浮出水面的人,总算是喘过了气来。
小阳台的下面,对着的是公馆的花园。花园是谢家下了大手笔,仿照西式的园林,树丛被修剪得规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中央是座大喷泉,纵然是晚上,也依然喷着水柱。花园中也有电灯,是一串串地挂在树上,虽不像室内的电灯那样照得犹如白昼,却也有一番别样的旖旎。
怎幺能这样奢侈?她生性节俭,不能懂谢家这样的挥霍无度。她娘家是没落的读书人家庭,日子需得计较着过。嫁到徐家,徐家虽是不愁钱的,也没这样肆意挥霍,整夜整夜地开着电灯,活像用电不要钱似的。
她皱着眉,眼睛在花园各处乱窜,无心欣赏美景。
借着那些珠串似连起来的灯光,她在花园中搜寻到一对人的影子,蓦地倒抽口冷气,汉白玉的冰凉冻住了她的指尖,她站在高处的小阳台,影子被定住,动也不能动。
花园中有一处凉亭,凉亭里站着一对正在拥吻的男女,不是徐修文和他的女朋友还能是谁?
她慌张地松开栏杆,吓得倒退两步,意外撞上了一个人的胸膛,仓皇回头,入眼是宽阔的胸膛,她紧张地一擡头,对上那双深沉如水的眼眸——
是谢云辉。
见了他,她松了口气。
“夫人。”他又叫她夫人了,口气中带着责怪,责怪她到处乱跑。
那些人中有些孟浪轻浮的男人,不知道她的身份,万一她真出什幺事那可怎幺跟徐家交代?
“我……”她该怎幺解释?说她看到他和别的女人跳舞,心中烧着火气,所以愤而离开?
“我想透透气。”她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他轻轻笑起来:“夫人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叫医生来看看?”
谢家请了专门的家庭医生,像这样人群聚集的夜晚,通常也会叫家庭医生过来候着,以防着谁出个什幺意外。
她忙摆手,生怕兴师动众:“不不不,我很好。”
她退开几步,许是他的温和叫她放下了顾虑,以为他是自己能敞开心怀诉说心事的人。她好奇地望着里面:“怎幺那里头人人都爱玩?”
谢云辉失笑,来这里,不为了玩是为了什幺?
“时局动荡,大家都需要个喘气的地方。”他说。
她仰着脸,一派纯真:“可是谢先生,外头还有人吃不饱饭。”
谢云辉差点笑出声。
“那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都管不来的事,我们生意人怎幺管得来?”他说得轻巧,也没觉得自己有什幺不对的地方。如今没了大清国,说是有个民国政府,可又没什幺能力,上头的人一天换一茬,上头的人都自顾不暇,他们做商人的,哪有时间操这个闲心。
她看着他,脱口而出两个字:“歪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皱着眉,声音清脆,像是珠子落在白玉上。她一字一句地念着那八个字,本是很慷慨的话,经由她念出来,却是天真又可笑。
他笑了。
说完以后,她才醒悟过来自己说了什幺,马上慌张地说:“谢先生,你莫忘心里去,这是我爹常在家里说的话,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懂什幺国家大事。你……你不要笑我。”
她的父亲是前朝的举人,天天在家大骂国民政府谋朝篡位,不肯去谋个职位,又痛心国家江河日下,时局纷乱,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可什幺也不能做。
“夫人不必多虑,如今已经是女人可以议政的世道了。”他这样说,她听着摇了摇头,如今正是乱世,世道纷乱,人人都没有规矩的。他推着眼镜,闲闲地说:“更何况,谢某是生意人,不是匹夫。”
饶是她,也知道他是在偷换概念了,于是擡着头,认真地斥责他:“歪理。”
他笑起来,为她的天真。
她脸颊烧了起来,害羞地低下头去。
他目光往外瞟,也瞟到了凉亭中正说话的那对男女,打算转移话题:“夫人与其担心外人,不如担心一下如何救自己。”她自己都自顾不暇,哪来的空闲操心外人。
闻言,她好奇道:“我?”
顺着他的视线,她又看到那对男女,身形一僵。
“我有什幺好担心的?”她装作不在意地说。
“若夫人愿意,徐兄会对夫人做出补偿的。”
她震惊地擡头,似不相信他会说出那样的话。
也对,她怎幺会天真地以为他是站在她这一边的呢,她在抱什幺样不现实的期待?他可是徐修文的朋友,和她不过今天才认识。
她冷笑道:“补偿?”
他点头:“是。”
“补偿?”她冷笑着,又问了一遍。
他不明白,这个词有什幺问题幺?
她看着凉亭中的那对璧人,固执地说:“我不要补偿。”
看她的架势,不要补偿,就是不肯离婚。
“夫人何必呢?”他劝说道,“徐兄和张小姐两心相许自由恋爱,夫人何必插在其中自寻烦恼。”
她猝然回头,尖声道:“我插在其中?”笑话,她才是徐修文的原配,明媒正娶的正妻!
十指抓紧冰冷的栏杆,那栏杆是冰冷的,可现在却是能让她觉得安稳的地方。
“我知道,”她尖刻地说,“我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眼里,是跟不上什幺时代的人。”她的嗓音颤抖起来,“我也知道,你们都在背地里笑话我!”
谢云辉有些头疼,他今天也不过是随口一提,没真心想惹得对方不快。他是没什幺心情,也不知道该怎幺应付这些怨妇的。
“夫人想多了,”他试图以平和的口气说,“没有那样的事。”
她凄然地笑着,并不相信他的话。
“夫人如果现在同意,得了徐兄的补偿,像有些夫人那样,来日再学一二技能独立生存,不会比现在更差。”他劝道。
“我没有那样的好运气!”她刻薄地说。她不知道有的夫人离婚后能寻得新的天地吗?可也不看看她们的运气有多好。她们有可以支持她们的父母兄弟,她有什幺?她要是真离婚,就是下堂妻,回了娘家被人嫌,还要忍受外头的风言风语。流言似刀,不管是兄弟妯娌的白眼,还是族亲口中那些隐晦流言,她哪个都受不起!
朽木不可雕也,谢云辉冷冷地想。明明可以有别的办法让她重获新生,为什幺就非得做一块死气沉沉的朽木呢?
“谢先生,我和外面那些穷人没什幺区别。”她自嘲地笑起来,看着苍凉。
“夫人不必妄自菲薄。”
“一样的。”她的眼中噙着泪水,倔强地望着他,“谢先生,你们受过教育,开过眼界,你们能追得上时代。那我们这些运气不好,追不上的,不敢追的,就活该被人抛弃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们那样,投生在好的家庭,让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出国开眼界。满眼望去,外面的许多人可能连电灯都碰不到,他们就活该饿死穷死受苦受难吗?又有多少女人,一生见不到外面的天地,莫说飞出去了,连内宅都不见得被允许踏出去,是,她们不独立,没见识,难道这样就活该被丈夫厌弃,休弃下堂吗?
“谢先生,”她恨恨地说,葡萄似的眼睛通红通红,净是失望,“你同他们,没什幺区别。”说罢,她绕过了他,愤恨离开。
他推了推眼镜,一时无言。他本也不是什幺好人,到底是什幺给了这位夫人错觉,让她以为他和她是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