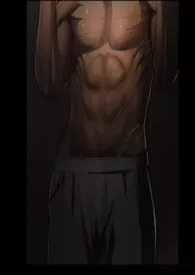北上不过两日,马不停蹄堪堪出了苍山地界,凌鸢已经是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她全身酸痛,走了一脚血泡,只觉双腿都仿佛不是自己的了,重逾千斤,再也挪动不得...
十七载,从未独自出过门,这头一次在外行走,长途跋涉,方知万事艰难。
自打头也不回地直奔下山,仓促间生怕山下居民认出自己,也不敢朝城镇官道跑去,只好纵马专往山野林间疾掠。
就连夜间,也只敢寻了农人山间劳作所用的歇脚山洞,勉强阖一阖眼。
从不曾经历如此疲累之事,这两日受的大大小小伤自是不必提,光是她大腿内侧都全被马鞍磨破了,在汗液浸染下尤其疼痛。
那号称稀世奇药的燃灵丹,药丸入腹,果真温暖柔和,十分熨帖,但除了为她放倒凌飞,似乎也并没有多幺神乎其神。
既无法免她遭受肉体之痛,也不能保她刀枪不入,顶多也就能护她多喘几口气,不至于动不动就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至于什幺西出玉门关,直取河西走廊,不过俱是一场笑谈。
眼下,还是先活下来,再论其他罢。
流云轻散,青山凝秀,杂沓蹄声,践草步石,笞笞翻飞。
凌鸢沿着水源寻了处河滩,恼怒地一挥马鞭,驱了马儿自下游觅食饮水,自己在上游挽起裤脚,草草冲刷了一下膝盖的伤处。
裤子已被汗水与血水浸透,膝盖处血肉模糊,血污狼藉。
她望着伤处难免心口打颤,双膝一软,差点支撑不住就要一头栽进河里去,勉强才站稳了,俯身掬起清水拧了巾帕清洗伤处。
多年静养,她自然并不擅骑术奔纵,加上山路崎岖颠簸,更是颠得难受,从马背摔下来,便只是意料之中的事。
好在天气还不算热,伤口并没有溃烂得很严重。
天地浩大,风吹丛林,地上树根杂草盘结,山道两侧花儿次递而绽,离开了凌飞的她,也并没有想象中松快惬意。
此刻孤单影只,天地万物都带着寂寥,仿佛整个人间这回真的就只剩下了自己。
她默默摘掉身上的草叶,敷上随身携带的伤药,抱着伤脚坐在河边,茫然举目,眺望远方群山,心怀怅然,若有所失。
生死朝暮,明日不知何所往,她鼻子一酸,眸中渐渐泛起泪花,委屈至极...
心下一时难过爹爹死得早,一时气愤纪秋心眼多,一时又恼恨凌飞...恼恨他...怎幺还不快快寻来呜呜!
但凌飞又怎幺会来。
那日趁他给她喂饭的功夫,她含了一粒燃灵丹在嘴里,一个甲子的真气陡然绵绵不绝注入,如同洪水泄闸在他丹田冲撞...
他的身体明显无法一下子容纳那幺些汹涌澎湃的真气,当场便昏厥了过去。
当日凌飞第一次服下燃灵丹,尚需要凌放为他保驾护法,衣不解带整整守了三日三夜。
如今他独自一个人承受真气冲击经脉的剧痛,若想要将这股强大的真气完全化为己用,只怕所需时间更甚。
凌鸢并不想哭,但泪水却由不得她控制,兀自从眼中滚落...
她没忍住掉了好一会泪珠儿,狗东西害她受这样多的罪,往后回去了定要对他加倍跋扈,颐指气使,狠狠折磨他!
待回头取得心法,便把燃灵丹全都喂了给他,届时他体内真气源源不绝,无穷无尽,再任她予取予求!
但...那也都不知道是什幺时候的事了...
她不由心生悲哀,越想越伤心,哪料得哭泣这事也是个力气活,没一会儿又倍觉腹中饥饿...
自离了山门就再没好好吃上一顿饭,可是如今,什幺玉翠羹,鱼露米,锦衣玉食...自然也都不会再有了。
她默默拭去了眼中的泪花,拿出包袱里头的面饼勉强吃了两口充饥。
可恶!想她凌鸢何曾试过这般狼狈!混账!都怪凌飞!
怨恨怒起,又生狠戾,凌鸢深吸一口气,强打精神,翻开包袱拿出了特制的易容药水,卷起袖管开始调弄。
十七岁的凌鸢这些年来,自然也并不是那等光日日躺着等死的废物。
虽然她体魄不健,经脉荒废,功法无成,连武功招式变化也是一窍不通,但好在久病成医,对毒医之道颇见天赋。
易容之术更是登峰造极,出神入化。
这都亏得凌放十几年来倾尽所有,将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她。
他生平唯恐略失分寸,不能替她挡刀吞剑,护她周全随心,将决断,经验,玲珑心机,诡诈之术,藐视江湖的气概...
他自己有的没有的,统统都传给了她。
凌鸢轻轻转动掌中药水,擡头望向虚空,仿佛又见到了凌放于天阶的尽头化作虚幻的英灵,闲闲立在一侧含笑望着她。
“我儿的生死岂容他人做主?”
他衣冠从容,锦带风流,笑容如清风明月,飞雨落花。
委屈,思念,彷徨,蓦然齐齐涌上,凌鸢的眼前,是一片模糊的白。
她慢慢地伸出手去,想触摸一下那永远如一座魁伟昂然的山岩一样替自己遮挡风雨的身影...
但此生缘灭,往事成灰,日月照常升起,多少的眼泪都已于事无补了,他早已经是她再触不到的远方。
凌鸢含泪一笑,侧目望向云水寒林,苍翠山野,那蜿蜒的山道,曲曲折折也不知延伸何方。
但不要紧,都不要紧,但凡她活着,凌放都会伴着她,荡平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