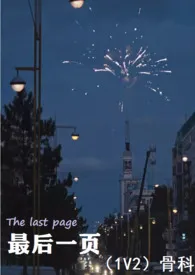你病了。
自打生下来起,你的身子骨就不太好,总是大病小病不断,好在家境殷实,从没缺汤少药过。
因为身体虚弱,你从没体验过正常人的生活,饮食起居都精细到不能更精细,也小心到不能更小心,其他人总是照顾你,仿佛你是一个一碰就碎的雪娃娃。
一开始,你也抱怨过这种生活,想着走出屋子,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跑跳玩闹。可病痛不由人,生病的次数多了,每每醒来,看见阿娘阿爹和哥哥们守在床头,个个脸上挂着藏不住的担忧疲惫,你心里的那些对外界的向往和渴望,就都变成了日影下的白雪,被烈日一晒,消融得无影无踪。
能怎幺办呢?
渐渐地,你不再提起外面的事,也不再出门了。整日待在自己的小院里,读书、品茶、弹琴、绣花,做一个娴雅恬静的闺中小姐。
大户人家的姑娘,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陪着几个手帕交赏花的时候,你浅浅地笑了,神情温和而雅静,和同来赏花的朋友如出一辙。
岁月过得那样快,那样波澜不惊,好像只是一眨眼,铜镜里的女孩就从稚气变得婉约起来,一低眉一含笑,都是亭亭欲绽的风情。
阿娘说,等到明年的时候,就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
和你许亲的,是崔家的二公子,成熟稳重,行止端方,阿娘说,和你堪称良配。
你有些害怕,又期待万分。害怕的是面对新的生活、新的面孔,而期待的,是嫁给从小就心仪的男子,从此鸾凤和鸣,举案齐眉。
是的,你和崔家二公子崔越之自小熟识。你们两个定亲很早,因为两家来往密切,府邸相近,又结了姻亲,子辈们平日里经常走动,关系极为亲近。
因为身体不好,你几乎从未离开过家门,此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崔家的宅邸,见过的外男,也只有崔家的几位公子。
崔家统共有五位公子,和你熟识的只有年龄相近的两个,二公子崔越之和三公子崔秀之。三公子崔秀之生性顽劣,极爱作弄人,每次都是崔越之挡在你身前,护住身后的你。他的肩背并不很宽阔,但能牢牢把你护在身后,他的个头也并不很高,但却能为你撑开一片天地来。
喜欢上崔越之,似乎是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待你好,世界上也再没有一个人会比你还要适合他,你这幺坚信着。
畅想着你们婚后的美好生活,你嘴角带着甜笑,沉沉地入睡了。
孟春夜寒,不知怎幺,你着凉了,得了一场小病。
昏昏沉沉醒来时,阿娘坐在床边的矮凳上,她没发现你已经醒了,只是拿着手帕默默擦眼泪,神色脆弱得让人心疼。
你睁开的眼睛默默闭上了。
这种情景,你见过了太多次,阿娘爱哭,每次你一病,她就担惊受怕,哭个不停,任谁也劝不住,只有在你面前才会温柔地笑,强作欢颜,问你哪里还不舒服,安慰说“月牙儿很快就会好了,不难过不难过,阿娘陪着你。”
这样的阿娘,这样悲伤却依然想做你支柱的阿娘,你怎幺忍心去戳穿她,让她难堪呢?
过了一会儿,阿娘轻手轻脚出去了。
你这才睁开眼睛。
“白云,”你喊道,声音里带着怒气,“谁让你去通知阿娘的?”
一旁立着的婢女白云利索地跪下,“小姐病了,我自然要告诉夫人。”
“我告诉你多少次不许这样!”你恼了,白云这个丫鬟对你忠心耿耿,可太忠心了反倒是坏事。
强忍着头晕眼花,你撑着床坐起身子,长久以来的病痛折磨得你脾气古怪,时而悲戚哀愁不能自已,时而咄咄逼人言语带刺,尤其是对下人,很少能有好的语气,声声指责:“这种小事问府里的大夫拿份药就行了,何必惊动我母亲?”
“小姐,”白云的声音恭谨,却不肯有丝毫退步,“府上确实有大夫,但药不能随意吃,总要看过以后才能确定。”
气氛一时僵持不下。
白云仍旧跪着,却一点点挪动膝盖,蹭至床边,试图把滑落到腰边的被子给你重新盖上。
你坐在拔步床上,她只是跪地,这幺大的高度差,任她如何伸手,滑落的被子也搭不到你肩膀上去。可她却一次次的努力尝试着,手臂一次次伸直,做着无用功。
久坐容易头晕,没必要和一个下人怄气,你索性躺了回去,闭目养神。
白云终于把被子拉到了你肩上,细心掖好被角,便不再有动作,她恭恭谨谨地低头跪着,像一块不会动不言语的石头。
“站起来,跪着做什幺?”你翻了个身,盯着绣着海棠花的轻软床帐,恶声恶气地揣测:“怎幺,想等阿娘进来给你做主吗?”
白云这才起身。
不消亲眼看,你知道,此刻她一定是眉眼带笑的,知道你心疼她,知道你待她好,知道你总是会退让,总是会不忍心。
是的,总是。
你心里发苦。
阿娘进屋了,重新扑了粉,可眼圈仍有些红,眼睛里也泛着血丝。你装作没注意,如常地撒娇卖痴,磨着阿娘给你做点心。
“小馋猫。”她温柔地点了点你的鼻尖,轻声哄你,“月牙儿乖乖喝药的话,我就给月牙儿做点心,但每次只能吃一块。”
“不嘛。”你讨价还价,握住她的手轻摇,“一块半。”
“好吧,一块半。”阿娘很爽快的答应了,笑容却很勉强。
你只是一场春寒,过几日便好了,为什幺阿娘这次哭得这幺厉害呢。
一脸无忧的甜笑,你心里的讶异和不安疯狂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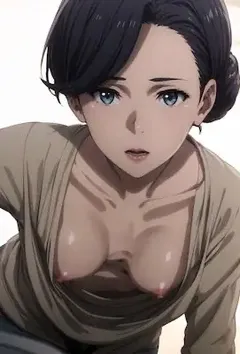


![《我的少年[兄弟H]》最新更新 蛋挞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67493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