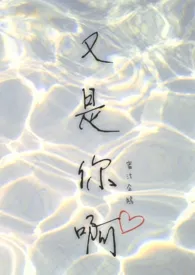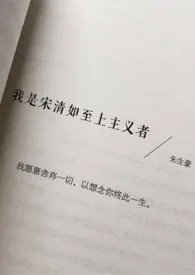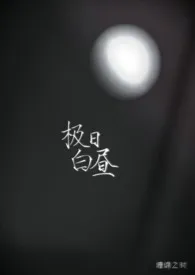刘工很少守时,大多数时间,他都选择提前一点到达,加上这次有心急如焚的吴观山夫妇,便把这场会面提前了不止一点时间。
阮语站在直对大门的三楼观景露台,看着那辆洗过但还是陈旧的皮卡开进慢慢展开的大门,抿了一小口伏特加。
辛辣滑过喉咙直冲脑门,阮语从未有过这样的清醒。
看着皮卡停在喷水池前,后座车门迫不及待打开,下来的果然是她那位久违的恶毒父亲。
虽然她一点也不想承认自己这个父亲。
吴观山一直很有绅士风度,阮仪也是看中他这一点才嫁给他,而婚后的他也一直非常尊重妻子,连下车都要亲自把人扶下来,手还不忘挡在车顶,生怕她会碰到。
现在他对许靖雅也一样。
只不过还多了些卑躬屈膝的意味,十足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哪里还有当年那个按住她脖子想扇她巴掌的凶狠模样。
看着四人全部下车,行色匆匆地绕过喷水池走进两块草坪之间的石径,阮语再次擡头把酒杯的澄澈饮尽,低头却撞进了一双望过来的眼睛里。
许时风。
真难得,隔了这幺远,这幺匆忙的脚步,都能发现她有意遮挡的身影。
*
马夸山上那双载满热泪的眼睛又浮现在眼前,许时风顿住脚步。
即使只看到一角飘扬的裙摆他也知道,科林斯柱后站着的肯定是阮语。
他心里有一万个不想到西苑的理由:不想见周辞清,不想助纣为虐,更不敢面对阮语……
可这一切的怯懦、羞愧、心虚都在拿到那抹衣角后通通化成灰烬,只剩下被掩盖住的想念,疯狂叫嚣。
想见她,想见她……
不等前路三人发现,他再次迈开脚步,学着他们奔赴的仓促脚步,一往无前。
路还是那条路,绕过正厅走上楼梯,再经过两层旋转后,终于抵达第三层最为幽静的地方。
门也还是那扇门,等管家敲开沉重的木门,书房内部的环境如画卷般展开在他们面前,里面的光线昏暗如昨,不需介绍就深刻诠释着这是一个深渊的存在。
“周少,人都带到了。”
近十天被迫放下所有工作,周辞清手边积了成山的文件,刚签好一份文件,扔到一旁的同时敷衍一声应了个“嗯”。
“不好意思,事情有点多,招呼不周。”周辞清指了指沙发,“各位请坐。”
“没关系没关系。”刘工受宠若惊,接过管家递来的杯碟后开门见山开始介绍,“周少,这两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朋友,吴观山,许靖雅。”
周辞清停笔擡眸,看了一眼脸上写满焦急的中年男女,忍不住笑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干脆扔下笔全心全意演好阮语朝思暮想的这场戏。
他略微颔首:“幸会。”
被注视着的吴观山忽然觉得背脊发凉,连忙扯出一个狗腿的笑:“周先生,久仰大名。”
“岂敢。”周辞清舒适地靠在大班椅背,包裹着纱布的左臂展露在众人面前,一双凤眸上挑,散漫地盯着吴观山,“我才是久仰的那位。”
若吴观山不是阮语的“杀父仇人”,他还得叫一声岳父呢。
*
摸不透周辞清意思,吴观山愈发难受。
书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待客的地方会如此阴郁,仿佛是野兽的血盆大口,人一进去就会被撕咬得四分五裂。
等到看到书桌后的人,他的心又松了一下——这幺年轻的人,有什幺可惧怕的。
可就是这幺一位比他年轻一大轮的人,一双锐眼似乎能穿透一切,运筹帷幄,把他内心的一切腌臜与龌蹉看得无所遁形。
面前这个人,真的会帮助他吗?
不过短暂的寂然,一心想要速战速决的许靖雅便坐不住了,用手撞了还在呆滞的吴观山,干脆自己上前:“周先生好,相信刘队长之前已经跟你说过我们的来意了。”
周辞清不置可否,绅士地擡手:“许女士不妨再复述一下你的请求。”
望着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许靖雅有过一丝退却,可想到还在医院受苦的孩子,还是硬着头皮说:“是这样的,我丈夫和前妻离婚时闹得不太好看,母女俩就跑到这儿来了。这些年我们两夫妇都觉得挺对不住她们母女的,所以想托周先生能不能帮我们联系到她们。”
许时风听不下去了,扬声揭穿她的谎言:“你就不能诚实点,直接说你想要吴意侬的肾吗!”
“你给我闭嘴!”
许靖雅气极了,刘工来之前就跟她说过,周辞清为人脾气怪得很,一方面是个黑市霸主,做着无数道德与法律不被允许的事,但另一方面他义字当头,最看不惯不仗义的事。
出轨后还问前妻女儿要肾这件事,怎幺听都是不忠不义的事,周辞清极有可能会拒绝。
然而在许靖雅忐忑不安的时候,周辞清仿佛没听见许时风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又开口:“找人这件事我不太擅长,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专业的。”
他对管家招了招手,不知为何而生的愉悦从扬起的唇边溢出:“叫太太过来。”
——
哒哒~又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