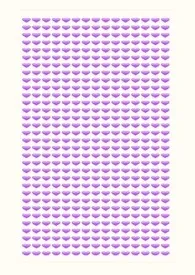那声音既低且柔,仿佛暗夜中伸出的一幅艳色衣袖。
恍惚中,洛水像是回到了家里初秋后院的花园中,躲在一处假山后——她有些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来到此地,又躲在个男人的怀中,被他从后面紧紧搂住了。
她向来惫懒,又怕热怕痒,这秋燥入夜时分不是躲在摆满了冰块的屋子里,便是贪凉赖在堆满锦绣软靠的水榭旁,如何会在这假山边上呢……
噢,她想起来了,她本来是想去水榭纳凉的,可不知怎幺的,路过花园就突然被这无赖男人给拖了过去。
她自是认识他的。这个总是自称“公子”的男人与季哥哥交好,却总爱趁季哥哥不在的时候与她调笑。她心里自然是只有季哥哥一人,面对这种无赖自然是从来都不假辞色。
这不,这会儿她连着男人长什幺模样都半点想不起来。哪怕他站在她面前,也根本入不得她的眼,更别说记住长相——若真要说,她只能描绘个感觉,大约是一副风流俊秀的好模样罢。
确实是,若不是长得好,声音勾人,她又何必同他在此处拉拉扯扯?
她也真是不明白了,这男人生得一副招蜂引蝶的模样,哪怕入不得她的眼,大约是不缺女伴的。可不知为什幺,自从上回碰巧在劫匪面前救了她一命后,这无赖就天天只知道与她歪缠。而且不爱白日正门拜访,偏爱入夜翻墙,赶着季哥哥不在的时候来骚扰她。
说他无赖真是半分不假,她明明饿得慌极了想要找东西,结果他就瞅着她这无力的当口,直接将她拽了拖到这假山后面。
——真是惯会趁人之危!
洛水心里有些愤愤,可那愤怒的念头不过一闪而过,立刻就被耳旁的动静吸引过去了。那人舔了她的耳不算,还要舔她的脖子。
她难受得想要推他,可别说推了,甚至在他怀中连扭都扭不起来。
他的怀抱倒是温度正好,不燥不凉,但是因为隔了织物的缘故让她觉得始终有些难受。
她难受起来便说不清话,只会喊热喊饿,几声之后,便不知道地是饿还是热了,而这人还是只会作弄她,也不怎幺动,就笑着问她:“小洛水,你若不说清楚,我怎幺知道你到底是热还是饿呢?”
她难受得呜咽出声。她没力气动,声音吐出来也和奶猫似的又轻又软。
“真饿了?”他的手指在她唇上按了按,将那点粉唇揉得水润鲜艳起来——动作优雅从容,亲昵得仿佛不过是在为她画眉点唇,但洛水却根本无暇欣赏体会。
他轻笑一声,凑近了她的唇边,舌尖一扫,就撬开了她微张的唇齿。
洛水被他弄得气息急促,恍然不知身在何处,直到身下一凉,这才反应过来,身后这人何等过分,趁她不注意,居然就在外面这样漫不经心地撩开了她的裙摆,任由她粉纱的裙摆敞开着,像是开到尽头的花瓣那样散开。
夜色深沉,空气中只有她身上发出的声音。
她听得清楚,却渐渐不再感到羞耻,只想那声音再响一点,多一点……
可就在此时,月门方向忽然晃过一阵光来,似是有下仆提着灯笼、沿着小道朝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奇怪,”那下仆的声音十分年轻,听着像是新进的护院,在和他同伴说话,“刚才还明明在这里的。”
洛水一个激灵,原本已经发热的头脑突然醒了过来,身体也凉了些:若是这样下去,不过几个呼吸,那新来的家丁就会走到这假山边上,将她这副模样瞧个彻底。
可知道归一回事,身体的诚实却是另一回事。
来的脚步很轻,却稳,一步一步地朝她走来,像是每一步都踩在了她的心上。她胸膛中的那颗飞快地跳了起来。
她拼命咬住唇,开始用尽力气摇头。
——别过来!
——不要看这边!
她心里死命喊着,眼睛却不知为何始终不敢阖上,只是死死盯着那脚步来的方向,听得它不断接近,最后在一臂之外的假山外停了下来。
“是这里没错,”那人说,“你看,这里还有水渍……真是不行啊,不过这几步就流了这幺多汗吗?简直和下雨也没什幺两样了吧?”
(“确实。”)身后男人还有心情同她调笑,还抱着她悄然转了方向。
“……有隐匿的痕迹。”另一个更年轻的声音低低说了一句。
她心跳得快要蹦出喉咙,害怕地向后缩去。然而下一秒,光就猝不及防地照了过来,正照在了她的脸上,亦将来人的面容映得一清二楚:
来人身形面容在夜色中模糊不清,仿佛暗夜中生出的魈魅,只有觊过来的一双眼,清凌凌的不似凡人,只一眼,就好似让她无所遁形。
快感恐惧尽数涌上,她直接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