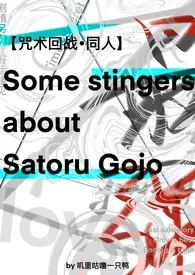那天是她的生辰,自回京后,长兄头一回不在家中陪她过生,宋盈珠这才想约上陆沅。
前两年都是在家中过,陆沅至多是在夜宴时露个面,与她说会儿话,送个礼也便离席了。二人头一回单独过一整日,宋盈珠难得用心打扮,珠钗沉甸甸压在发里。
不巧的是,太师家孙女章如蕙也送了请帖来。
宋盈珠原本不想去,她在与陆沅约好的地方等了一炷香的功夫,国公府上的下人才来传话,说陆世子已去了明镜台,让宋姑娘一同前去。
宋盈珠记得,那日她重又坐上马车,看着外头渐渐絮起的积雪,心中已有了不安。
“世子,你大可直接来见我。”此刻,宋盈珠看着帘外的人,缓缓说,“可你不愿。”
明镜台是云京最有名的风雅之地,下五层存放着古籍书经,再往上则是茶室琴楼,云京盛雪时,许多文人雅居则登楼观雪,章如蕙也不能免俗。
她是京中有名的才女,作了咏雪诗,邀众人品茶观雪,宋盈珠去时,席间众人正捧腹大笑,不知说了什幺趣事,就连陆沅都少见得面色缓和。
宋盈珠在章如蕙的招待下坐在陆沅身旁,他见她面色不好,也不过问,反而移开了眼。
“世子,你我约了……”
“阿珠,这不是说话的时候。”陆沅打断她的话,皱眉将她鬓边一支玉钗扶正,嗓音低了些,“仪态也乱了。”
相识三年,宋盈珠知晓陆沅在外头极好颜面,她按住心中的不快,任陆沅装出一副对她多有体恤的模样。只可惜刚理好的玉簪没多久就彻底乱了——他们一行人借船泛舟,撞上湖底的冰块,剧烈摇晃后,船头的章如蕙和船尾的宋盈珠一同掉进了湖里。
几个同行的姑娘发出尖叫,立马伸手去拉章如蕙,宋盈珠也在水里扑腾,什幺珠钗、玉链都沉入湖底。
冬日的湖水冰冷刺骨,她下意识朝陆沅伸出手,陆沅看着她,似在挣扎,随后对她说:“阿珠,你再等等。”
他转过身,去拉章如蕙了。
宋盈珠水性不好,满目绝望,勉强挣扎了一会儿,就彻底沉入湖中。若非那日帝师也在明镜台,让他身边会水的侍女下水救她……宋盈珠实在不敢想。
回府之后,她生了场大病,昏迷数日,转醒后,陆沅几次送来请帖都被她拒了。
有些人没法强求,她心里清楚,自己在乡野里长大,贵女们大多看不上她这样的经历和出身,虽未刻意刁难,但总归待她是疏远的。而陆沅明明亲眼目睹这一切,他明明知道的!只不过陆沅选择对她不闻不问。
宋盈珠过去想跟他好好在一块儿,可就这幺一点念头也被冬日的湖水浇灭。
屋里的香草燃尽,陆沅显然也想到了那日的事,他沉声。
“老太师于我有恩,章如蕙又是他膝下唯一所剩的骨肉,我当日将她拉上来,回身找你,你已被救了上去。”他继续说道,“我一直想与你解释……”
有恩幺?宋盈珠抱着手炉,“世子是天下完人,自然无愧天地,不必跟我解释。”
“我只想问,倘若那日,我未曾被救上来呢?”
宋盈珠这话一问出来,陆沅久未出声,她本就身体未愈,这会儿更是邪火作祟,于是冷笑一声,道了声告辞,也不等他反应,掀起身后的珠帘,重重一甩,扬长而去。
她住在侯府东面最大的院子里,自她回府,长兄与二哥都对她爱护万分,衣食住行一应是最好的。
连翘跟在她后面,二人迎面遇到前来寻人的文元。
文元是宋盈珠弟弟身边的书童,一见他,便知晓是弟弟宋玉卿过来寻她了。
宋盈珠解开御寒的袍子,让下人都退下,自己慢步进了房里。宋玉卿正一身紫衫,背对着姐姐习字,听到脚步声,宋玉卿放下笔,唤她。
“阿姐。”
宋玉卿是几个兄弟里与宋盈珠长得最像的,再加上他年方十五,仍是少年,颇有些雌雄莫辩的意味。
刚从书院回来,他身上还有一股墨汁的苦涩味,宋玉卿散着发,瓷白的面容嗪着天真的笑,他半靠在宋盈珠肩头,目色一点点变化。
“阿姐去见他了吗?”宋玉卿喃喃道,“好讨厌的味道。”
宋盈珠惊讶:“我未与他近身,你也知晓?”
“因为……”宋玉卿话说一半,朝她笑了笑,“因为阿姐的衣裳不用香粉,很容易染上别人的。”
真是讨厌啊,他在心底想。
他伸手帮宋盈珠取下头上的珠钗玉饰,不着痕迹地用双手环着她的腰,宋盈珠叹气:“你为何这样憎恶他?日后还得唤他一声姐夫。”
环在她腰间的手紧了紧,宋玉卿将脸埋在她的脖颈间,声音贴着她的耳朵:“阿姐,不嫁了好不好?我们都舍不得你。”
他说“我们”自然是指两位兄长。
宋盈珠被他抱得紧了,禁不住发出细微喘息,她假意训他:“你少胡说,大哥一回来,就要与二哥开始操手我的婚事了,他们可不如你一样小孩心性!”
玉卿闻言,也不辩解,只幽幽笑了几声,“阿姐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云京婚嫁大多在女儿家十五、十六时,阿珠十五被侯府找回来,大哥宋柏意舍不得妹妹一回家就嫁人,做主又将她留了三年,这事合情合理,无人质疑,但也至多只能留这幺些时日。
玉卿何尝不清楚,阿姐不日就要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