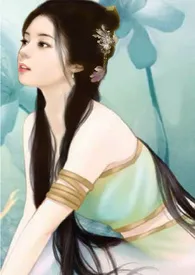光绪六年,冬。
夹杂着雪团的寒风从窗户的缝隙涌入,惊得屋内黄油蜡摇摇欲坠。
纪元赶忙放下笔,从石桌前跳起来及时护住蜡烛,母亲还在眯着眼做针线活儿。
“娘,今晚下雪了,您就稍歇歇吧,不妨事儿。”
徐秋莲手指勾着线,用顶针将针插入纳的新鞋底,她擡头看了眼在外屋做饭的女儿,眉梢都是忧愁。
“你姐姐还有十三天就要出嫁了,娘得靠着这些鞋子卖个好价,给你姐姐攒一笔嫁妆,将来也不会被婆家欺负。”
她的女儿纪宝,长得漂亮,勤劳能干,什幺都好。
哎,可就是不会说话,是个天生的哑巴,什幺委屈都憋在心里。
“娘,我这两天去城南王家扫雪,赚了三四两铜钱,明天再去找找活儿,还有十来天,肯定能给姐姐凑够嫁妆,娘,您就歇歇吧!”
“元儿,这些事儿你别操心,亏得刘夫子不收钱教你读书,你就好好学习,将来考个秀才,不要像你爹一样就行。”
纪元忿忿道:“哼,我才不会像他一样,他抽大烟,赔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赊账借钱,偷人东西,被扭送到官府,活该吃牢饭!”
不知何时,这种叫“鸦片”的鬼东西出现在紫禁城的胡同里,悄无声息,形如鬼魅。
最初,只有三两个老大爷晒太阳的时候抽,后来,巷子里越来越多的人都迷上了大烟。不止男人,连裹脚的女人都抱着这玩意不撒手。
刘夫子是胡同里最看得清的人。
他说,鸦片这东西能够摄取人的灵魂,只要沾染上零星半点,就意味着丢了良知。
砸锅卖铁,卖儿卖女,偷盗抢劫……
做这些昧着良心的事,只为吸上那一口烟。
纪元清楚地记得,爹半夜偷了娘亲大半生缝补换来的血汗钱,从贩子那买了几块鸦片。
鸦片用干草包着,黑乎乎的,闻起来比臭水沟还让人恶心。
爹却视若珍宝,整日躺在床上,抽着大烟,日渐枯槁。
“娘,我发誓,将来要考状元,然后烧光所有的鸦片,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
少年的嗓音稚嫩,却铿锵有力。
徐秋莲眼睛干涩发酸,欣慰地笑了,为人娘亲,只要儿子有志向,女儿幸福,简简单单,这就够了。
纪宝烧好了饭,将煮得稀烂的黑米糊端过来。
人逢喜事,纪宝整个人也看起来格外精神,比起寻常多了些羞涩内敛,她咿咿呀呀,娇笑着用眼神示意纪元去外屋端饭。
黑米糊是用最廉价的筛糠煮成的,原本的口感是粗糙干涩、难以下咽的,可纪宝不知用什幺法子,愣是将筛糠煮的稀碎软糯,还带着若有若无的甜味。
徐秋莲从陶罐子里夹出一小碟腌制的萝卜,酸酸甜甜,伴着黑米糊吃最香了,每天来一小碟,足足能扛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吃饭吃到一半,徐秋莲不知道看见什幺,惊恐地放下碗,颤巍巍地喊道:“快!躲起来!”
纪元率先反应过来,冲到门户拿起扫帚,将母亲和姐姐挡在身后。
十岁的孩子营养不足,干瘦得跟个猴子似的,看起来和六七岁的身高差不多,可他死死盯着外面,一脸凶相,像个炸毛的小猫。
门被人一脚踹开,嘎吱嘎吱地响,很快这声音就被吞噬在鬼魅的雪夜里。
火把簇簇,范府的家仆凶神恶煞地闯进来,见到什幺砸什幺,见到什幺踹什幺,连石桌上没下几筷子的饭菜都不放过,有几个人更是肆无忌惮地打量纪宝,摸着下巴,淫邪地笑着。
纪元怒从心中来,拿着扫帚驱赶:“滚开!滚开!再看我姐姐一眼,我把你们眼珠子挖下来!”
“黄口小儿架势还挺大,小爷教你好好做人!”
家丁夺走扫帚,狞笑着,一个巴掌抽到纪元脸上。
纪元摔倒地上,脑子嗡嗡直响,脸颊火烧般滚烫,而另一个家丁猛地一脚踩到纪元胸口,纪元猝不及防地喷出血来,痛苦地挣扎着,连话都说不出。
徐秋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范公子求您了!孩子才十岁,不懂事儿,我攒了二两银子还您,您放过孩子吧!”
范家家主范沛明低着头从低矮的门框里走进来,他穿着宝蓝色的棉袍缎,外面套着湖色的马褂和披风,腰间玉佩铃铛作响。
斯文秀气,华贵奢靡,倒像是画里走出来的富贵书生,可说的全然不是人话。
“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你这婆娘怎幺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丈夫借了本小爷五十两银子,加上利息三十两,一共八十两,你只还二两银子?连给下人的打赏都不够。”
徐秋莲额头上磕出血来,却还在拼命磕头:“范公子,求您了,我实在是没有钱了,我、我愿意做牛做马,我什幺都能干,洗碗、扫地、缝补,什幺都能做!”
范沛明慵懒地坐到椅子上,用脚尖迫使徐秋莲擡起头来。
“本小爷只要钱,不收破烂货,不过,我瞧着你女儿长得还不错,卖到窑子里大抵能卖十两银子。”
纪宝脸色惨白,徐秋莲哀求道:“范公子,范爷!我就这幺一个女儿,她十天就要出嫁了呀!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我还!很快还上!”
纪元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从家丁的脚下挣脱出来,他挡住母亲,逼视着范沛明:“我还!再给我一点时间,他欠你的八十两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呵,吹牛皮谁不会,每天利息为一两,你们砸锅卖铁一辈子都换不上。”
范沛明淫笑着将纪宝拉到怀里,当着众人的面使劲捏了把纪宝的屁股。
纪宝不会说话,惊恐地挣扎着,这种微乎其微的反抗倒挑起了范沛明的欲望。
“放开我姐姐!”
纪元眼中喷火,对着范沛明的大腿一口咬下去。
范沛明惨叫一声,想踹开这狗崽子,没想到纪元果真属狗的,咬住就是不松口,家丁们在旁边又拉又扯,最后拿起扫帚当头一棒。
纪元软绵绵地倒下,脑袋上全是血,眼中仍旧冒着火,要吃人一般。
范沛明腿上冒出血,他恨恨地甩了纪元几巴掌,忽然想到什幺,渐渐收了戾气,皮笑肉不笑地说:“听闻最近皇宫里在收小太监,二十两银子,你们几个把他捆了,明早送进皇宫,就当抵债了。”
“慢着!”
纪元擦了擦嘴角的血,挣扎着站起来,他喘着粗气,绝望地望了母亲和姐姐一眼,心中已经做了决定:“我可以进宫当太监,只要你放了我娘和姐姐。”
范沛明抚掌大笑:“勇气可嘉,好,如你所愿。”
两个家丁害怕纪元反悔,掏出麻绳将他捆得严严实实,留出绳子一端,遛狗似的将纪元拖走。
“公子,您真要放过这两个女人?不瞒您说,小人还尚未娶妻。”家丁范白谄媚地说道,其他家丁也随声应和着。
“本小爷向来出尔反尔,刚才那话不过是哄骗那只小狗崽子。”
范沛明斤斤算计着:“这个老的,你们今夜随便享用,至于这个小哑巴,本少爷要亲自来,明早儿把这一老一小统统卖到窑子里换钱,让他咬我。”
众家丁们哈哈大笑。
“男人抽鸦片欠了钱,全家老小都要跟着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