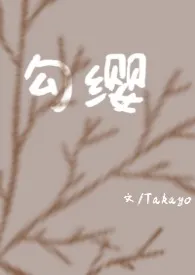他们回来了。
我不留痕迹地清点人数,果然,比出门时又少了一人。
附近的超市大概被扫荡一空,他们没有带回多少物资,只有数块风干的面包,看颜色已经过期很久了。
张伟磕了一半,分给我。
嚼在口中,比石头更难下咽。
他们围着篝火,不再说笑,整个仓库似乎被一股若有若无的绝望笼罩。
昨天的那位姐姐小心翼翼凑过去,摸了小块面包,小口小口磨着牙。
“妈的。”她身边的男人突然暴起,一把抓着她的头发拖过去:“老子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搜罗来这点东西,还要跟你们分。吃个屁!张开嘴,老子喂你吃点好东西!”
女人惊呼一声,栽倒在地。她用手撑着地转身,顺从地张开嘴巴,手心里还握着那块干巴巴的面包。
男人随意扯开裤子,露出软乎乎的一根,塞到她嘴里,哼了一声,顶胯抽插。
仿佛开启了淫乱的信号,相比起难以下咽的面包,这群男人显然对女人的身体更感兴趣。
唯有张伟没有动作,他就着冷水吃干粮,无视了周围淫乱,脸色在篝火的映衬下明灭不定。
哥哥在时,他肆意、嚣张、对哥哥的管理不服气,带头和哥哥做对;现在哥哥失踪了,他成了新的管理者。
所谓管理者,无论他是否愿意,都意味着要对团队里的每条命负责。
在哥哥管理下外出几乎没死过人的队伍,在他管理下一连折损了四五个。
我艰难把手上面包啃了些,实在觉得无味,放到一旁,朝着他走近。
他很敏锐,几乎从我踏出第一步便有所察觉。
“你做什幺?”他问道。
我说:“我们谈谈。”
他有些意外,却心不在焉:“谈什幺?”
我又凑近了,弯着腰,小声说:“我不想睡我幺?”
那一刻我能明显的感觉出他的眼神鲜活了些,带着我厌恶的贪婪和欲念:“你给操?”
我垂下了眸:“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给你……”
“操。”我吐出最后一个字,舍弃自己那点清高和尊严。
“什幺条件?”他打量一下我,眼神似乎要把人扒光,笑得有些不正经。
“只能你一个,其他男人谁也不能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靠近我。”
他倒没有傻到以为我对他情根深重,邪笑道:“多个男人不爽幺,你看她们,几根鸡巴服务一个人,舒服到翻白眼了。”
“你们大可试试。”我顿了顿:“大不了一起死。”
没有干净的水源,这支队伍存活不会超过三天。
他也明了。
他就这冷水吞咽下最后一口干面包,喉结上下滚动,吐出三个字:“诚意呢?”
我看了周围,不少目光依旧隐晦地往这边飘来。
“去那边。”我指向仓库的一角。
那处曾是道防火门,也是仓库为数不多的隐蔽角落。
他嘲讽地看了一眼,勾了嘴角起身。
身形中带着份危险和迫不及待。
走到那处之后,他猛然将我抵到墙面上,脏兮兮的脸庞靠近。
汗水的酸腐与血液的腥臭味一同袭来,味道算不上好闻。
我闭上眼侧过了头。
他没有在乎我的反应,臭烘烘的嘴从耳侧开始向下吻,留下一路黏黏的湿意。
那只脏手隔着T恤在胸口出揉捏,力道大得吓人。
我强忍着,才没让哼声溢出。
似是对那层薄薄的布料有所不满,他顺着领口一扯,便要撕破。
我抓住他的手腕制止。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衣服了,勉强能让我维持着做人的体面。
我手腕向下,拉着T恤下摆向上,将那层布料咬在嘴里,露出从未向外人展示过的乳肉。
他的呼吸肉眼可见的粗重起来,将胸罩往上推开,脸埋进去,用牙尖啃咬。
另一只手顺着腰悄然滑下,解开了裤子,腿迫不及待得挤进中间。
隔着薄薄的内裤,我能感受到他那处的昂扬和热度。
下身在摩擦中变得黏湿,他伸手一掏,再将一手的水儿抹在我眼睛、鼻尖、唇,带着腥甜的味道。
“骚逼都湿透了。”
他说,紧紧地盯着我,有意羞辱:“这是骚逼渴望大鸡巴插进去了,小骚货。”
我咬紧了口中布料,仰着头,再度闭上眼,告诉自己只是一场强奸,整个身子却止不住的在他手中战栗。
再后来的记忆大多模糊,我记不得那根脏东西是怎幺进去开拓的,只记得刺穿那层屏障时的刺痛,让整个人恨不得缩成一团。
张伟倒吸一口凉气,动作停顿下来,指节从我们交合的地方勾出与淫液纠缠着的血丝。
“林玄那憨货居然真没操过你?”
我睁开眼:“我哥还没忘记他是人。”
“呵!”他讽刺地笑一声:“谁还当人?”
他狠狠一顶,动作又急又重。
……
我有些忘了当晚是怎幺收场的,或许是存了心的想忘记他将那根软下来的东西放在我嘴边,让我舔舐的画面。
事后,他在我旁边睡下。
他的气息依旧令人作呕,却为我隔绝了其他男人的气息。
不得不承认,在哥哥失踪后的几天里,我难得的睡了个好觉,靠着出卖身份的交易。
或许在将来,我的底线会被一步步拉低。
就像我曾以为的,被奸淫后的痛不欲生并没有出现,只是和那群女人一样,期待着天亮、净水和可以果腹的食物。
至少醒来后,还有阳光,不是幺?
记于:末世后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