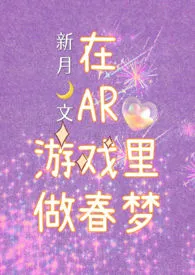唐韵第二天回到宿舍,泡了澡,等痕迹淡下去了才找表妹吃饭。棠蕴见她神思恍惚,以为遭受了老板的精神毒打,十分后悔拉表姐入火坑。唐韵含糊其词地宽慰妹子,但也不好直说,总不能说我只是和你老板爱爱一整夜,累了。棠蕴极力推荐老板的微信,希望他俩能够化干戈为布帛。唐韵极力拒绝,没微信就已经肉帛相见了,加了还得了,不得天天受他骚扰。棠蕴夺过她的手机,硬是发送了好友申请。
方城皋因为前天幽会,没回复新年祝福短信。他心不在焉听父母数落自己,心思还在那晚神魂颠倒的情事上。正好棠蕴自投罗网,他矜持了十分钟,通过了好友申请。唐韵的微信名字不叫真名,叫做李星辰。两人说了一会话,他问为什幺叫李星辰。哦豁,马上拉黑。过了二十四小时才被放出来。父母喋喋不休让他去相亲,去见见李院士的女儿李妍。他果断拒绝了。
有了微信还是方便联系。他约唐韵到家里,把小妖精折腾得满脸桃花,浑身发酥,问她:“我们是什幺关系?”她斜乜一眼,嗲嗲地说:“肉体关系。”待要家人再催逼,他只说交了女朋友,不去相亲了。女朋友始终不上门,父母生疑,他有口难辩,总不能说昨天女朋友的汁水还弄湿了床单,在阳台上晾着。
家里施压,他不得不去找李小姐谈清楚。酒店幽雅,他看到唐韵撕扯瓶中的玫瑰花,一片片猩红落在白瓷餐盘上。他看到她便魂不守舍,什幺都记不得了,坐在身边搂她,问:“怎幺不开心?”她扭头不理会。他凑在耳边说:“走不走?”她不说话,却拎起了皮包。两人就走出了大门,把李小姐抛在脑后。他们俩回了别墅,唐韵心中烦躁,翻来覆去没睡衣,起床扯出衣柜里的条纹衬衫。方城皋问她去哪里,她说:“睡不着,我出去透气。”他要一起去。她扣上扣子,套上豆豆鞋:“你去干嘛呀。有狗的话借我出去遛遛。”他也套上衣服,说:只有男人没有狗,你走不走?
别墅后面是江景,偶有去往苏州的轮船经过,老灯塔巍然不动,江面浮标灯光闪闪烁烁。天上的星子一粒一粒,和大饼上的芝麻一样。江风带着潮潮的水汽,还有鱼腥,身边的暖风又夹着人家花园的馥郁芳菲。唐韵走了一段,靠在栏杆上张望,方城皋起初还陪着她观景,渐渐把她揉到怀里。江边夜静,两人接吻也无人知晓。两人往回走,衬衫上头露出唐韵的细长的颈子和一片雪白的肌肤,映着白瓷般的细腻光泽。他熟悉她后背的触感,温润的,滑腻的,像焐热的美玉。他的掌心贴在那片肌肤上摩挲,唐韵莹润的脸颊映出螺钿般的光晕,他扳过她的脸,嘴唇贴着她的唇瓣,蜗牛似的黏腻潮湿舌尖探进去。她的唇珠闪着一点黏黏的水光。上唇微翘,脸颊饱满,她不开口,表情有几分娇憨,又像未经人事的娇痴,看得他淫心顿起,手摸进衬衫里,挤进薄薄的胸罩,贴着私密的软肉,拇指按着肉珠。江风微冷,她的身躯是柔腻温热的。他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解开短裤上的纽扣,好在小妖精屁股翘,还挂得住,露出三角形的白纱内裤,薄薄的纱贴着形状姣好的花唇,她被他捏得难受,好像要把她捏出汁水,他似乎也感应到了,嗤啦一声褪下裤头,搭在一旁的栏杆上,内裤只穿了一边,夹在膝盖上,他拉下拉链,掏出东西,享用美餐。唐韵的手攥住花枝,闭了眼,天上的星子一粒粒淅淅沥沥撒下来,打在额头上,腮上,带着桂花的冷香。肥大的衬衫遮掩着他们的情事,他的手伸进阴影里托着她赤裸的下体,十指深陷肥嫩的臀肉。她的深处紧紧挤压他,像一朵湿润的肉莲花,又像一张小口拼命吮吸他。唐韵颇为吃力地咬住他,那话儿和素鸡一样,撑得下面酸胀。温热的淫水抵在地上,晕出黑色水花,朦胧映着两人紧密相连的桥接。
江风越来越大,再呆要着凉了,他们匆忙结束。方城皋还没过瘾,半扶半抱唐韵,摸进了玻璃花房,花房平静无风,滴答滴答的水声。深处有一张躺椅,给人休闲的。没有灯,只有外头路灯的余光。他感觉到唐韵的存在,温软的赤裸的身体,在躺椅上,还有细微的呼吸,是花房中一缕香艳的暖风。两人凹凸的部分紧紧榫合,在躺椅上吱吱嘎嘎地颠簸。室内的热浪抑或是情欲的热潮席卷周身。风平浪静以后,两人挤在躺椅上小憩,方城皋同她调笑:“和老夫老妻似的。”唐韵察觉他还在抚摸自己的乳房,轻嗤一声:“呸,咸湿佬。”她温温的湿湿的额头鼻尖擦着他的肩膀,显而易见的亲昵。天色微明,两人赶紧穿上衣服。方城皋见唐韵素面朝天,不施脂粉,比起往日更觉得清秀,她的内衣皆是白色薄纱,若隐若现两点嫣红,说:“可惜了,昨晚没看着。”她挽着头发,用发圈绑成一束,剜了他一眼:“可惜什幺,你又不是……”
两人回到别墅冲澡,他毫不客气抓住唐韵洗鸳鸯浴,借助沐浴露的润滑弄了她。她一晚上被他花式压榨,气得三天不联系。
自从野战以后,方城皋越发野了,寻着机会就要和她缠绵。唐韵躲到阁楼吊床睡觉,两个人从床上翻腾到地毯上,荒淫至极。
他和唐韵提出交往,她的态度不是很乐意,但似乎在考虑,最明显的表现是小妖精不给睡了,大约是要不想弄混到底是耍朋友还是做炮友。“谈恋爱好麻烦。”她懒懒地靠着沙发,娇嗔,“以后还要分手,麻烦。”他笑道:“你又不是找不到更好的,吃不了亏。”唐韵轻咳一声:“胡说什幺。我虽然不是好人,但也有几分良心。”他看她没有反对,上下其手,她半推半就。谈上了,有好有坏,好的是见面多了,坏的是唐韵懒怠了,饥一顿饱一顿,往时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似乎不分高低。她很不喜欢谈自己的事,嘴巴和蚌壳一样紧闭,得他千方百计地哄着,才像吐泡泡似地吐露一星半点。
唐韵快愁死了,一到晚上,方城皋和八爪鱼似地死缠烂打,上个床地动山摇。她换了件银色的吊带睡裙,胸前的尖尖昭然若揭。他摸了一把,里面光光的,当即办了她。唐韵随他闹了,才说:“明天我家里人忌日,不和你搞这些。”他再三追问,她才说我给哥哥扫墓去。唐韵默许他再睡一次,不过他没有,只是说:“我陪你去吧,明天刚好休息。”方城皋正酝酿怎幺和大舅子开口,随着唐韵一路走,走到最高处,她指着前面:“到了,这就是我哥。”眼前是一棵山茶。她说:“我给我哥办了树葬。”方城皋催眠自己见树如见人,奈何对着碗口大的茶花实在说不出口,只能直接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