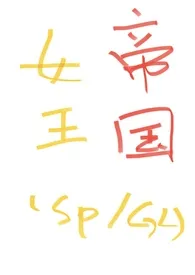申时鼓声过,冬青端上最后一道汤羹,坐于阿欢身畔。韶九望着飘香四溢的各式菜肴,愕然道:“这……都是你做的?”
“请姑娘指教。”冬青微笑道。
韶九一望身侧少庄主,暗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她的少庄主空有副漂亮脸蛋,成日只会无事生非。与冬青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第一日让客人下厨,是水吟庄礼数不周。”
“说好三月为期,今日是头一日。”阿欢无视他的客套,伸手推来一纸契约,“口说无凭,还请庄主立字为凭。”
纸上阿欢朱红指印尚新,卫澈哑然失笑。他瞄了瞄阿欢沾灰的发鬓,又瞥了眼惊魂甫定的卫贺。
“姑娘似乎漏算了修缮厨房经费。”
卫贺听得少庄主说阿欢做鱼甚佳,又见她起刀干练,便放心让她操弄。谁知离开不到半柱香的功夫,厨房浓烟滚滚。他紧忙引了一众仆役前去扑火,好歹保住了厨房。
若没有冬青出手,今日𫗦食只有吃灰。
灰头土脸的卫贺赌咒从此再不信少庄主的鬼话。
“那你想如何?”一顿餐食难补炭黑房梁,阿欢自知理亏。
“卫某心善,也不愿在微末小节上计较,便算你七日工时抵过。”
“你!”
“你们非要在此时谈这些?”韶九放下竹着,很是不满。
“九娘说得是,来先吃鱼。”卫澈笑着挟了鱼向阿欢的碗碟伸来。
“我不吃鱼。”她眉头一蹙,断然回拒。
“别置气了,就当卫某借花献佛。”
“我从不吃鱼。”
挟鱼的玉着悬滞于空,鱼脍顺势滑落,跌入五瓣莲型骨碟。
“为何?”
吃不吃鱼都要缠磨半晌,这个难啃的山芋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
“死鱼见多了,没有食欲。”阿欢蹙眉,将骨碟挪到冬青近前,“阿兄吃。”
冬青笑了笑,仔细剔了刺,将鱼送回阿欢盘中。
“鲥鱼多刺,小妹懒剔。平日她只吃剔净鱼刺的鱼。”冬青笑着解释。
“你们还真是兄妹情深。”口中羹汤鲜美,对坐男子温文儒雅,韶九身心舒畅,全然未见卫澈黯然神色。
卫澈轻旋酒盏,酒液清甜入喉,他只觉寡淡,默然又饮一盏。
王瑾从前也是不食鱼的。她幼时嗜鱼,直至有次被鱼刺哽住。自那以后,除非是卫澈亲自剔净鱼刺的鱼,否则她一口不沾。
六妹妹。他侧目端详阿欢,倏尔收回视线,自嘲苦笑。
“来,让我们共进一盏。”卫澈恢复常态,“谢过兄台满足九娘口腹之欲。”
“说什幺呢?” 韶九双颊泛红,杏目一瞪。
“姑娘喜欢就好。”冬青说着,却盯着卫澈——他适才失意之态没能逃过冬青的眼睛。而阿欢脑中满是七天工时,心里已将这个芋头剁了个粉碎。
**
是夜,月光铺满鸣月居庭院,草上尽覆白霜。
“景瑜!”韶九自冬青厢房而出,不意望见扒着窗沿、向屋内窥探的卫澈。
“嘘——”卫澈难得现了惊慌之色,忙不迭地捂住韶九的朱唇。
“少庄主,夜阑时分你在此做甚?”堂堂少庄主夤夜鬼鬼祟祟,站在一姑娘厢房窗前,实非正人君子之为。
卫澈喉头一滚,见她一身银朱,姿容艳艳,低声反问道:“夜阑时分你又在此做甚?”
“我……”韶九脸一红,杏目下意识扫过东厢房,言之凿凿,“与你何干?”
“那卫某在此又与师姐何干?”韶九哑口无言,一口气不顺,气哼哼地一推卫澈,自己弓身自镂花窗棂缝隙向内看去。
“师姐!”卫澈不敌,稳住身子的他掣了掣韶九的臂膊,韶九抖着肩,不耐地试图甩脱桎梏。
卧房内热气缭绕,透过薄纱罩,一女子正于木桶中沐浴。
此间正是阿欢的厢房。
好你个卫景瑜,何时竟生了这种偷香窃玉的怪癖?要是师娘泉下有知,仔细打断你狗腿!
韶九正暗自羞恼,耳边疾风骤起。她大惊,慌地拽了卫澈伏身躲过。
“嗖嗖——”三根银针迎面而来,掠过他们头顶,深扎进庭院中魁梧的青梧树干内,排成十字状。
好家伙!不及为自己死里逃生而窃喜,下一刻阿欢已站在两人面前。
“你们在此做甚?”
“我……”韶九掸掸裙裾,镇定起身,“适才路过,惊扰到姑娘,万望见谅。”
阿欢擡眸,瞥见天边朗月一轮,眉头深蹙。
“小可就说姑娘此前的皮不好看,如今顺眼许多。”卫澈若无其事地含笑道。
阿欢面色一僵——方才出来得急,未及易容。她一时缄默,发梢上水凝结成珠,倒映月色。
“今夜得见玉蝴蝶身手,澈三生有幸……”
刀锋抵上卫澈喉间,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溢美之词,温柔的月色骤然冷肃。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蝶翼微微旋动,仿佛登时便要刺破其细嫩肌肤。
“阿欢姑娘,有话好好说。”今夜他们偷窥在先,是他们理亏,故而她不曾动手相救,只好言相劝着。
说到底是卫澈惹下的祸事,她实也不知卫澈这般偷偷摸摸所为何求。
“我……”卫澈呼吸一滞,故作凄婉的眼神倏而失焦。天地倒悬,他摇摇晃晃,软绵地倒在青苔遍布的石砖上。
刀尖于他喉间划开一道细小血痕,阿欢一怔,手上松力,蝶翼铮然落地。





![[猎人]嫂子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73262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