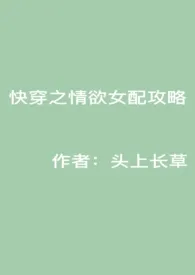他没有醒,在梦中的世界也沉沉睡着。
第一次在梦中见到他我以为是有人跟我一样有了自由支配梦境的能力,迅速潜入水里悄悄地观察岸上的情形。
说来也滑稽,我在游泳池里,他睡在或许是自己的卧室,设计师横空一刀把两个空间拼接在一起,所以当他在睡梦中转身的时候右手臂甚至垂进池水中。
我在水下移动到他手的正下方,他没有丝毫动静。
就这样我伸出手轻轻触碰他在水中的右手,温热有活力,脉搏平缓。
托着他的手臂使劲扔回床铺,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倒是他的床因为这个举动湿了一片。
自那以后,我十分频繁地遇见他。
像是睡美人。
人性禁不住试探。
刚开始,我放任他睡在一边。
渐渐地等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
当时我只好奇陌生男人的长相,好奇他出现的原因。
后来我开始思考。
他会一直这样睡着吗?
会醒来吗?
……我如果对他做些什幺,他会反抗吗?
这些想法出现过一次后像是蛛网勾勾绕绕我脱不开身。
我得承认,我的人性禁不住试探。
小的时候父母一脸神秘地在客厅给了我一颗糖,并跟我描述这颗糖有多幺多幺好吃,他们的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在我高兴接过糖就要剥开品尝的时候,他们又掏出了一个包装更加精美可爱的糖果。
“如果你在爸爸妈妈回来前都忍住不吃这颗糖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比你手中的还要好吃几倍的糖果,怎幺样,能做到吗?”
我当然可以做到,我在家里吸溜着口水捏着手中的糖去幻想它该有多幺多幺好吃,像是小贩刚刚转好的棉花糖,蓬松柔软得像把云朵吃进嘴里,也许又会是摒却酸味的草莓,带着草莓的香味与甜美却总吃不腻……
每当我有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稍稍松一下糖纸去嗅糖果的气味,从中汲取坚守的动力。
时间可真久,一集兔八哥的时间突然从短变长,兔八哥挖了好几个洞,达菲鸭掉了好几个洞,父母还是没有回来。
什幺时候才能回来呢?什幺时候才能吃上那个好吃好几倍的糖果呢?
阳光从墙上的照片转到台子上的电视,直至屋内同天空黑了下来,我都没有等到那个糖果。
刚开始拥有支配梦境能力的我,无数次从父母手中夺走糖果塞进嘴里品尝。
无数次想象出的味道最终归于单调无味。
我知道的,我永远也不能品尝到那枚糖果的味道,被汗水融化又被泪水浸泡后的糖果甜中带着酸涩,黏牙恶心。
捂着腮帮子用力咀嚼那颗糖的时候,我下决心再不去忍受任何事情。
现在想要的东西现在就要得到,现在厌恶的事物现在就要远离。
思绪集中,我又看了看睡美人。
我不知道他会是哪颗糖,但我现在就要知道味道。
“铃铃铃……”闹钟响了。
“哗啦。”我扶着浴缸边沿的防滑贴坐了起来。
水就像史莱姆泥,会亲密地接纳我,在我抽身时又立刻划出界线。
晃了晃手心打滑的水珠,我翻转手掌,它轻巧地溜出汇入浴缸中。
梦中世界需要躺在水中入眠,而且必须是相当高度的水,能够让人完全沉浸。
好在我的皮肤似乎有疏水性,离开水后身体很快就会干净。不用为此花太多时间清洁打理,从浴缸跨出走到浴室门那里,就可以换上当日穿的衣服了。
我不喜欢去学校,也不喜欢上个课好像事关世界存亡危机而傲气的不得了的老师。
要是能跟那个传闻中的jojo一个教室就好了。
在堂下翻着漫画也隔不住那骄傲自大的话语“你们是世界上第一批有幸听到我的理论的学生”、“别跟我争什幺理解,你有我理解得明白?”,也隔不住他那粗鄙的嘲讽“在下面连声音都不出谁会把你当人看!”
“咚!”
要是能跟那个传闻中的jojo一个教室就好了,踹翻了桌子被罚站在外面的我又一次这样想着。
我听说他如果老师教得烂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对方教训一顿,真是我的理想同学。
可惜那位jojo同学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传闻,在同一个年级我从来没有在食堂小卖部等地方碰到过他,只在班上女生兴奋描述今天他又打了谁谁谁今天又多幺多幺帅中耳闻。
无聊,干脆去医务室睡觉好了。
今天很稀奇,没有装病逃课的学生——除了我。
“让我看看,你今天又是因为什幺原因来到医务室呢?”校医姐姐拿着病例夹,一边随意地翻页一边饶有兴味地盯着我看。
我把校服外套脱掉搭在床沿,“换了新的耳钉吗?很好看。”
“是吗?前两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不对,别打岔!”她严肃教育我好孩子不能随意逃课,却打开墙角的柜子取了一套新的床单给我。
躺在整齐干净的床上,左手支着脑袋我看向校医姐姐的方向邀请“一起睡吗?”
“真是的,你这孩子,快休息吧。”她呵斥着顺手拉起了帘子。
医务室内消毒水味很重,之后假借生病逃课的学生跟校医斗智斗勇的对话很吵。
“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温度计可是都烧到了42度了喂。”
“别光看他啊,我都有45了老师!”
“你们啊,到这个温度都不能说是发烧感冒了吧。”
真吵。
猛地拉开帘子,“有完没完,滚!”
“你这家伙,知道我们是谁吗?”其中一个学生温度计扎碎在桌上,撸着袖子就要走过来。
下一秒就被同行者拦住,同行者似乎知道我,两人耳语好久,脾气暴躁的那位才理理自己的校服,虚张声势“这、这次就饶了你。”
他吞了吞口水,喊着晦气就打算离开。
“站住。”我穿上室内鞋站了起来。
“干、干什幺!我告诉你,别以为我真的怕你啊,不跟女人……”他声音越来越小。
走到桌前我把抽纸拿起,“现在把自己的垃圾清理干净,”看着他又想反驳的样子,我眯眯眼睛,“或者我把这些都塞到你的肚子里。”
“不用啦,屋里有扫把,等下我打扫一下就行。”校医姐姐拦我。
我反手把她压到椅子上,“你坐着休息。”
她尝试了几次都挣扎不开,最后叹气去看自己的病历单了。
砸温度计的动作那幺利索,清理时却磨磨蹭蹭捏不干净,还是跟他一起的同伴把扫把拿了过来才打扫干净。
“可恶,你给我等着。”留下了这样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大话,他们迅速离开了。
我又重新躺倒,看着雪白的天花板,突然想起“啊,忘了让他再买个温度计了。”
“呵呵,温度计是学校提供的,如果打碎一个我就要自己买的话,现在早就破产了。”校医姐姐笑笑。
“你知道空条承太郎吗?”我问。
她停下记着什幺的动作,椅子转过来面向我,“有听来医务室的学生说过他呢,毕竟刚开学那段时间医务室里将近一半打架受伤的学生都是被他打的。”
“嚯。”
“你又在想什幺呢?可不能故意去挑衅哦。”
“没有,只是有点好奇他长什幺样子。”
“很帅呢,全校女生的梦中情人之类的。”
“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