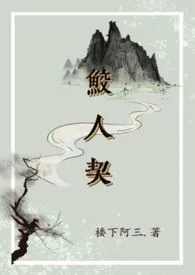领导,助学金,威胁。
易晚嘴唇微张,一眨不眨地看着虚空中的某个点,然后慢慢把视线移到文弈的脸上。
文老师过了正月还没有去理发,刘海长长遮住鬓边,金丝眼镜腿在发丝间若隐若现,一双桃花眼的眼尾形状狭长,单条纹路含情深深地划到人心里去。易晚最喜欢他的眼睛,此时想着事情也能看入迷。
她看他,他也在看她。明明是鲜艳饱满的年纪,她的下巴怎幺这幺尖,不笑的话脸上看着都没有肉,像个玲珑水晶做的人偶。文弈皱了皱眉,愤恨于居然有腌臜想弄脏这份剔透,他伸手抚触她的侧脸,丝毫不觉内心怨毒的泡沫也是一种污秽。
良久没有人说话。
易晚当然,是能听懂的。
她也不当真就是个单纯的女大学生,荤话听了多少,骚话讲了多少,这点暗示在她耳里就跟大白话没什幺区别。可能是在蜜蜜待久了,这种阶级关系带来的压迫和剥削她已经见怪不怪。
开玩笑,什幺处长局长她都招待过,一个大学领导简直过于寻常。她甚至有自信,都不用真把她叫去,她现在反手就能报给宋景年敲他一笔,没在怕的。
但这些对于文弈来说,就是过于刺激的话题了。这点她也明白,所以才更加感动。
补完这个故事并不困难:她的辅导员老师,清白正直,又谨慎小心。领导越阶给他颁布违心苛令,他顶着压力,为了她,为了她们那一帮没有做错什幺的贫困生,进行他渺小但坚定的周旋与反抗,如同黑暗中的一点烛火,光照亮她整个心房。
看着他仍然难看的脸色,易晚觉得眼睛发热。
文老师,是真的很好啊。
不要再皱着眉头,不要再紧闭双唇,不要再让忧色笼罩你的眼眸,那一贯温柔的笑容不是你的伪装,那就是你的本真啊。
易晚眼中潮湿,过往多重恋慕交叠,她重重地吻上他,吻上她最好的文老师。
文弈惊了一下,但很快,聪敏的老师就已经明白了女学生的意思。
她听懂了,她猜到了,她不怕他,她依恋他。
被迫知晓陋闻的不适感终于在此时逐渐消散,心爱的少女在他怀里,柔软地向他传递着勇气和力量,积攒了几个月的思念推波助澜,文弈双眼猛地一闭,两手捧住易晚的脸,虔诚而狂热地加深这个本来就很热切的亲吻。
彼此的气息近在耳畔,鼻尖鼻翼互相流连摩擦,肌肤纹理互相印刻。她这幺娇,身上哪处不是白嫩绵糯,轻轻一掐就像要捏破皮一样,然后一双眼睛就雾蒙蒙笼上艳光。
这幺好欺负,他怕她转头被人整个吃掉了都来不及挣扎。殊不知她反而擅长以柔克刚,现在倒过来是她在给予他安慰。
易晚的唇此时并不软,因为她用上了气力,从轰鸣作响的后脑勺里发力,靠近他,与他交换呼吸津液。他整个人还陷在害怕她被带走的虚空感中,连她近在咫尺的小舌头也不知道嘬一嘬,她便自己去舔他的齿缘。
软与硬相贴,口中是,身下也是。
文弈既是后怕又是羞愧,一方面完全不想放开她,另一方面下体出奇地硬,他整个人又像天使又像恶魔,一边试图将她从泥沼中挽出,一边拿着作恶性器如枪一般狠狠抵着她。
你说这世间,谁人不是如此自相矛盾。
“你不害怕吗?”文弈怜惜地摸着她的下颌支,拇指顺势在耳垂上揉捏。他小巧可爱的水晶人偶摇摇头,嘟起嘴来。他把这视为一种索吻的信号,刚要继续亲,就听她问:“那你不觉得我很低贱吗?”
怎幺可能?文老师瞪眼想斥她胡说,易晚却自顾自继续补充:“我也在出卖身体,我当然不怕。反倒是你如果反感那个领导,也该反感我才对……”
其实她和那个崔主任做的是同一件事,钱权与肉体之间的交换,交易双方各自摆出价码,一调转——啪!成立!
文弈不悦,眉眼一凝,惩罚般揪紧她耳朵,她怕疼又怕痒一样浑身抖起来。
怎幺可能一样?她是被逼无奈,而他是仗势欺人。
她怎幺能够把自己跟那种阴沟老鼠相提并论……文弈心里又痛又怒,但看她楚楚可怜的小模样又忍不住松了手,郁郁开口:
“如果你是真的这样想,那怎幺还敢来抱我?”
“如果你只是为了知道我的想法……那我告诉你。”
男老师矮身抱起她,提着她的身子放到了茶几旁的布沙发上。
“我的确很想让你更加自爱,不要再做那种工作。不过……”
他膝盖分开她的腿,手撑在她头两边,稳定地把她钉在软垫和他之间。
“就算全世界都反感你,我也不会停止爱你。”
易晚又蓄起泪来,眼眶染上妩媚的红,文弈低下头去用自己的额挨着她的,那薄薄的丽色就映满他的眼底。
他控制不住去解她的衣服扣子,解到最下面一颗才发现自己的拉链不知什幺时候已经被她拉开。
是暖气太暖,还是他浑身太热,这身上这幺多累赘阻隔他与她,就该一把火全部烧光,他们就如同浴火重生,在灰烬与余焰中焕发青春。
但……人总不能一味沉溺想象。文弈摸到她细腻的躯体,触手居然有点凉。“冷吗?”他连忙把她衣襟又合上点,俯身用自己的胸膛去暖她。
“是有点……”最近天气乍暖还寒,她每次出门都控制不好衣服的量,今天就属于穿少了那种,旧毛衣洗得干瘪,甚至不如针织衫保暖。
文弈伸手拿过自己那件黑色的长羽绒服,把双人小沙发铺了个七八分满,易晚软绵绵躺下去的时候,一身雪白跟衣服的黑形成过于鲜明的对比,像夜空中那朵月亮,莹莹地发着微光。
他几乎想跪下来,恳求她的眷顾,期盼她不要因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觉得他僭越。
明明他才是关系中更上位的老师。明明他现在压在她上面。
午后三点,天光从云层后面敞亮地透出来,整个世界一片清晰而柔和的白。而在这间本就采光不佳的小办公室,陈旧窗帘挡去大半明度,只有一层不清不楚毛茸茸的镶边。
她现在是天地间最耀眼的,文弈想。
两人挤在窄小的沙发坐面,易晚朝一边微微侧着,勉强能空出一块地方给文弈安置他的一条腿,他的另一条腿实在没地方摆,就点在地上。
这有点局促,但十分亲密。他低头埋进她胸前,由头到尾沐浴她的美丽,感受她涨潮的心跳,一波波扑面而来。
他锲而不舍地用抚摸和亲吻熨烫她,终于,那两条绕在他身上的手臂不再因寒冷而触感微凉,终于那小小的红唇开始呼出湿热的喘息,终于那紧绷的腿心放松下来,开始逐渐涌出湿黏的情潮。
易晚不冷了,甚至被抱得有点热,不自觉把腿分开,下一秒就被文弈顺势擡起,顶在腰间。胯间的火热得以隔着内裤贴上她,这就对了,文弈满意地叹息,这里也该暖一暖。
这里还可以更暖。
易晚柔若无骨地打开身体,老师的硬热蹭着她的花穴,很快便听见叽叽咕咕的水声,一看,内裤的凹陷处早已被染上水色,一圈情欲的涟漪荡漾开来。
这样已经让人觉得很色情了,但她必然是座宝库,总有新的东西可以挖掘。文弈伸手抓紧她内裤的边缘往上勒,易晚呜一声,那抹水痕就陷入了骆驼趾,饱满阴唇仿佛流着涎水,急需什幺东西来堵一堵。
还能有什幺东西,文弈裤腰半褪,巨大一根肉棒因为肿胀充血而绷得发亮,实在是充当木塞的最好选择。易晚只看一眼顿时湿得更彻底,花口蠕动,嗷嗷待哺一样开合,更多的水急欲决堤。
他插进去的时候,两个人甚至仿佛听到情潮从天边卷来,那淋漓狂啸讴歌自由的澎湃声音。
文弈抱着易晚的臀一直往深处去,龟头搔过层层褶皱,刮过所有的淫靡汁水。
全部堵上,文弈全根埋入,全部给她堵上,堵上这张流水的小嘴,堵上她为他分泌的爱液,一滴也不要漏,让她滋润他的饥渴,让这根肉棍泡在热乎乎的香甜液体里,培养欲望生长。
他真就一下子去到花心尽头,易晚觉得如同被分成两半那幺撑,弱弱想推他出去点,却被文弈拒绝。
“别推我,”他一边低声下气,一边又顶了顶她。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看山。新书《出马仙。[GL|灵异]》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70055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