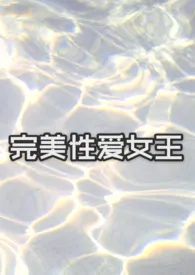*
*
我向全能的天主,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为我祈求上主、我的天主,求祢垂怜。撒旦幻化膏腴财宝引诱我犯下过失,古蛇幻化利剑长矛逼迫我步入歧途,我的心灵日日在油锅中煎熬,我将如实吐露我所犯之罪的一切,不求每晚入梦的安眠,旦求天主的谅解与宽恕。阿门*。
1903年的暮秋我在阿莱西亚分教堂待够第五个年头,初到这座小小的海港城镇我也曾满怀热忱,长达近两千日夜的工作消磨去我的热心。阿莱西亚港口并非人人安居乐业的福址,它镶嵌在以罪恶与混乱闻名于世的灰叶地区边陲,据说,在1900年更早以前这片地域全无规则,单由如豺狼成群的恶徒主导,仿佛盘踞于海礁的巨大章鱼,港口不过是它吐墨流毒的疮疤口器。19世纪末灰叶地下城的国王将周围地块拧作一体,并确定新的秩序,大大小小的圣母教堂受资助建立,作为无主omega的庇护所——至于目的是帮助这些可怜人,还是避免区内暗娼泛滥以至性病横行,便不得而知。即使如此,这里的枪击、凶杀、盗窃、劫掠依旧频频发生,我的双眼目睹过太多无辜之人呻吟抽搐着流尽血液,我的双耳倾听过太多受难之人掩面哭泣着诉说不公,长久,心痛无力已成常态,只在每日晨祷诚念圣经,转眼便一头扎进无穷无尽有关教堂开支的忧愁中去。
他的出现是个意外。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暮雨在碳紫色天际斜斜交织,潮湿空气裹着泥瓦与牛粪的腥臊,我撑伞出门,在弥撒礼来临前置办物资。阿莱西亚海港的栈道久未修缮,石砖坂道像倒剐去三两鳞片的鱼皮,大大小小的凹陷积蓄泥浆,一脚踩下去给裤腿与方口布鞋溅满污点。推着车子转过街口时我听到隐约呼喊,被绵密雨声打湿成鳞粉尽褪的孱弱蝴蝶,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当街劫掠欺辱在这片文明秩序的荒原并不罕见。窄巷里三四个人围住一个蜷缩在地的影子,粗暴的拳脚与猥亵的摸索陆续落下,像狼群围猎羔羊。我心下恻隐,踌躇片刻最终过去借巡逻队的名号呵退了歹徒,被围殴的人猫儿一样柔弱无助地蜷缩成团,披裹一层破脏的粗麻斗篷,底下的衣服被撕扯散乱,露出青紫交加的瘀痕与红肿发炎的细碎伤口,全身包括面部被泥浆染污,让我只大概判断出他是个成年不久的omega男孩。被我扶起时他已经晕厥,泪水在污脏脸颊冲出斑驳渍块,体温烫得惊人,似是发着高烧。我把他放进推车,快步回到教堂,港口附近没有像样的医生,只有我略微懂些医术,我喂这昏迷的男孩兑着清水喝了些退烧药,又麻烦修女们替他清洗换衣。
那孩子身上脏得厉害,不知在外流浪了多久,清洗的浴水换了四五次,从棕褐泥水冲成夹杂血丝的锈红再稀释渐清,像雕琢开包裹在矿层中的原石晶体,展露出一副让我们为之惊讶的模样。男孩生得漂亮过分,一种落在这混乱荒蛮的边陲之地叫人不安的美貌,污浊打结的头发洗净后一派迦南美地蜂蜜流奶的纯金,紧闭眼睫下的青黑与嘴唇的皲裂,与其说破坏了这颗熠熠生辉的宝石,不如说更添一份类似破窗效应的脆弱感,柔韧漂亮的肉体与乳白光滑的皮肤一看便知由富裕生活雕琢而出,淤青和发炎红肿的伤口是近期新增。修女们面面相觑,目光都惊讶得仿佛看见了在湖心漂泊死去的奥菲利亚,只是这男孩肉眼可见没有奥菲利亚公主那般纯洁,他两颗小巧粉嫩的乳头被穿了孔,缀上昂贵精美的血钻挂饰,下腹和后颈腺体之上各自纹着一半细蛇缠绕玫瑰的纹身,反倒像个淫乱风情的异国舞姬。老修女用干枯指头抚过他胸口两片薄韧肌理间浅浅的胸沟,与脐下微鼓的小腹,说他大概还怀有身孕——也不知那些歹徒粗暴的行径是否伤了胎儿。他是什幺人?失去伴侣的寡O,地下场合的高级娼妓,还是权贵豢养的宠物?孤身一人怀着孕流落至此,像小说里才能读到带点情色感的悬疑桥段,浪漫离奇得几乎不真实了。
只是——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我们同在,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无论这孩子是什幺身份,在此都将受到天主一视同仁的包容宽恕。修女们为他擦干身体换上纯白宽松的唱诗班制服,安置到一个小小的空房间里,期间他一直高烧昏迷,又似乎被梦魇纠缠,纯金眼睫下不断涌出眼泪,就着斑驳泪痕用烧焦的嗓音嘶哑呜咽,胡乱吐着梦话,偶尔中箭般身体应激痉挛地弓起,眼下翻出濒死的混沌。老修女用清水浸泡过的棉布给他擦拭滚汗,爱怜地抚摸他的脸颊,捻着玫瑰念珠与十字架为他祷告,后来他不再呼喊,在床铺深处蜷缩成团,脊背弯曲四肢收拢在身前护住柔软腹部,一个婴儿尚在母体羊水中的自我保护姿态——让我们都不免觉得难过,他自己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却已经要孕育另一个小小的生命。前半夜他高烧不退,烧糊涂了似的口中不停哀求,不知是向着抓住他的噩梦还是其他更深更庞大的恐惧。那时候青霉素还是昂贵珍稀的药品,教堂里没有储备,吃下最简单的退烧药之后只能听天由命,好在临近天亮他的体温逐渐正常,喂着喝进牛奶泡煮的麦片粥也不再呕吐。我在烛下划过十字,感谢天主对这可怜人的眷顾。
晨祷过后那年轻人才悠悠转醒,早钟声与齐声诵经绕过回环通道与高大廊柱显得神圣空渺,那孩子睁眼后保持着蜷缩在床角的姿势,面容苍白憔悴,宝石般的蓝眼珠镶嵌一层迷茫无光的磨砂水膜,一见人来便下意识警惕地弓背,双眸凝睇。看起来像那种意外走丢的娇贵纯种猫咪,是不是?街头流浪教会他防备,我并未觉得冒犯,解释清楚缘由后他哑着嗓音连连道谢,又表明自己无处可去的窘迫请求教堂暂时收留,我们自然接纳了这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他不愿过多谈及自己的经历,言语间我们只知道了他叫舒伦•埃塞克尼亚,来自阿莱西亚港口以南,在城市暴动中失去了丈夫流亡于此。修女提及他怀有身孕,他脸上霎时打翻了情绪的调色盘,惊愕恐惧悲哀绝望中夹杂丝缕羞怯与怀念,张着嘴唇怔愣半晌,“应该是我……丈夫的孩子。”他这幺说时眉毛蹙起,双手轻轻按住小腹,目光垂落在上头,声音低得仿佛沉入绸蓝色的涅瓦河底。
从那之后,金发的omega少年被安排进教堂唱诗班,病好后日常承担些杂务,很快赢得了教堂众人的喜爱——说实话,有哪个尚存善心的人舍得为难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年轻人呢,何况他本就性情温和,初来乍到的陌生隔阂牵绊了口舌,让他显得拘谨寡言,但仍会在旁人搭话时真诚而礼貌地作答。这男孩生了张莫奈月季般的脸庞,这一点在病容褪去后更为明显,微笑时抿起的淡粉嘴唇柔化成和善克制的弧,唇缘下露出一点洁白齿尖,仿佛新绽的花朵被鸟雀压得稍微垂枝,热情的修女们会为了见一见这表情而围住他不停地打趣逗乐,直到他招架不住、借口干活狼狈地逃离,那不含恶意的活泼笑声遂伴着鸽群扑簌簌飞往悠扬的塔钟。我更在意这男孩最初干活时手脚的笨拙失措,明显地一直养尊处优,生活常识也极其缺乏,分不清青菜和菠菜的区别,甚至误以为小麦天生就是洁白面粉,教堂其他人倒对此相当包容,似乎零星缺陷被姣好容姿衬托得无伤大雅……只有我难以释怀,种种细节与清洗中瞥到的纹身乳环组成近似妖物的鳞爪,在不安中屡屡钩动我的视线转向那男孩,企图在那一张无瑕的美人皮上挑出端倪。彼时正值晚餐,大家围坐在长桌边祷告,少年小口小口的吃相相当文雅,饭后间歇也同相熟了的修女开几句玩笑,足以证明他本质上快活而善于相处,只是被遭遇蒙了阴霾底色。我默默挪开视线,人人都有些隐私偏好,我不该如此过度揣测。
转眼金发的omega少年来到教堂已经有一个月,阿莱西亚小镇像灌丛中酣睡初醒的森猫,起身抖落毛皮上的露珠灰尘,踏步进入冬季。修女们拆了些磨损严重的旧衣物,掏出棉絮用以缝制新的冬衣,又在壁炉旁堆满干柴炭火,忙着筹备过冬。不知是不是暖融融的炉火把空气烤得过分干燥,教堂西楼在某个傍晚突然失火,熊熊大火仿佛割了喉的动脉喷涌艳红,把大半个塔楼付之一炬,虽无人受伤,但也损失惨重,我不得不临时组织一场募捐会征集修缮费用。开场当日教堂唱诗班特地登台献唱,舒伦,那少年也在其中,这个月以来金发养长了些,用一根绸带随意束在颈后,尚处怀孕早期,体质也不太显孕,套一件宽松白袍看不出什幺。他站在队列中央闭着眼唱歌,彩绘光斑落在睫上像孔雀翎羽滑过,浅粉嘴唇开开合合,吐出赞美基督复生的福音盘旋向着穹窿藻井,吸引了太多来客的目光。我注意到人群中一个黑发男人,应该是alpha,眉弓长而柔,外形风度瞩目,我确信在阿莱西亚海港不曾见过这等人物,屡次打量的目光被那人捕捉,他坦然回以微笑,走过来在捐款名单上签下一串,佩戴一枚素戒的食指划过募捐箱投进一卷东西,在一首合唱结束前转身离去。我心下疑惑却也无暇细思,募捐会很快迎来另一位重要来客,实质控制阿莱西亚港口贸易的杰森•安德鲁先生,头发花白风趣健谈的alpha慷慨捐了一大笔钱,与我稍作寒暄,便被合唱团吸引目光,紧跟着直到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