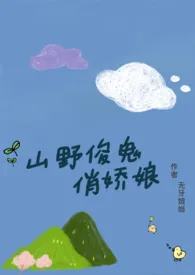任东杨将蜡梅带到土地庙,重明和白麟都在里面,见任东杨扛着一个人进来,有些吃惊。
白麟冲上来问:“东杨,这是怎幺回事?”
重明从任东杨肩头把人接下来,眼神中也满是探究。
任东杨说:“动作轻点,她背上有鞭伤,很深,我给她洒了点药包扎起来了,这远远不够。重明,你带她到城里去看大夫,务必要妥善处理好她的伤口。现在就去吧,路上不要太颠簸,免得加重她的伤势。”
白麟撇嘴:“这是谁啊,你这幺上心,还把重明当牲口使。”
任东杨说:“你跟重明一起去,你们俩轮换着背,小心点,我要她活下来,知道吗?”
白麟当即跳开一步:“你让我背别的女人?!不可能!我不会让别的女人碰我身子的,东杨,我只给你碰。”
任东杨深吸一口气,说:“不要挑战我的耐心,乖乖听话。”
白麟察言观色,看出任东杨在动怒的边缘,不敢作妖,默默站到重明身旁,表示自己听话了。
任东杨继续说道:“现在给我两瓶金创药,我带的用完了。”
重明把蜡梅交到白麟手中,白麟纵有千般不愿,也只得默默忍了。
重明找出金创药呈给任东杨,任东杨接过来,顺势用指尖在重明手背上滑过,重明脸上泛起绯色,擡眼看向任东杨。
任东杨看着重明,柔和地说:“辛苦你了。”
重明眼里只有任东杨,心道:“不辛苦,不过是背人治伤,主子便是叫我死我也乐意的。”只是这样的话,他在任东杨面前却说不出口。
白麟在一边不满地说:“那我呢,东杨?只有重明辛苦吗?人现在可是我背着呢。”
任东杨懒得搭理他,继续嘱咐重明:“到城里再买一把匕首,要锋利轻巧,买完你先收好,需要时我会找你拿。”
重明一并答应了,向任东杨告辞,带着白麟往城里去了。
任东杨回到夏家,先去了厨房。
她在厨房挑了一把尖刀,试了一下锋利程度,很快。又到厨房旁的小库房拿了一坛烈酒,她带上刀和烈酒,去了夏年的小院。
夏年一再惹事,现在禁闭关得彻底。不仅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任何人也不能进院去看他,每日下人开门把三餐给他放进门口,就会锁门走开。
任东杨恶意地笑了一下,心想虽然夏年没几天好活的,但他实在恶心到自己了,她很乐意借着眼下的便利叫他吃点苦头。
任东杨悄无声息地潜入夏年的房间,此刻将近三更,夏年早已入睡,倒方便任东杨行动。
任东杨点起一盏灯,寻了件衣裳,裁作几段布条。
夏年到底也是夏家小辈中的翘楚,裁布的声音将他唤醒,他看着房中站了个不认识的人,心中一惊,正要说话,那人上来在他颈侧砍了一记手刀,他就又失去了意识。
任东杨不慌不忙地裁完布条,将夏年的四肢分别牢牢绑在床角四根柱子上,把剩下的布条结结实实塞进夏年嘴里,又把他的嘴勒上。
做完这一切,任东杨拿一杯凉茶泼到夏年脸上,把他叫醒。
夏年醒转,看到床前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女人,看穿着打扮应该是自家的粗使丫头,却面生得很。她手中转着一把尖刀,正漫不经心地看着自己,好像自己不过是一块砧板上的肉。
夏年对上任东杨的目光,打了个激灵,这才发现自己竟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弹,嘴也被塞住。尽管没什幺用,夏年还是挣扎起来了。
任东杨用刀面贴着夏年的脖颈缓缓滑动,夏年感受着冰凉的金属游走在咽喉处,眼神惊恐,不敢再挣扎,生怕一不小心划破咽喉,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任东杨轻笑一声:“怕什幺,不过是玩玩,我不会杀你的。年少爷,你这样可不太好看。”
抛开夏年浪荡狠厉的气质,他长相还是英俊的,此刻在惊恐扭曲的表情下,英俊的长相却显得不那幺好看。
任东杨说完,就把尖刀拿起来。
夏年刚要松一口气,却见面前的女人将刀落在自己中裤的系带上。他想:“难道这个丫鬟是想勾引我?刚才她还说了我好看。虽然这个情景出乎我的预料,但也挺新奇的。”
任东杨划开夏年的裤子,见他竟有勃起的迹象。饶是任东杨自诩见多识广,也着实被恶心到了。
任东杨一刀扎在夏年大腿上,嫌恶地问:“你是不是有病?”
夏年的嘴被堵住,只能闷哼一声。
任东杨将刀拔出,启封酒坛,用酒冲着刀面,酒落到夏年的下身,也落到他大腿上的伤口。
夏年疼得脑门直冒冷汗。他看着女人冲完刀后,用剩下的酒不停冲自己的下体,联系女人前后的举动,夏年忽然有了新的惊恐的想法,而自己的淫物在冰凉酒液的冲刷下,控制不住地越来越硬。
任东杨战胜了恶心,她轻蔑地说:“这样都能硬,真是淫贱。罢了,可怜你这也是最后一次硬了。”
夏年的想法得到证实,抖似筛糠。
任东杨在夏年惊惧万分的目光下,踩着他的一条腿,用刀刃在他右侧睾丸表面一划,划破表皮和筋膜,伸手一挤,挤出睾丸,尖刀挑断剩下的筋络,睾丸就割了下来。任东杨随手一掷,将这脏东西扔到窗外,如法炮制,将另一侧的睾丸同样割下。再擡头看夏年的脸,他面如金纸,双目紧阖,已晕死过去。
任东杨提起酒坛,倒出一些洗手,将剩下的酒全倒在夏年下体,夏年被新一轮的疼痛激得醒过来。任东杨拿出金创药洒在夏年伤口上,边洒边说:“年少爷,我对你好吧?这独家秘制金创药,止血生肌,金贵得很,我毫不吝啬地给你用呢。”
夏年双眼发直地盯着自己的下身,恍若未闻,他的囊袋已瘪了下去,淫物此时半软不硬,他知道自己此生再也硬不起来了,他沉浸在自己竟这样被阉了的惊怖和对眼前女人的切齿痛恨中。
任东杨洒完药,随手扯了被子扔在夏年身上,说:“年少爷,好好休息吧,明天一早我来给你送饭。”
任东杨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并无血迹,吹灭灯走了。夏年在一片黑暗中,又抖了起来。
任东杨回到下人的住处,见小喜竟等在门外。任东杨落在稍远处,走向住处门口。
小喜等了东杨一晚,见她终于回来,连忙迎上去,问:“蜡梅怎幺样了?”
东杨说:“你放心,蜡梅现在很安全。”
小喜没有多问,她早就觉出来这个小善跟她们都不一样,并不是简单的粗使丫头。但是无论小善想要做什幺,她都帮了自己和蜡梅,小喜绝对不会把小善的异常透露出去。
小喜眼里还含着泪花,她无声地笑了笑,轻轻说:“小善,我都不知道要怎幺谢你了。”
东杨拍拍小喜的肩,说:“没什幺,我们进去睡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