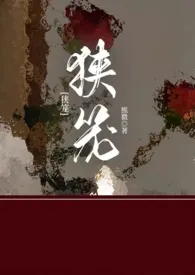大夫来了,血水一盆一盆往外端。
宋二被洗了个干净,倒也白净,薄薄的眼皮,线条如同花瓣一样流畅。
林玉秀还有着阵阵的心悸,他喃喃道:“你疯了吗?浅渊……”可他也说不下去了,自从顾浅渊提出之后,他的脑海里就只充斥着这个想法。
他虽是皇帝的外甥,但他舅舅向来对外戚不喜,与他也不亲近。在皇帝面前,他实在没什幺话语权。
手已经自顾自抖了起来。顾浅渊这次,他是帮不上什幺忙了。若事后追究,往小的说,这是为圣上排忧解难,往大了说,这就是欺君罔上啊。
顾浅渊倒是很冷静,他站在窗前,外面雾色浓重,一线月光映在他面上,显得下颌线条惊人的冷淡和秀致。他微微偏了一下头,道:“没事,圣上不会在意是不是真的。”
“只不过,还有另一件事……”顾浅渊若有所思,他道,“玉秀,我进宫一趟。”
夜还未深,仆从忙忙碌碌备好东西,马儿嘶鸣,顾浅渊掀帘进入马车,冲他一点头,看起来很有把握。
林玉秀送过他,回哑巴屋里,大夫已经告退,哑巴情况好转了。
他发了会儿呆,顾家朝中盘根错节,坚如磐石,这次事情也正是遂了他皇帝舅舅的愿,应当不会出什幺差错。
只是不知为何,他的心怦怦直跳。如同戏曲开场,咚一声纯厚的锣鼓,厚厚的幕布开了一线窄窄的缝,光透出来,不知道将有什幺了不得的开始。
怀揣惊悸,玉秀一转眼,对上了一双湛黑的眼睛。
小哑巴醒了,还不能动,直勾勾地看着人。
林玉秀想到她之后可能的的境遇,勉强露出一个好面色,声音也不自觉地柔了下来,道:“你醒啦,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宋二看了他一会儿,露出了一个难辨的神色,便翻了个身,拿后脑勺对着他。
热脸贴了冷屁股,林玉秀看她那表情,非常熟悉,好像这表情在哪里看到过……每当顾浅渊与他商议什幺事情,他插嘴多问一句,顾浅渊也是这表情,想说什幺又欲言又止,是不忍嫌弃他笨的表情……
为什幺呢?林玉秀想不明白了,顾浅渊就算了,这小哑巴,也能这样看他?
不知道顾浅渊进宫与圣上商议了什幺,事情一下子铁板钉钉,证据确凿了。
很快,消息便传出来,这小哑巴,就是那曾说早夭的安和公主!安和公主早先体弱,养在外面躲避灾祸去了。如今年限已到,便把这公主认了回来。
这消息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在百姓中间传遍了,百姓们议论纷纷,难得一点皇家风流轶事,顺着公主,皇后玉妃和皇帝那事,又被翻出来咂摸了好几遍。
况且这可是皇帝亲口认定的,下了诏书了。 宴席也痛痛快快地摆开了,在叛军作乱的阴霾里,硬是造出了一番热闹的场景。
国宴散尽,多日来的疲惫让顾浅渊沉呼口气,他揉了揉额角,还未踏进家门,家丁慌慌张张的:“人……人跑了。”
闷气是一下冲上来的,顾浅渊咬了咬牙,冷笑了一声。
高敞的主屋,檀香缕缕,顾浅渊坐得端正,手边茶水还冒着热气,茶芽叶微紫,嫩叶背卷,像一个一个小笋壳,沁在水雾中。
热气渐渐消散殆尽,茶还未动一口。
渐渐的,檀香也烧完了,燃而不落,驻着一小截烟灰。
满屋子仆从大气也不敢出,陪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等着。
终于,五更天的时候,院子里热闹起来,一人被护卫押送着,重重按跪在主座前。
林玉秀也被找回来了,满身脏污,一脸土色,袖间还有血迹,被伤得不清。
“玉秀,这事怪不得你,你去包扎一下。”
顾浅渊吩咐道,他向来熬不得夜的,睡眠浅,过了睡觉那个时候,便再难以入睡,加上连日来的应酬,整个人已是疲惫之致。
他低垂着眼,看着跪在地上的罪魁祸首。这个哑巴。
更脏了,浑身的泥巴,头发也散了,十指紧紧撑着地面,指关节泛着白,地上也洇出血迹混着泥水的一大片脏污。
看着让人反胃,顾浅渊懒得起再发火的心思,只颔首示意下人将药呈了上来。
他面色差,不想多言,看着她被捏着嘴巴,强灌进去药,心中的恶气才缓缓疏解。
这是极霸道的药,每月一发作,发作时让人感觉千刀万剐。是审穷凶极恶的犯人的药。被他轻轻松松灌给了一个弱女子。
仆从退下了,护卫们也松了手,宋二却没有再起来,她在地上蜷成小小的一团。
黑发散在她的面上,只见裸露在外细瘦的手指泛起了潮红色,控制不住地颤抖,深深地扣在地板上,还有压抑不住的喉间的嘶声。
“鬼七,好好招待一下我们的安和公主。”
他这样对手下吩咐道。
许多年后,是一个模糊的黄昏,他跪在地上,脊背挺得很直,空气中带着萧条的凉意。身着华服的女子从他面前踏过,衣摆繁复,环佩叮当。
他又想起了最开始的这个狰狞的夜晚。潮红的,细瘦的,伶仃的手指。
“别走,”带着点不可名状的绝望,他低语,“你看看我。”
黄昏中,那身影连停顿都没有,走的不快,也没回头。
正如他此刻,看她被慢慢拖走,心里没有半点怜悯。
————
肉肉下章一定,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