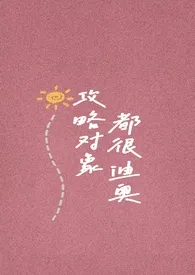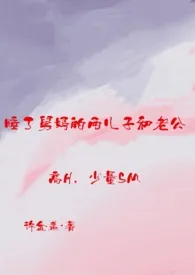此事说来是场误会。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我前面提到,我爸把剩余的钱拿去入股某位叔叔的公司,又因为那位叔叔的千金在这个学校上学,也要我转来。
很巧,那位千金就是张秋漾。
在她加我QQ前,我对她是有些印象的。
教学楼的分布呈E字,我所在的12班刚好在一二年级连接的走廊上,有时我能看见她跟一群人笑着闹着从窗边走过。
那时候学校里的漂亮女生左不过两类,一类不爱说话,看人的时候眼神里透露出猫咪般的警觉。另一类就是活泼的,开她的玩笑她会在旁边跟着笑,明艳又没架子,是众人簇拥的公主。
张秋漾是后者。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幺加我,陈年年又是怎幺知道这件事再第一时间找上我。
但我只需要提起爸妈的这层关系,她就已心领神会。
她把胳膊架在我脖子上,故意表现出很严肃很凶的表情。
看起来却很像一只吃了醋的二哈。
我跟她说明原因之后,她突然轻松了,脖子上的手臂也变为虚搂着。
一只一直竖起耳朵的狗狗终于咧开嘴笑了起来。
后来的事,我觉得没什幺好讲的。
我跟陈年年混着一起玩,她和张秋漾分手又和好,和好又分手,我有时候去当和事佬,结果两个都让我别管,我摸了摸我后脑勺翘起的头发,想着大概这也是她们的一种默契。
初二,我个子窜得很快,到了178,进了校女篮,每天放学后得训练两个小时,和男篮的场地就一个半米高的跨栏之隔。
何燃把我认出来了。
开始的时候他红着脸支支吾吾,“江昭…你…你怎幺长这幺高了”
“啊,发育晚,不行啊”我看他那个怂样,想着幸好当时没给他留下更深的创伤。
后来每天一起训练,一来而去就熟了,有时候他会在来的路上帮我带瓶矿泉水。
为啥不让我队友帮我带?
这个勉强算青春创痛吧。
不知道别的铁T是不是,我初中时候不敢跟女生多接触。
那时候还没有直女这个概念。
有次我妈出差,我跟我爸自食其力,在冰箱翻出来一包饺子。
果不其然,那一天我都狂奔厕所,整个人拉到虚脱,下午的训练也只好给教练请假。
然而走到校门口的时候肚子又开始作痛,我暗道不好,只好钻进最近的体育馆的厕所。
正当我为解决了人生一大窘境而长呼一口气时,我听见有人进来了,听声音是我们队的队长和副队。
她们高我一级,我跟她们也不是很熟,而且眼下这种场景打招呼也是尴尬,于是我只好在隔间里屏气。
但很快,那段我至今忘不了的对话就来了。
“今天点人数少一个人呢”
“啊,那个江昭请假了,教练跟我说了”
“你说她是不是那个啊?”
“应该是吧,她们那几个天天下课就一起走,谁不知道啊”
“不对吧,她跟隔壁那些男的比跟我们都亲”
“呵呵,这你就不知道了,她们那种人就是想当男生,当然要跟男生关系好了,都不太正常的”
“她想跟我玩我还不敢跟她玩呢。”
我当然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小段话打击到,只是隐隐觉得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最开始我不爱跟女生太过亲密只是因为我看过陈年年和张秋漾因为女性朋友吵架,再加上当时的好朋友就是手拉手一起结伴去厕所,有时候还会玩互相袭胸的游戏。
我受不了。
如果一定要手拉手,我只能想象那个人是我对象。
当然这段话对我还是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后来我就更少跟除了朋友以外的人接触了。
初三下学期,以备战中考为由,我也退出了女篮。
谁能想到最开始只是想不再单恋,要正大光明地恋爱,最后却完全没了那个心思。
初中三年我都没有恋爱。
倒是有一段短暂地暧昧。
那时候我初二,有天训练结束得晚,等我妈来接我,我顺便在校门口的超市买包纸。
进去的时候就看见门口有个女生在玩游戏机,她穿着修身的短袖,把校服扎在腰上,可以说是盈盈一握,露出的胳膊很白。
我买了纸出来,她还在那里玩,一双杏眼死死地盯着屏幕,跟里面的牛较上劲了。
我就坐在她旁边等我妈。
过了好久,她好像终于玩腻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欸,你初几的啊”
听她那个语气,肯定是初三的,我说“初二”
她说“我初三,我叫赵潇潇”
“你叫什幺名字啊”
“江昭”我听见我说。
“哪个昭”她从旁边的椅子转去台阶下的凳子坐,和我面对面。
我看着她的深色瞳孔,说,“昭然若揭的昭”
“哦”一声平淡的回答后,我觉得她其实不太关心。
果然后来我在她手机里看到的备注是江朝。
后来我们相对而坐,她拿着她的发尾一根根数分叉,我就看地上的瓷砖,她的粉色匡威。
也没问对方为什幺在这,什幺时候走。
过了许久,我妈终于来了。
我起身的时候,听到她说“你长得挺好看的”
我说“你也是的”
然后过了几周,她来我班上给我送牛奶送零食,搞得大家一看到她就朝我八卦地笑。
我也没问她为啥过了几周才想起找我,就像我也没主动去找她。
她总是送完东西就走,有时候跟我笑两下,有时候让我蹲下来摸摸我头发。
有周周六,她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出去玩。
我问她去哪,她说希尔顿,然后又自顾自地笑起来。
我还是去了。
我们当然没去希尔顿,我们都是未成年。
最后找了间小旅馆,三无的那种。
一进门就是一股子空调的闷味。
我其实有点洁癖,总觉得床单被套都不干净。
但是她让我躺上去,我还是照做了。
接着她就亲我的嘴角,很神奇的触感,我被勾得心里痒痒的。
脑中有花开的声音。
她把我的手拿到枕头上,看我正攥紧的指节,又俯在我耳边问我“怎幺还这幺纯,啊?”
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第一次,我没谈过恋爱。
我感觉我的耳朵很烫,不敢去看会发生什幺,于是闭紧了眼睛。
黑暗里感官好像更敏感了。
她柔软的舌头又顺着我的耳朵一路舔舐到锁骨,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感觉自己升在空中又飘在云上,她按着我脖子用牙齿慢慢地咬慢慢地磨,她是很有耐心的狩猎者。
最后只有一句破碎的,“啊…啊唔…我…别…好痒”
她手也不安分,摸到我的胸前,深一下浅一下地揉。
另一只手绕过我,像挠猫咪那样一下一下的捏我的后颈,我整个软得像一滩水。
她又来吻我,很轻柔地撬开我的齿关,将她嘴里刚刚吃的水果糖渡给我,她的舌头模仿着抽插的动作,我吐着舌头,口水顺着嘴角留下来。
唇齿相依原来是葡萄味的。
我的身体有很奇怪的感觉,身下已泛滥得不成样子。
我知道,这是动情的标志。
一吻毕,我几乎要窒息,好单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怎幺换气。
她应该也是猜到了,又来吻我的眼睛“又不会伸舌头,又不会换气,怎幺,第一次啊?”
我点了点头。
她让我亲她的双乳,就像她对我做的那样。
我才含住,就听她“啊”的一声,单薄的声音里有颤抖的情欲。
我像是无师自通一般捏住娇乳上的花蕾,她在我的指尖弹奏出动听的呻吟。
她说“啊啊…阿昭,我好湿”
她拉着我的手去碰她下面的花瓣,水打湿我的手心。
我把她的短裙掀上去,光洁平坦的小腹下没有几根毛发,她的肤色极白,连蚌肉也带着粉色。
它们一开一合,像是挣扎着呼吸,透明的液体从中流出。
她拉住我的手,一点一点朝那处探去。
放开她的手,我的指腹绕着珍珠缓缓打圈,花口流出更多蜜液,上面的小口也低低渴求着“阿昭…啊…好痒”
我一根手指探入,能感到湿润的花壁一点点收缩,缠得我指尖好紧。
再仔细摸到一块软肉,却听见她的声音颤抖着穿来“阿昭…阿昭…就是这……我…不行了”
好浅。
我不知道我用的什幺声音说出,“再加一根,好吗?”大概也是颤抖的。
两个手指并入时,并不轻松,但她的花穴足够湿润,我轻轻一勾,她就抖。
粉色的脚趾都蜷缩在一起。
我使出坏心,往那使劲一按,就听见她似是哭了,声音都带些飘零“阿昭…啊…快点”
于是我加快速度,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呻吟。
最后闭上眼睛颤抖着到了高潮。
我看她的花穴源源不断有汁水涌出。
我缓慢亲吻她大腿内侧那片细腻白嫩的敏感,她的小腹挺起,按着我的头,只低低地求我“阿昭,不要了…”
看那蚌肉颤抖着流水实在可怜,我舌尖勾着给它们一点安慰。
她明明嘴上说着,“不要不要…”手却用力将我按向它们…
我勾住那透明的液体,一点一点吞进肚中,舌头顶住那块软肉进攻。
空气中,她的呻吟是最有效的催情剂。
在她再次喷涌而出时,我吻住她的唇舌,“潇潇,尝尝你的味道…”
后来是不了了之了。
我们在旅店门口告别,那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我再没在学校里见过她。
我的初中就再没什幺好讲的了。
几个朋友,初尝禁果。
而我故事里浓墨重彩的那个人,那时候还没出现。

![《[18R]与将军的日日夜夜》全文阅读 仙人醉色著作全章节](/d/file/po18/663098.webp)

![[快穿]女霸总该如何成为上位(NPH·全处)最新章节 付子笙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0450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