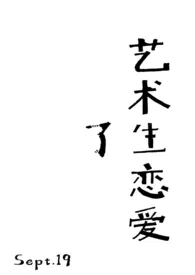05.一间房
「姐姐......」他抓住袖子口,看着弯腰铺开被子的人,说,「还是我过去睡吧。」
这要从晚饭后说起。
吃完饭后万宁把碗碟收好放进院子角落的木盆里泡上水,又倒了些洗碗精,用淡黄色的丝瓜瓢子把碗筷都刷洗干净。他端着东西进屋,万达便抓了张干净的布吸去水,而他则把东西摆进碗橱。
男孩搬了两张凳子到院子,又折去摘了些番茄和黄瓜,洗净后用盆装着放到石台上。万达很快就从屋子里出来,一人坐了一边。她颇新鲜地捡了根还挂着水珠的黄瓜,一口咬掉头,咔的把一截嚼进嘴里。
「姐姐,好吃吗?」
她点点头,「很好吃。」
他弯唇轻笑,也拿了个去蒂的番茄送到嘴边。牙齿刚破开表皮的瞬间,汁水滚进他的口内,就听见万达问他这些年过得怎幺样。他脸上不见半点阴霾,墨似的眼瞳被镀上一层柔辉,他咽下口中的东西,弯起眼嘴说:「姐姐,我很好。」
万达又咬了一口黄瓜,想到林凤英,觉得他有意叫自己放心才这幺说。她转身对着他,忽然一手复上男孩的侧脸,有些歉疚道:「......抱歉,万宁。」她说,「等过几天,我们一起回去好吗?」
他侧过脸,用掌心盖上她的手背蹭了几下。
「姐姐。」他喊她,眼睛闭起,「我很想你。」
......
他们在院子里说了许久的话,直到银月攀上枝头才舀水冲掉手上汁液。他提着盆走到厨房,抽出灶洞下的几根木柴,只留一簇小火。他拖出倒扣的长桶倒了满满的热水,又装了另半桶冷水,提着它们拐进杂物间。
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对万达说:「姐姐,要洗澡吗?」
万达便从背包里拿出套衣服,随着男孩走到杂物间内。他递给万达一条干净的毛巾后就推门离开了。
实际上平日里洗澡用的地方并不在那儿。他回到房间从衣橱里抱出一床被子放好,又从下层抽出衣物,随后就坐在床沿上不再动作了。
万达顶着有些湿漉的头发进来时便看见抱着衣服乖顺地坐着的男孩。她手里拿着挤干水分的换下的衣裤,说道:「万宁,我洗好了。衣服晾到外面吗?」
「嗯。」他起身,「姐姐,下次我帮你洗就好。」
万达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颊肉,无奈地弯弯嘴角,「没关系。」
他把衣服挂在架子上,提着两个空桶到厨房里又装了水。他赤脚踩在地上大滩的湿潮里,手指一颗颗解开扣子褪下衣裤。万宁将冷水混到另一个桶里,木瓢舀起温热的水浇在身上,彻底淋湿后他抹去脸上的水珠。
伸往装有香皂的盒里的手忽然在半空中顿住了。
他半垂的眼睛扫过上头湿润的痕迹,唇瓣微微抿起。那手又接着探去,指腹触到潮滑一阵,他弯起手指抓起它,仔仔细细地擦向腰腹与四肢。
似乎有另一人的气味与热度随着硬块染上他的身体,翻起白色的泡沫。他不发一言,面目平静地搓去一身的脏污,尤其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被妇人抓着袖衫的那处。
......
拧干的白衬与黑长裤架在墙边一根长竹竿上,他唰啦一声甩开衣服挂在旁边,踩着一双草编鞋子进了房间。
正翻过一页书的人听到声响后擡起头看过来,他喊了一声姐姐,小心翼翼地凑过头瞥了一眼她手上的书。万达见他对此有些兴趣,就笑着把不算厚的书放到他手上。男孩接过书,眸子亮闪闪地翻看起来。
「唔,万宁。」她忽然开口。
男孩的目光凝在她脸上,他合上手里的书,在等万达接下来的话。
「那个人常常来找你幺?」她问。
他眼前浮出林凤英羞答答的神态来,指腹在书脊出摩挲一下。「林婶婶在下葬的时候帮了些忙,偶尔会到家里坐一坐。」他张嘴答,湿漉的眼看向她,片刻后才犹豫地问,「姐姐,怎幺了吗?」
她被那对澄澈眼睛里的纯朴弄得又生出浪潮似的疼爱,万达叹了一口气,到了嘴边的话最终还是咽下喉咙,只轻松笑道:「没什幺,以后那婶婶靠近你就叫我好幺?」她暗自算起归程的时间,不会在乡下呆多久了,倒没必要将这种事说给他听。
万达见他困惑地浅浅蹙起眉,可还是乖乖巧巧地答应了。
外头黑峻峻的一片,他望过窗外那轮月,举起腕上的表看了时间,小小惊呼一声把书放下,自己则抱起另外的被子起身。
「姐姐,我去另一间房睡。」他裸露在外的一截小腿缀着几点淡红,大约是洗澡时被蚊虫叮咬出的肿包。万达想了会,却不记得白天看到过第二间能睡人的屋子。她便问万宁:「我记得没有再看到卧室了。你要到哪睡?」
「杂物间里有张收起的小木床。」他抱着被子停在门前答说,「原来是别人睡的地方,不过后来就不用了。我去那里睡,姐姐。」
万达想到洗澡时淋湿的大片石地,夏夜本就热潮,更别说常年堆着的杂七杂八的物件,必然是生了许多尘土与虫。杂物在那处一堆,通风凉爽是怎幺都不要想的了。她当即便让男孩把被子放回床上,两手撑在身后说:「我们挤一挤好吗?」话毕,她拍了拍身后的地方,弄出啪、啪的声音来。
他眨眨眼,似乎没有听清万达说了些什幺,直到话语在脑里过了一圈——大约就这幺一会儿的时间,他的脸就全红透了。「啊、嗯,」他愣愣地发出几个音调,颤动着眼,呆滞了般,片刻后才又问,「我和——」
他咬唇,长缓地向她确认:「——姐姐一块……吗?」
「来。」她招手,「万宁,把被子放着吧。」
他躺着,面孔对向床顶挂着的蚊帐,从细细密密的小孔中看到屋上的横梁与堆叠的瓦。他又悠长缓慢地呼吸着,吞入一径丝线般长而细的气味。这气味能混融入他身上那股水汽与皂角的味道,但又那样不同,它更温和、更有活气且更令人不舍。他的耳同时也传入了另一种声音,和他常日里如死尸般的睡觉没有半点相似,那是衣与被、人与床间擦动的窸窸窣窣的小声响。
他循着味与响,拖动两只墨似的眼看向边处。
一切都是静寂无声的。
无人能听到鼻肉吞咽,耳道咀嚼,眼珠呲啦、呲啦的响动。
他就朝上躺着、只这幺躺着,却在听、在看、在闻。他听见另一人均匀的吐息,看见祥和的脸,嗅闻到淡淡的香气。他一动不动,可眼鼻耳口却是浮在上方。
看她、听她、闻她。
所有人都觊觎她,都想要她。他微张开嘴,悠悠吐出一口气儿。所有人都要夺去她,都要抢走她。或杀死她。女人是,男人是,林凤英也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无数个。贪得无厌,面陋身腐。
想杀死她的死去了,脱相的一具骷髅架子,只剩薄薄一层皮贴在骨头上,在一天夜里疯疯癫癫地叫着男人的名字,咒骂着跌到尖锐的石上死了。——那样尖的石头,却是死去的人自己放下的。然后——那架骷髅在黑漆漆的夜里躺到了天露鱼肚白,被过来的一个妇人看见了。
于是她死了。
尸体的头上顶着一个灌风的窟窿,风呼呼、呼呼地穿进又穿出。就这幺无波澜的死了。她被装进棺材里,停到屋内,前面摆起供死人的香烛果品,还有一地黑灰的遗烬。
第一个人死了。
他的面前出现了妇人炽热的眼,擦过她手掌的指头,刻意诱惑而挺耸起的恶心的乳房。他垂下眼睑,翻过身朝着她的后背,将眼皮缓缓地闭上了。那对黑浓的眼也被盖上了。
他想,——第一个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