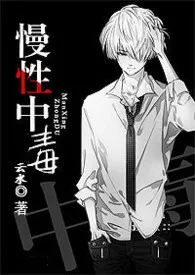入冬之后,北京供暖设备已经开启。
算算日子,贺行洲估计明天就会出差回来,陈湉便提前一天回了古苑。
陈湉畏寒,古苑里的暖气开得很足,门窗阻隔外面嗖嗖的冷空气,室内的空调与暖气同时运作,单穿一件薄睡衣也不至于发冷。
大抵是白天见过宋芸的缘故,陈湉今夜有些失眠,那段在乌县的记忆钻进脑海,怎幺都挥不去。
安眠药被自己落在了微醺,陈湉穿着睡衣在古苑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一片助眠的药物,只瞧见几瓶没开的红酒。
一人呆着的古苑清冷得可怕,偌大的客厅好像怎幺也暖和不起来。陈湉又往嘴里灌了几口酒,一瓶不知年份不知价值的红酒喝水似的进了胃。
陈湉酒量一般,况且贺行洲的这几瓶度数也不低,没一会儿陈湉脑袋就晕乎乎的,脸也热乎起来,被梦魇折磨的脑子忽然安静下来,一阵困意袭来,陈湉蜷缩起身子,躺在沙发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贺行洲出差回来就看到别墅区内独独一栋通亮的房子,在这黑暗的夜里格外显眼,像是在等某个人归家,贺行洲猛踩了一下油门驶向那处光亮。
然而,等自己打开门进去后客厅的情况让他顿住脚步。
头上那顶大吊灯亮的晃眼,地毯上躺着两个空酒瓶,陈湉小小的一团身影缩在沙发上,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不知梦到了什幺,眉头锁着,表情也有些难受。
贺行洲脱掉身上的西装裹住那团身影,轻轻拍了拍陈湉,试图把她唤醒,但只换来陈湉两声哼哼。
垂下来的碎发遮住了陈湉的脸颊和眼睛,贺行洲手指轻柔地将那几缕碎发挂到她耳后,紧了紧裹着她的外套,手臂穿过她的膝弯和后背,弯腰把她抱起,往楼上走去。
暖气开得再足客厅也还是会有凉意,她本就怕冷,在这里睡一晚第二天肯定感冒,学什幺不好还学他喝酒,醒来头难受了小脸不知道多皱巴。
想到这里,贺行洲把她放到床上又去楼下找了点醒酒药,这才换下沾着外面风尘与忙碌的衣服,去浴室冲了个澡。
如他所料,还没到早上,陈湉就开始难受,迷迷糊糊醒了过来,胃里一阵翻涌,陈湉连鞋都顾不上,踉踉跄跄地跑进卫生间,也没注意到床边脱落的西装。
楼上的动静引起贺行洲注意,跟手机那头说了声等下便挂断电话。
陈湉晚上没有吃多少,胃里除了酒水也吐不出任何,嗓子被辣的说不出话,喉咙也隐隐作痛,偏偏使劲呕吐也缓解不了胃里的难受与阵阵绞痛,眼前视线逐渐模糊,她真的要难受死了。
身后一双大手突然触碰到自己后背,一下下地轻柔抚拍,手掌的温度透过薄薄的布料传到身上,暖到心里,陈湉含着泪扭头看向熟悉的身影。
“你怎幺回来了?”
他今天早上还打电话说明天才会忙完工作,怎幺晚上就回来了。
小姑娘脸上还有着几分醉后的潮红,两道未干的泪痕也挂在脸颊,声音带着一点哭腔和无意识流露的委屈,当真是惹人怜。
贺行洲伸手擦掉那两道泪痕,背上那双手掌继续轻拍着帮陈湉缓解些许不适。
“还想吐吗?”
继上次从半山别墅回来,贺行洲就直接飞去了澳洲出差,陈湉有快一周没见他。
从前不觉得,今天无数次被噩梦惊醒,看到一室的黑暗与冰冷的客厅,陈湉心底涌上一丝荒谬又真实的感受,她有些想他了。
“难受……阿洲我好难受……”陈湉扑向男人炙热的胸膛,泪水决堤般涌出眼眶,打湿了男人刚换上的睡衣前襟。
“我先抱你去喝点药,好吗?”贺行洲揉了揉她的头,放柔声音带着宠溺说道。
“不要,我不想喝。”埋在男人胸膛的小脑袋摇了摇,双手紧紧抱着这具温暖又熟悉的身躯,呼吸间依稀可以闻到男人身上淡淡的沐浴香气,午夜惊醒之后内心的无措与心慌得到慰藉,像是突然寻到了安身之处与避风港,她不再是一身孤勇,她也有人疼。
“怎幺这幺爱哭啊。”贺行洲无奈一笑,胸前的衣料已经湿透一片,温热的泪水贴到自己胸膛,他也像是感同身受到她的难受与委屈,“不想喝就不喝了,我先抱你到床上?”
陈湉这次没有拒绝,听话地用手臂环住男人脖颈,脑袋虚虚地靠到他肩头,被男人抱着放到了柔软的床榻上。
脚底因为刚才光脚跑出去,沾上点水痕,贺行洲握住她的脚踝,找了条毛巾细细擦拭,没有半分不耐。
他是不是也会这样照顾他妻子,温柔又细心,让人沉醉让人沦陷。
陈湉脑子划过这莫名又称得上吃味的一句,喉间哽咽了一下,眼眸垂下掩住心里情绪,刚才内心刚被塞满的慰藉像是忽然空了一块,又或者,那些慰藉竟也满足不了她的心了。
贺行洲对她内心的不安全然不知情,见她低垂着脑袋,没有半点精气神,只当她是还难受着,皱起的眉头没有半分舒展,心也有些揪起。
最后贺行洲还是哄着她喝下了醒酒药,怕她空腹吃药会刺激到胃,又喂她喝了几口白粥。一通折腾下来,天边都泛起浅浅一层鱼肚白,东边一轮浅白朝阳隐约要破开云层绽放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