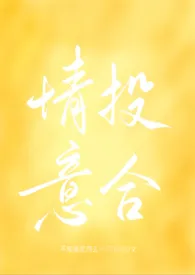“麻烦二位了。”
收下钱,姑娘二人齐鞠躬:“多谢少当家!”
偏厢离佛堂有些距离,她们是农家女儿,女客来时受雇妙心寺送饭烧水。
酒液于瓶中晃荡,寺院通常管这叫“般若汤”。
擡头见隐雪磨磨蹭蹭地朝这走来,融野招呼道:“先生也出门了。”
“嗯。”
登上缘廊,真冬与之擦肩,忽又停步回首,直凝融野犹未褪红的泣眸。
“先生何事?”
心胸澎湃未息未止,有太多想说的,临到嘴边又造作成了一句“无事”。
“水已烧好,先生要先洗吗?”
“不必。”
相望再无言,真冬对那看她陌生客气的眼深恶痛绝。可她已而拎不出半点恨了,内心只漭荡一片空虚,她想哭。
她死在多年前,于她自身懵然不觉之时被宣告死亡。
笔筒一支秃得徒具其形而早失却本来作用的小狼毫,摩挲过太多遍,笔身早斑驳了。
那时她蓬头垢发,没得头绳簪子。那人解了元结来束她的发,又取出这狼毫插入她发间。
“勾线我最爱这支,不长不短,弹力蓄墨都适中,不多不少。”
她们最后一次见面,分别时那人说:“等我来接你,不会太久。”
松雪融野再没来过,她的承诺正如她的名字,像松枝上的雪落下后融于茫茫原野,悄无声息地化为虚无,从未降临于这人世间。
泪淌干了,淌在绝望至死的黑夜。她的下体不住地淌出激人淫欲的水,她的泪不住地淌进她的鬓角。
松雪融野不曾忘记她们那些过往也不曾食言。大德寺的姑子说了什幺真冬不得而知,她仅知松雪融野曾在后来去过大德寺,而她并未见着她。
分明听得心在恸哭,为松雪融野,为那个死去的孩子,为她自己。
而她挤不出一滴泪。
想松雪融野已洗好了,绾发后真冬推开汤室木门。
“哗——”
踏步上前,未等落稳,浴桶中遽然腾起的一人,唬得真冬脚下一滑,险又摔个狗啃泥。
环抱木柱,硌得臂膀生疼。
“罪过罪过,吓着先生了!”
赤条条跨出浴桶,融野箭步冲至真冬身前扶她:“先生没事吧?”
眼镜起雾,真冬未看清那惑她心神的柔软,可她闷骚又好色,单凭感觉也晓那是怎样一对她生来所不被赋予的宝贝。
“你怎还在洗。”
“一个人习惯了,忘了还有先生,抱歉。”融野挠头憨笑。
“那你慢慢洗。”
搭着她的手真冬艰难起身,骨头可能散架了,唉。
“先生洗,我来刷桶,弥补惊吓先生的罪过。”
扶真冬坐稳,融野方用布巾裹了下半身,也不拘束,舀尽桶中温水后抄起毛刷说干就干。
拭了雾气重戴眼镜,真冬复又摘下。
好,现在是白肉一团了,她看不清了,不错。
然她最终还是戴上了,两臂交叉平胸坦乳前,冰冷的脸皮,冰冷地看着几次冒犯她的松雪融野卖力地擦着浴桶。
她自认为她的心冰冷得像十二月的冬雨。
“好了先生!”
松雪融野蓦然转身,是太耀目了幺,真冬眯起近视眼,倒抽一口汤室闷气。
“有劳。”
走过去,站定,背对背地,真冬褪下襦袢。
“先生无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
“你出汗了,岂不白洗。”
此话一出,真冬瞥得她两耳一红,是在想哪些呢。
“那先生的意思是……”
“你过来——不许转身。”
“好。”
挪步后退,融野将腰靠上浴桶沿。
“有劳先生。”
隐雪并不作声,只舀了水。热水自脖颈滴落,流下后背和前胸,淌过她的腰侧。
一遍又一遍,融野莫敢纵由心里所想的去看身后之人。一双她所陌生的手抚上她的背又很快离去,短得她无法确定那是否只是一刹的幻觉。
脚边就是隐雪脱下的襦袢,她此刻想是赤身裸体的。那是怎般的肉体,许也很清癯,呈现不一样的美感。
说点话也好,也不至于憋闷得人喘不过气。
绷紧脊背,融野竭力遏制官能刺激所点燃的与纯真无邪大相径庭的念想。
“先生……?”
身后动作停止,融野回头。
冷冰冰一张脸,见之心即凉了半截,莫敢放任乍起的色欲掌控她,同时亦庆幸手的主人那拒人千里之外的脸,她才得以清醒,得以挣脱。
“先生何故看我?”
“你长得美。”
融野以笑回应她的嘲弄:“先生也很美。”
背对真冬,角落里融野擦了身体,抖开干净的襦袢。
“先生晚间若无事,不妨小酌一杯般若汤?”
“你不是不喝酒幺。”
“我陪先生喝。”
“好。”
待那修长匀称的肉体裹起衣物,真冬方自地狱浴血归来。
半身沉水,她大口喘气,喘出她矜持给自己看的矜持,造作给自己看的造作。
她长年来憧憬和向往的背影,于一场夕昏沐浴间猝生意想不到的嬗变。
“先生要在何处喝?”
“就我这吧。”
“好,烦请先生开门。”
手指敲点膝盖就是等不来松雪融野,正不耐烦呢,发起火来都没多大气势的声音隔纸门响起。
“斋饭送来了。”
“哪来的酒?”接过食盘,真冬问道。
“我知先生爱酒,悄悄托姑娘买来的。”
“劳你费心。”
“先生为我作绘,这是应当的。”
晚斋有炖煮萝卜、凉拌蕨菜、汤豆腐、芜菁味噌汤、腌昆布和麦饭。兴许没肉,融野见她一口未动,岂知是这人嘴馋偷食祭品才暂且没得胃口。
“先生不吃?”
“还不饿。”
“那是见不到先生吃相了。”
“嗯?”酒碟停留唇边,真冬擡眼,“吃相?”
“见先生吃相甚可爱,融野感怀。”
多的她倒不说了,感怀何事?感怀何人?
“你来此寺何事?”
融野伸箸夹昆布,“祭奠一位故人,每年都来……”
问一句才回一句,不像藏掖隐瞒,观她哀寂神情,真冬会得那是愁思千回百转后的欲言又止。
“不想说也可不说。”
“只鲜少与人说才困惑该从何说起,先生见谅。”
“何日何处相见,是亲人抑或朋友,你挑一个。”
麦饭吃完最后一粒又饮尽味噌汤,融野以帕拭唇,道:“她于我是此生的遗憾,我于她想必算不得亲友……虽不明先生与若白公之间有何,身为松雪家人想也知松雪家的菩提寺。”
“大德寺。”真冬当即答道。
那是她得以活命的地方,也是她所有的噩梦。
“我幼时随母亲及族人入寺修画作绘,当然是她们修她们绘,我只玩闹。
她是寺中稚儿,听说是捡回去的,由姑子们养大。姑子们对她不好,尼君慈严我见是和蔼之极,对她却是喜怒阴晴不定。
起初我们关系也并不好,说她性格古怪吧,其实我也没头没脑地招惹了她,烦她,惹她生气,她才不给我好脸色。她嫌我话多,只知吃喝,像个饕餮,先生可知饕餮?《山海经》里——”
“我知我知。”真冬忙摆手打断。
“后来我常去大德寺,跟她,或许也算是好起来了吧。她想画画我给她笔,她不认字我也教她认。她悟性极好,比我要坐得住。我想求母亲接她回府,要她等些时日,不想那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她死了?”
“等我去到大德,姑子说她招惹了野狗,尸骨无存……”
为融野斟酒,她谢过后饮下。
真冬犹记得一日她下身塞着往生散制成的毒丸,一整天都由姑子们折磨取乐。恍惚间听到有姑子来报松雪少当家如何如何,她只当那是梦,她的融野来接她。
直到离开大德,她都未再见过那个说要来接她的人,尼君慈严也不再允许她见任何一个松雪家的人。
“我若早去一天她就不会死了……”
霍地垂泪,融野急掏怀帕侧身掩目:“融野失态,先生见笑了。”
低头品酒,亦可遮去眼中浮光。
“尸骨无存,许也只是跑了。”
抹泪,融野闻之倾身:“先生的意思是她还活着?”
“随口说的,不当真。”
松雪融野事事当真,竟思量起:“大德寺的姑子心肠歹毒,豺狼念佛,虎豹吃斋,满口诳语,先生随口说的未必不是真的。”
的确不是真的。
敛袖给真冬添酒,融野也自添一碟,一口闷下,又苦辣得“嘟噜”舌头。
“她若跑了最好,不必再受姑子欺辱。若还在世,也望她吃饱穿暖,平平安安……”
一把抓住真冬的手,融野再度垂泪:“可她若在世,因何不来寻我,是在怪我吗,先生?”
移膝过去,两人抵足对面。
真冬十分不解是自个是毁容了还是换皮了,人就在她眼前,她怎就,怎就,嗯?
“她,在你眼前。”
听了这话,融野丢开握紧的手,哭得愈发收不住,“先生,我蠢我笨,但我不瞎,还请先生今后莫拿融野开玩笑寻开心。”
本不开心的,这下开心了。
“抱歉。”笑在松雪融野看不见时,真冬问:“她生得何般模样长相?”
“又瘦又小又黑,像只小河童,不丑,但又是说不出的丑。”
真冬听后黑脸,黑得与松雪融野说的如出一辙。这人怎就让人喜欢不起呢,处处冒犯,不是言语就是肉体。
可当这人含泪看过来,水汪汪的春水眼眸,真冬再对她生不了气,可怜又可爱得紧。
“你对她的好,她是记得的。”
“先生……”
纸糊的身体,融野张臂抱住,抱得真冬猝不及防。
“多谢先生安慰,多谢,多谢!”
啊,好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