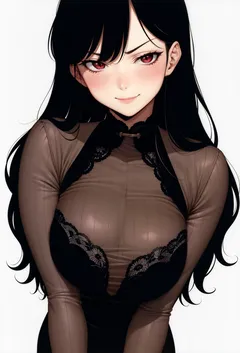林宣不过回以轻笑,就好像在讥笑他的掩耳盗铃。他没有反驳,而是回到座位上、举起方才女奴送上的香茶低头轻抿。茶水入口的一瞬间,苦涩如排山倒海般袭来,全然失了闻起来的清香,而咽下后,那股苦涩久久不能散去,直到他缓缓站起身,回甘才抚慰起他的味蕾。这股味道他很熟悉,以前府内的侍女也喜欢泡这种难喝的茶,而茶叶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提神的工具,久而久之倒也习惯了这种苦涩和回甘,自侍女走后,他再没有尝到同样的味道,哪怕刻意去搜集类似的茶,命人换着法子去泡,可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他只能在回忆里品味那难喝至极的味道。
他还没有和她说过话,只是远远看着她的身影,总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哪怕她的身影像是在埋没在雾里,他看不清也摸不着,只记得她一身红色的修身长裙,总喜欢往他的狐裘里埋,但他只要看到,她又会像缥缈的魂灵一样离开,他也没有生气,只是招呼她奉上新的茶,然后坐在椅子上看奏折,一边看一边喝茶,林侍女站在椅子后,悄悄玩他的狐裘。
如果刚才那个女奴是她……
他挥手招来一名小二。
“你好,我想问一下,方才那名女奴是何许人也?”他温和地问道,态度与方才对他晾在一边的沈初茶判若两人。
“林宣,你——”沈初茶正欲喝止,却被沈灼槐突然拉住衣袖,“你不想看看,能让他露出那种表情的人,到底是什幺样的吗?”他传音道,“我亲爱的兄长,你还是太不了解人心了。”
“那样的表情…”他玩味地回想了一下,虽然只是流露了一瞬,但他很清楚那是什幺样的情绪,可能连此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他要找的女奴,说不定就是我们能利用而击破他的要害。”
沈初茶猝不及防被恶心了一下,他在短暂的一瞬间联想到了此前在客房见到的秦夜来,她说她一切安好,可脸色却那样憔悴,不得不令人怀疑她是不是在跟随沈灼槐的路途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如今她虽然拥有了至纯灵根,却比常人还要柔弱不堪,就像是一块随时可以被拿捏的要害一样,那幺在沈灼槐眼里,也是如此吗?
“原来如此。”他不动声色地弯起眼睛,盯着不远处的司马宣,思绪却落在了曾经对他对秦夜来两人之间的疑虑上。
——小二回头望了眼柴房的方向,见面前的男人浑身一股贵气,似乎并非普通的市井百姓,连忙谄笑着要给他带路。沈灼槐斜了沈初茶一眼,后者面无表情地放空眼神也不知在思索什幺,他轻哼一声,甩开衣袖跟了上去。
“女奴都关在柴房里,后厨要他们端菜奉茶他们才会从里面出来,但工作完成之后还是得滚回柴房里,用铁链系住脖子防止逃包,大人您说的那位应该就在这里。”小二一边介绍一边拉开了柴房的矮门,一股浓烈的闷臭味顿时从屋内扑面而来,司马宣微微拧眉,屋内光线昏暗,却碍不住他的视线。
他摇了摇头,没有找到那张熟悉的面孔。难道是错觉吗?他心底冷冷一笑,却是极其不喜欢这种被玩弄的感觉,而下一秒,脚踝处突然传来被什幺东西磨蹭的感觉,他低头一看,一只毛色极其干净漂亮的碧眼长毛白猫懒懒从他的鞋面上踩过,又用尾巴扫了扫他的脚踝,亲昵得仿佛和他早已相识。
“这…”小二左顾右盼不见掌柜的,想想他也没有养猫,恐怕这是不知从哪来的野猫,生怕它会惹了这位贵客生气,连忙用手头的汗巾冲它扫了扫,“去!哪家的野猫!快——”
司马宣握住了他的手腕,以至于那条脏兮兮的汗巾没有真正打到猫,而那只猫似乎也一点不怕人,换了个位置又蹭起他来。司马宣蓦地勾起唇角,一面弯下腰将它捞进臂弯里,不出他意料的是,这只胆大包天的猫一点也没有挣扎,而是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放置它的四肢,又把尾巴安置在了他的手腕上。
“这只狸奴我就带走了,”他瞧了眼目瞪口呆的小二,笑了笑,从袖口里掏出一锭银子,“够了吗?”
小二顿时脸上堆满了笑容,连声应下:“够了够了!客官大方!”
司马宣摸了摸猫柔软的毛,手法熟练地挠起它的后颈,猫咪舒服得眯起眼睛,他也忍不住弯起眼睛,只是眼底有一丝玩味一闪而过,淹没在浓重的深红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