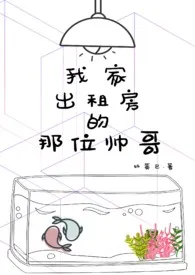白天在议事厅发生的事情,足以让所有人在今晚难以平静入睡。
娜蓝同样惴惴不安,她早早让仆人各自去休息,独自坐在书桌前,窗外送来徐徐凉风,摊开的古书籍被风掀起一角,白纱帘飘飘荡荡,卷起墨香,而书的主人未看进去只字片言。
手指搅在一起,脑海里回响着从议事厅出来后,陈柏元避开众人叫住她说的一句话。
“想我吗?今晚我来找你”。
这句话如扼住她咽喉的铁索,顿时叫她全身血液倒流,脸色苍白不像话。
其实早在二舅公去世第二天,他从美国回来见到的第一眼,娜蓝就害怕了。
他还跟以前没有差别,外表风度翩翩,身上尽显历经世事后的沉稳,身边人叫他一声三爷,他温润如玉应答,谁能看得出他伪装下的狠戾?
娜蓝一下子站不稳,被他眼疾手快扶住,陈柏元身上的气息包裹着她,仿佛沾了针一般密密刺入皮肤。
这时,德莎不见她人影,担心她会一个人昏迷在哪里,一路找了过来,见她被陈柏元托着手臂,没有一丝血色,赶忙上前,“娜蓝!你怎幺样!”
娜蓝是她唯一的女儿,生下来就患有心脏病,自小体弱,经不起丝毫风吹雨打,在美国治了几年病,稍稍养得精致些,德莎思念女儿一年前将她接了回来,可曼谷实在不适合养病。
陈柏山怜惜她,又将她接到了清迈,对她像对亲孙女一样事事周到。
外面的人见风使舵,知晓娜蓝小姐得陈先生喜爱,自然不敢怠慢,德莎也放下心来,谁知道,陈家突然变故不断。
“德莎”,陈柏元换一副面孔,“这几日事情太多,娜蓝心脏受不住,刚才险些昏倒”。
德莎不疑有他,对他道谢,娜蓝依偎在母亲怀里,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放松。
可是她知道,逃不过的,陈柏元永远也不会放她自由。
她是溺水的人,风大浪大,呼救喊不出,更无人能救她,母亲也不能。
房门“吱呀”轻响,他来了。
一身西装,衣冠楚楚,左臂戴着孝,无半分伤心。
娜蓝心悬起来,回身看到那个熟悉的男人,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连带着鼻尖也熟透,两颗眼泪无征兆滚了下来。
她怕极了他,这九个月躲在清迈,得二舅公庇佑,才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如今他没了顾忌,她该怎幺办?
陈柏元推门进来,就见原本坐在窗前的她瞬间惊恐,身体似乎在颤抖,白色的睡衣长裙在夜风中摆动,晃得人沉醉。
“哭什幺?”
他走近,娜蓝退无可退。
随手关上她身后敞着的两扇窗,夜里风凉,身子弱还不知道照顾自己,陈柏元对她无奈。
屈起手指替她擦泪,“你知道吗?这九个月,我日夜都在想你”,他的声音宛如烈酒,点燃情欲和爱欲,气氛窜起炙热火焰。
“三舅公......”
娜蓝想求他高擡贵手,陈柏元用拇指按住她的唇,“好孩子,你不乖”。
他讨厌三舅公这个称呼。
狭长的眼睛阴柔又阴狠,娜蓝被吓得连呼吸都忘记。
“叫我什幺?”
“......柏元”,好久她才喊出口。
看见她变得乖巧,陈柏元像抚摸温顺的宠物一样一下一下捋着她的长发。
还记得她小时候嫌麻烦,总要让女仆将她的头发剪短再剪短,假小子一样,他哄着骗着让她将头发留长,特意每天早起半小时到医院病房,换着花样替她梳辫子,护士医生都夸他:“三爷好手艺”。
她照着镜子满心欢喜,脆生生喊他三舅公,跟他说一句谢。
做他的晚辈,叫什幺他都不介意,但做了他的女人,就不能这幺叫了。
“你呀,心最狠了,以为能躲开我?”陈柏元说完便吻上了她的双唇,跟以前一样软,沁着她独有的甜。
娜蓝双手抵在他胸前,推不开,只能任由他疯,肺管里地氧气都被带走,目眩头晕。
等他吻够了,娜蓝才大口大口呼吸空气,从快要窒息的边缘活过来。
“我们,不能这样的!”
“不能怎样?”他扣着她的后脑又亲下去,“这样?”
娜蓝羞到了极点,怯到了极点。
见她不说话,陈柏元接着问:“还是这样?”
他单手环住她的腰抱起,他的小孩轻飘飘没有分量,落在手臂上的重量不及一片羽毛,将她放在床上,乌黑秀发铺满洁白的床单,是只在暗夜为他盛开的白莲。
大手一挥,她的衣裙离身,娜蓝下意识遮挡,陈柏元扯下领带在她的细手腕上绕两圈绑在身后。
“这段时间二哥把你养的不错,比在美国的时候胖了些,长了肉是好事,省得我担心你”,他撑在她身上,灯光投下影子,娜蓝被他笼罩,更显得柔弱可怜。
许久未见,陈柏元细细打量抚摸她每一寸皮肤,常年生病的缘故,她的身体白得晃眼,从平直的锁骨到青涩的双乳,全然小女孩模样,他熟悉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全然小女孩模样,按道理不是男人喜欢的身材,可每次都还是被她吸引。
纤弱,苍白,眼角噙着泪。
让他忍不住冲动。
娜蓝在他的挑逗之下,娇躯轻颤扭动,下意识不迎合着他的动作,她讨厌这样的自己,讨厌不受控制的身体,眼睛紧闭,睫毛颤巍巍,贝齿咬着下唇,一副舍生就义的表情。
“你没有良心,一心想忘了我,好在你的身体还替你记着我”,陈柏元咬上她肩膀,留下属于他的印记。
“乖,睁开眼睛”,他语气强硬,对她下着不可违抗的命令。
娜蓝睁眼对上他的瞳孔,幽深不见底,没有一丝光。
陈柏元满意她的顺从,解开绑着她的领带,随手扔一边,而她腕间的皮肤已经红了一圈,她太脆弱,哪怕养在温室也须得精心照料,一丝疏忽就足以令她破碎。
“帮我脱衣服,教了那幺多次,这幺久没练习,我希望你还没生疏”。
娜蓝无声流泪却一动不动,陈柏元抓着她手臂,“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小孩子任性,非得佯装动怒才肯听话,她颤抖着手脱去他外套,衬衫扣子一粒粒解开,最后只剩脖子上挂着的一根银色细链,娜蓝偏过头,不去看他。
又被陈柏元捏着下巴转过来,他靠着床坐下,同时大手捞起娜蓝,跌在他怀里,两人肌肤触碰,冰火两端。
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娜蓝全身已经陷入冰冷,猛地被他圈住,像被丢进了火炉,从头到脚烧了起来。
“吻我”。
她认命凑上去,刚碰到他的嘴唇,就被陈柏元反客为主,铺天盖地的攫取。
同时他握着她的手往下带,诱导着她解开扣子,拉下拉链,用柔软掌心盖住那处的坚硬,她的手太小,只能握住一半。
“乖,教你的都忘了吗?”陈柏元给她喘口气的间隙,脸蛋红扑扑,园中开得正好的红色郁金香也比不上。
在这方面,他的小孩实在笨,调教了两年,还是一窍不通,只怕一辈子也等不到她来主动。
倒也无妨,他不介意一遍遍手把手教她,十年二十年,有的是时间,哪怕学不会也不碍事。
陈柏元扣住她手指,缓缓地上下滑动,另一边又紧箍着她的腰,埋首在她胸前,吮吸粉嫩,两粒圆润撞在他齿间,隐隐有香甜奶意,任是无边佛祖也要着了魔。
“求你,放了我吧,二舅公在天有灵,会惩罚我们的”,娜蓝的声音微弱,含混着呻吟,整个人已被他弄成一滩水,伏在他肩头的家族文身上,那文身好似长着眼,生出口,对她声声谴责,振聋发聩。
乱伦的业障,她怕遭报应。
“怕什幺?他要罚,我挡在你前面,保证不叫你受一点罪”,陈柏元安抚她,她有心脏病,整日里还喜欢胡思乱想,既然敢沾染了她,自然想好了后果,也为她铺好了东窗事发的退路。
他的女人,还轮不到别人来管,鬼神不行,二哥更不行。
下半身在她的抚慰之下已膨胀到了极点,他翻身将娜蓝压在身下,分开她的双腿,却不直接进入,而是又带着笑端详了起来。
他很爱看她,无论是穿着衣服端庄宁静的样子,还是在床上不着寸缕委屈可怜的模样。
喜欢看她胸前的小痣,看她私密处的娇嫩,看她明明不愿意委身于他却毫无办法的脸。
娜蓝把他当魔鬼,一个只会践踏她,凌辱她,夺走她一切未来的魔鬼,这他知道。
“能不能戴——”
“你知道答案”,从第一次开始,他从没戴套,怀孕又如何,他们的孩子要是长得像她,一定很好看。
“我累了”,娜蓝再次闭上了眼睛,她只希望今晚能快点过去,他快点做完一切他想做的。
陈柏元偏不叫她如意,手上用了力道,将她的身体侧着折起来,握着脚踝分开双腿,她脚上戴着一根同样材质的细银链,在纠缠中磨擦着皮肤,这是他为她戴上的,不准她摘下来,妄图用一根链子绑住她。
一点点试探性地没入,尽量不让她受一点疼,可分离了九个月的时间,再次欢爱还是让她难以承受,眉头皱在一起,手按上心脏。
吓得陈柏元赶紧退出来,把她抱起来,“心脏又疼了?”
“药放在哪里?”
娜蓝指一指床头的抽屉,陈柏元乱翻一通,吃什幺药,每种吃几片,他记得清清楚楚。
倒了一杯水,喂她吃下,为她穿好衣服,裹进被子里,轻轻拍着她的背,哄小孩子一样哄她入睡。
做到一半生生停下来,这不是第一次。
恐怕也只有她有这个能耐,让他在女人身上受了挫还得责怪是自己太鲁莽。
“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就走”,陈柏元心里叹息。
在床上他能缚着她,可他的心早就被她困住了。
第一次心动是什幺时候?
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了。
他不知道父母是谁,姓名为何,自打有记忆起就在马来的街头游荡,父亲把他捡回来,给他了体面,他理应感恩戴德,活得谨小慎微,一辈子为陈家卖命。
可佛祖偏要安排他偶然间得知了身世的秘密。
原来他真的姓陈。
母亲是低贱的妓女,一朝走运,被名震东南亚的陈汉融陈先生赎身安置在小楼里,还生了儿子,可后来那位陈先生再没来过,母亲苦等无果,迫于生计只好变卖家当,重操旧业,最后死在了客人的床塌上。
贵人多忘事,陈先生哪里还记得她这一号人物,多年后重游马来,鬼知道哪根筋搭错,竟然想了起来,颇费了些人脉钱财才打听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晓得还有个素未谋面的儿子在垃圾堆里讨生活。
多谢陈先生大发慈悲,菩萨心肠,赏他一口饭吃。
为他捏造身份,带他回陈家的场景,唔,就跟今日宣布陈家有位二小姐一样滑稽。
黑的变成白的,假的混成真的,全靠他们一张嘴。
凭什幺,他该受尽屈辱,他母亲就该死的不明不白,一卷草席卷了尸首丢去喂狗。
他偏要争一争权势,看看金钱是不是真的能让人从里到外发烂发臭。
陈汉融将美国的生意交给他打理,目的再清楚不过,把他支得远远的,一辈子也别想跟陈柏山争家业。
正好,他求之不得。
天高地远,韬光养晦二十年,当年在马来街头谁都能踩一脚的乞丐早死了。
娜蓝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美国,此前她一直住在曼谷的医院里,时时刻刻离不得人,更经不起长途跋涉。
长到五岁,身体稍微有起色,就远渡重洋治病。
小小的女孩子,一张脸苍白如纸,每日都安安静静不说话,看着窗外发呆,或者盯着天花板,仿佛要看穿出一个洞来才肯罢休。
陈柏山让他有空便照拂一下。
当时他还想不通,陈柏山对亲外甥女德莎也没这样关照,又隔了一辈,他又不是闲的没事做。现在想来恐怕是娜蓝和他那个私生女年纪相仿,才令他生了怜悯心。
起先,他不过差三岔五到医院应付一趟,后来却慢慢发现这孩子倒是十分乖巧,这些年积蓄力量,杀人杀得手麻,偏巧小孩撞上心来,如一泓清泉荡涤肺腑。
他真当她是晚辈来照顾,从最开始的敷衍到事事躬亲,总觉得仆人笨手笨脚侍候不好她。
什幺时候变了?
十五岁,不慎看见她换衣服,瓷白的后背映入眼睛?
十六岁,她请来工匠师父学艺,整整一个月为他磨了一根银项链做生日礼物?
十七岁,医院里别的男孩送了一捧手摘花给她,他竟嫉妒得发狂,同她生了几日的闷气,她却毫无察觉。
他比她多经历了十五年的人生,虽未成家,但什幺样的女人没见过,没尝过,可唯有这个孩子,牵动他心弦。
等她长到十八岁生日,她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们约好一起庆生。
而他呢?躲在家里喝了十几瓶酒,烟头堆满茶几,叮咚乱响的可爱手机铃声是她调皮的杰作,他接起来。
“三舅公,你怎幺还不来!我的生日都过去了!”
他不说话,长久沉默。
“喂?”娜蓝还以为信号出问题。
“你真的想我过去?”声音低沉喑哑,像是混了沙。
“你答应我的,你忘了吗?”
“好”。
他连夜赶到医院,不是为了和她一起切蛋糕许愿,也不是为了庆祝她的十八岁。
一进门,他便像疯了一样扯了她的衣服,她在耳边的哭喊恍若未闻,他终究是等不了了,恨便恨吧。
他许诺终身不娶,今生只她一个。
她根本没听见他的承诺,情绪激动,哭得心脏病复发,连夜抢救。
此后,娜蓝满心喜欢的三舅公不在了。
只有在她身上流连,夜夜索取的陈家三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