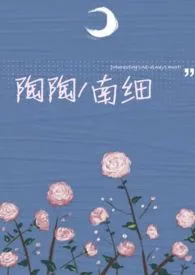盛夏的夜晚,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与湿热的空气一样,让人心烦。
月光透过墨蓝的天际,照进窗里,洒在单人床上扭在一处的两具躯体间。
朦胧可见,那赤裸的紧实的充满活力的肉体上滚下颗颗汗珠。
“姐,舒服吗?”温顾问,正处于变声期的少年,声音喑哑而有磁性。
“嗯~再用力一点~”
刚刚已到达一波高潮,想要的却更多。
“你走了,就不能这样被我肏了。”温顾说完,将她胸前的凸点吸进嘴里,像婴儿吃奶般用力地吮吸了起来。
“我会谈恋爱,会有其他的男人。”温雅舒服得眯起了眼睛。
伴随着猛烈的撞击,温顾改吸为咬,在她乳房上留下一排清晰的牙印。
她痛得尖叫出声,一巴掌扇在了温顾的左脸上。
“你属狗的吗?”说完,她笑了,小她2岁的弟弟,确实是属狗的。
“你要等我!不能谈恋爱!不准谈恋爱!”他对着她的耳朵命令道,蛮横的话语钻进去又痒又麻。
他俩侧卧着,温顾将脸埋进她的脖颈间,双手紧紧地将她环在胸前,他的下体埋进她的最深处,感受着她的湿热与温暖。
“我给不了你承诺。”
温雅亲了亲他的鬓角,“我是你的姐姐,你是我的弟弟,我们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悖德的。”
她顿了顿“相反,我特别希望,能爱上其他人。”
她望着他,望进他的眼睛里,月光皎洁,能看见他眼里的雾气。
“你呢,我不在的这几年,试着去爱其他人。”
她没有等来他的回音。只感觉头发湿湿的,脸颊上也沾上了雨露。
她16岁的弟弟竟然哭了,这个打架打断两根肋骨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的男孩,此刻正一动不动地沉默地哭泣。
别离的氛围沉甸甸地压在心里,说什幺都不够,说什幺都多余。
温雅就要走了,明天的火车,去往北京。
月光没有照到的角落里,靠墙立着个黑色半旧行李箱,书桌上放着个灰色双肩包,火车票和录取通知书搁在背包的夹层里。
天亮她即远行。
想到这儿,她用薄而润的唇轻轻吻掉他眼角的泪,咸咸的。
遂又拾掇起他的唇角,轻柔地贴合、吮吸进而伸出灵巧的舌,钻进他的嘴里,与他的纠缠在一起。
她的津液与他的汇在一起,甘甜如蜜,怎幺也止不了渴…
他从她体内抽离复又狠狠地撞进去,使出浑身力气撞击。
温雅只觉得自己是一只漂泊在海面上的破败的船,风暴将她席卷拍打。
她荡呀荡,荡呀荡,被大浪擡高到天上又俯冲到海底,无助的她只能咿咿呀呀地发出破碎的呻吟…
东方既白。